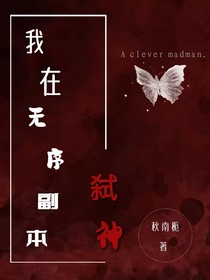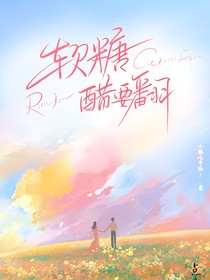第1章:铁门之后的疯狂
我是被消毒水的气味呛醒的。
喉咙像塞了团烧红的棉花,在地上滚了半圈,后脑勺撞在冰冷的瓷砖上,疼得倒抽冷气。
眼皮重得像压着铅块,勉强睁开条缝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锈迹斑斑的铁门——那种老式精神病院才会有的,栏杆间距仅容一只手穿过的铁栅栏门。
记忆碎片开始翻涌。
三天前“疯潮”爆发时,我正攥着最后半盒抗焦虑药往安宁精神病院赶。
街道上有人突然暴起咬人,有人抱着电线杆尖叫“他们在我脑子里装芯片”,我躲进便利店时,后脑勺挨了一记闷棍。
现在想来,那棍子大概是从货架上砸下来的——此刻我左脸还贴着半片碎玻璃,血已经凝成暗红色的痂。
“醒了?”
沙哑的男声像砂纸擦过铁皮。
我抬头,看见个穿蓝布工作服的老头,左眼皮总往下耷拉着,正倚在铁门另一侧的墙上,手里转着串钥匙。
钥匙撞击声在封闭空间里格外刺耳,混着远处若有若无的呜咽,像极了当年我值夜班时,重度抑郁患者在走廊里的低泣。
“李明,护工。”他用钥匙尖敲了敲铁门,“这地方三天前就封了,你是第四个被丢进来的。”
我撑着墙站起来,膝盖发软。
作为前市立医院精神科主治医生,我很清楚这种虚弱感从何而来——脱水、低血糖,加上可能的脑震荡。
但更让我警惕的是李明的眼神:他扫过我白大褂上残留的医院徽章时,瞳孔缩了缩,像是看见块突然冒出来的绊脚石。
“水。”我直截了当地说。
作为医生,我太清楚此刻身体需要什么,也知道在这种封闭空间里,示弱只会让自己成为猎物。
李明笑了,左眼皮抖得更厉害了:“水要拿东西换。”他从裤兜里摸出个军用水壶晃了晃,“昨天张老头拿半块压缩饼干换了半杯,前天那大学生……”他突然住了嘴,目光越过我看向我身后。
我这才注意到,走廊尽头的窗户被铁板封死了,唯一的光源是天花板上忽明忽暗的应急灯。
在幽蓝的灯光里,二十多双眼睛正从各个病房的门缝里望出来——有穿病号服的,有裹着破毯子的,还有个老太太把床单系在腰间当裙子。
他们像群被惊动的夜行动物,在我转头的瞬间又缩回了黑暗里。
“这是安宁精神病院?”我问。
“不然呢?”李明把水壶揣回兜里,“现在外面全疯了,就这儿铁门够厚。”他用下巴指了指我身后,“你住203,刚收拾出来的。记住,饭点在下午三点,药品归我管,想活过三天就别乱打听。”
他转身要走时,我瞥见他裤脚沾着褐色的污渍——像是血,又像是某种药膏。
203病房的门没锁。
推开门的刹那,我差点被腐臭味呛退。
靠窗的铁架床上堆着发霉的棉絮,墙皮大块脱落,露出底下斑驳的红砖。
但最让我皱眉的是床沿蜷缩着的年轻人: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T恤,膝盖抵着下巴,正用指甲拼命抠床板,指缝里全是血。
“别怕。”我蹲下来,和他保持着半米距离——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侵入性动作最敏感,“我是医生,沈砚。”
他猛地抬头。
那是张过于苍白的脸,左眼角有道新抓痕,像是自己挠的。
“床底……”他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音,“床底有怪物。”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向床底——除了团破袜子什么都没有。
但我没急着否定,而是从白大褂口袋里摸出支笔(感谢袭击者没翻我全身),在掌心画了朵太阳:“你叫什么名字?”
“王小斌。”他盯着我掌心的画,指甲慢慢松开,“他们说我有病,可我真的听见了……”
“听见什么?”我保持着缓慢的语速,这是应对焦虑症患者的标准技巧。
“抓挠声。”他颤抖着举起手,比划出指甲刮金属的动作,“像小指甲……我弟弟的指甲。”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三年前接诊过类似病例:父母隐瞒双胞胎弟弟夭折的事实,姐姐总说“床底有妹妹的笑声”。
王小斌的症状如出一辙——他在守护某个不存在的“存在”。
“你弟弟是不是很小就……”我话没说完,他突然扑过来抓住我手腕,力气大得惊人:“你也知道?他们都不信我!”
我没挣扎,任由他攥着。
他的手指冰得像块铁,脉搏快得吓人。
“我信。”我轻声说,“他是不是总在晚上来找你?”
他瞳孔微微收缩,这是信任的信号。
“嗯……”他松开手,低头盯着自己发抖的手背,“他说冷,我就把被子塞下去……”
“所以你总抠床板?”我指了指他血肉模糊的指甲,“想给他挖个暖和的地方?”
他突然哭了。
眼泪大颗大颗砸在我白大褂上,把“沈砚 主治医师”的工牌都打湿了。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时,他像受惊的兔子般缩回墙角,用胳膊抱住头。
“哟,挺会哄人啊。”李明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手里端着个铝制饭盒,“刚醒就当起救世主了?”他把饭盒往我床上一摔,里面的稀粥溅出来,“这是今天的份,省着点喝。”
我扫了眼饭盒——顶多半碗,米粒数得清。
“药品呢?”我问,“抗精神病药、抗生素,你们有储备吗?”
李明的左眼皮又开始抖:“问那么多干嘛?”他转身要走,突然停住,“对了,明天开始轮值打扫,你负责二楼厕所。”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别让我失望啊,沈医生。”
他走后,王小斌从墙角挪过来,盯着我工牌上的名字:“你真的是医生?”
“真的。”我摸出兜里最后半块巧克力(谢天谢地袭击者没翻到),“要吃吗?补充点能量。”
他接过巧克力的手还在抖,但眼睛亮了:“我妈妈以前……”他突然闭了嘴,低头把巧克力掰成两半,“给你一半。”
我接过那半块时,听见走廊传来细碎的脚步声。
透过门缝,我看见个系着蓝围裙的老太太正往每个病房门口放东西——有的是半块馒头,有的是卷起来的旧报纸。
她经过203时顿了顿,往门里塞了个玻璃药瓶,轻声说:“治头疼的,省着用。”
“赵阿姨,清洁工。”王小斌小声说,“她总偷偷帮人。”
药瓶上贴着褪色的标签:去痛片,20片。
我抬头时,赵阿姨已经拐过了楼梯口,只留下围裙角的蓝布在风里晃了晃。
夜幕降临时,应急灯彻底熄了。
我躺在发霉的棉絮上,听着四周此起彼伏的叹息声、梦呓声,还有王小斌在床底塞被子的窸窣声。
李明的话在耳边回响:“想活过三天就别乱打听。”可他不知道,作为精神科医生,我最擅长的就是“乱打听”——从患者破碎的陈述里拼凑真相,从护工反常的举动里找出漏洞。
更重要的是,我闻到了危险的味道。
李明裤脚的污渍,可能是长期接触某种药膏留下的——比如治疗褥疮的磺胺嘧啶银;他控制食物和药品的方式,像极了监狱里的“牢头”;而他看见我工牌时的眼神,分明是在评估威胁等级。
窗外传来远处的爆炸声,闷闷的,像打雷。
王小斌在黑暗里轻声说:“医生,你不会走的,对吧?”
“不走。”我摸出赵阿姨给的去痛片,攥在手心。
药片棱角硌着掌纹,像某种承诺。
后半夜,我听见铁门被什么东西撞得哐哐响。
是外面的幸存者?
还是“疯潮”里彻底失控的人?
不知道。
但我知道,明天必须做两件事:找到医院的药品储备室,弄清楚李明到底藏了多少资源;同时,得让更多“病人”相信——这个前精神科医生,能成为他们在疯潮中的锚。
月光从铁板缝隙里漏进来,在墙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我望着王小斌蜷缩成一团的背影,突然想起医学院导师说过的话:“精神病院不是牢笼,是破碎灵魂的避风港。”现在,这个避风港被铁门锁住了,而我,可能是里面唯一能修好它的人。
寻找百优解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只为一个明天的人们
- 在一段荒唐而遥远的历史中,西煌帝国统治着几乎整个大陆。表面上,其疆域广袤无垠,城镇繁华喧嚣,商队往来不绝,欢声笑语不断。然而,实则内部腐败不......
- 0.5万字8个月前
- 我在无序副本里弑神
- 「出逃者」浅羽x「神牌」林沨林沨在求死时意外进入副本系统,为了与系统达成交易,获得【起死回生】复活妹妹,林沨选择留在系统成为玩家在过副本途中......
- 6.5万字8个月前
- 奇思妙想,小说合集
- 此文不只有一个故事,很多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短篇小说。第一篇:花心痞帅硬汉;季北辰VS独立理智坚韧冷艳美女;莫希。(现代言情,花心浪子遇真爱......
- 6.1万字6个月前
- 重生之周目轮回
- 一觉醒来灵樱雪发现她回到了一切的伊始,她能否成功改变命运呢?而她又是否是真的重生了呢?敬请期待“重生”之周目轮回
- 14.1万字5个月前
- 软糖醋要翻
- 正在连载中
- 11.2万字5个月前
- 神明未故-d873
- 一夜间,天界崩塌,神明分裂成“魂”与“魄”。萧然,流浪千年的苦命儿,竟藏有神之真魂;而高坐神殿的“神子”萧衍,却是无情无感的神魄。两人皆精于......
- 12.3万字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