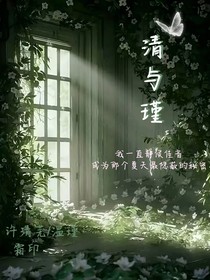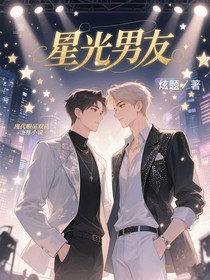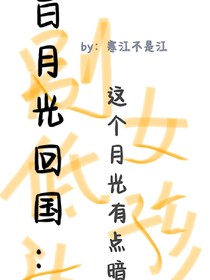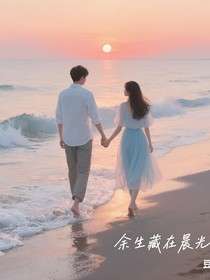无题
苏然这次回家,是接父母去城里小住。出发前,父亲把葡萄架最后检查了一遍,断过的竹竿上缠了新麻绳,他拍着架子说:“等咱回来,葡萄准能挂满,歪的地方结的准最甜。”母亲往包里塞了把菜园土,用旧手帕包着,说“城里的花得沾点老家的土才肯长”。
车子开出村口时,母亲一直回头看,直到老井的影子缩成个小点。“那口井的水桶,我特意换了根新梁,”父亲摸着方向盘,语气有点舍不得,“可总觉得不如断梁的顺手,像少了点啥。”苏然从后视镜里看,老井边的石板路上,仿佛还留着父亲打水时歪歪扭扭的脚印。
到了城里的住处,父母站在楼道里有点拘谨。父亲摸着墙壁说:“这墙太光溜,不如老家的土墙,能钉钉子挂竹筐。”母亲却径直走到阳台,把带来的菜园土倒进花盆,土撒出来点,她也不擦,说“让土先认认门”。
第一顿饭,母亲在苏然的小厨房里折腾,橱柜太高,她踮着脚够调料,碰倒了瓶酱油,洒在灶台上,像画了朵褐黄色的花。“这样才像做饭的地儿,”她笑着擦,“太干净了倒不敢下手。”炒出来的菜,咸淡依旧不均匀,父亲却吃得香,说“比饭店的合胃口,带着点‘手忙脚乱’的味”。
苏然的阁楼被父母收拾出了新模样:母亲把父亲织的歪毛衣挂在床头,说“夜里冷了能随手抓着”;父亲把那只断梁的水桶洗干净,摆在窗台上,里面插着从菜市场捡的野菊,花枝歪向一边,倒比花瓶里的更精神。“你这剪辑室太素净,”父亲敲着旧电脑,“得添点‘过日子的响动’。”
第二天带父母去菜市场,王老太老远就喊:“亲家来了!”拉着母亲看她的新豆腐坛,坛口的泥封故意抹得七扭八歪,“你看这封,跟然然他妈捏的韭菜盒子似的,漏点气才香。”母亲摸着坛子笑:“我就爱这股实在劲,比城里超市的真空包装对胃口。”
络腮胡大叔拎出只断螯螃蟹,非要送给父亲:“叔,这蟹跟您修葡萄架似的,缺了角也不耽误活泛。”父亲把螃蟹放进水桶,断梁的桶此刻派上了用场,螃蟹在里面横着走,桶晃悠着,像在给老伙计打招呼。
中午在便利店吃饭,老板媳妇端上刚蒸的馒头,有个瘪得厉害,母亲伸手就拿:“这我爱吃,面发得有脾气,像咱老家的地,得顺着它的性子来。”父亲喝着便利店的散装酒,酒瓶塞还是松的,他说:“你看这酒,漏点气才醒得透,跟人似的,太严实了反倒闷得慌。”
下午带父母去看苏然拍的片子,屏幕里王老太的手在豆腐上轻轻点,煤球举着煤晶追夕阳,父亲修葡萄架的背影也在里面一闪而过。母亲突然抹起眼泪:“原来你拍的这些,都是咱天天过的日子啊。”父亲没说话,只是把母亲的手攥得更紧,他的指甲缝里还留着菜园土的痕迹,像给生活盖了个章。
晚上回住处,母亲在阳台种的菜发了芽,歪歪扭扭的,却透着股钻劲。父亲搬了个小马扎坐在旁边,说:“你看这芽,不直溜才好,说明根扎得深。”苏然看着他俩的背影,突然觉得,自己的家从来没离开过——父母在哪,那些带着土、沾着烟火、漏着点气的日子,就在哪。
夜里,苏然被父母的说话声吵醒,父亲说:“明天教然然编竹筐吧,他那相机包总破,编个歪筐给他装镜头。”母亲说:“我教他捏韭菜盒子,就教漏馅的那种,让他知道,过日子漏点啥不算啥,补补接着过。”
苏然翻了个身,嘴角带着笑。窗外的菜市场渐渐安静,只有晚归的摊贩收拾摊子的声响,像老家院门外的虫鸣。他知道,不管是在老家的葡萄架下,还是在城里的阁楼上,只要身边有这些带着不完美却依旧热乎的人,日子就永远有拍不完的故事,家就永远有回不够的方向。
第二天一早,父亲果然找出竹篾,母亲和面的盆里,面发得鼓鼓囊囊,又要开始捏那些漏馅的韭菜盒子了。苏然举着相机,镜头对准他们忙碌的身影,心里头亮堂堂的——原来回家,就是回到这些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回到这些不完美却最踏实的温暖里。
躺平失败:我在综艺当显眼包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草莓思恋
- 也许上帝带给了你痛苦的家庭,但往往会派一位天使把你解救出来。而7岁的沈翊在某一天也遇见了属于他的天使……
- 1.4万字9个月前
- 清与瑾
- 亲爱的读者读者,你们好:欢迎你们打开这本又甜又虐的小说,(没有狗血剧情,拒绝一切抄袭)本人作者喜欢痞帅男主,无抄袭,希望你们喜欢,也希望你们......
- 3.4万字3个月前
- 星光男友
- 意外邀约:经纪人透露综艺背后是顾司寒点名要他。
- 2.7万字3个月前
- 白月光回国:这个月光有点暗
- 宋止清是顾寒凉的白月光,这在京都公子圈不是什么秘密。听闻顾太子爱宋止清连命都不要了,深情至此,真让人闻着落泪,听着伤心。宋止清一朝回国,发现......
- 0.3万字2个月前
- 余生藏在晨光里
- 两个恩爱的人会发生什么事情
- 9.0万字2个月前
- 海风吹过咖啡馆
- 世界总有人在隐藏着自己的秘密,自己过去的往事,当你遇见那个可以诉说秘密的人时,往事带来的伤口会绽放出夏日最灿烂的玫瑰,林千宴不止一次的看过海......
- 1.5万字2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