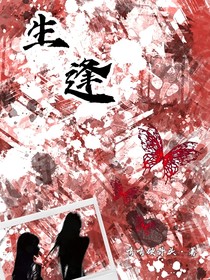无题
(一)
苏然的相机包放在玄关的旧鞋柜上,带子上的银杏叶补丁被晨光染成了金箔色。他弯腰换鞋时,指尖触到鞋盒里露出的半截歪竹片——那是综艺结束后,扎扫帚的老爷子塞给他的,说“下次拍扫帚,用这个当支架,稳当”。
厨房飘来面香时,苏然正对着电脑整理照片。屏幕上是综艺里的画面:爱豆举着歪馒头笑出酒窝,小花蹲在歪木桶前数铜丝,老木匠的刨子在木板上划出的弧线,像给时光系了个蝴蝶结。手机在桌角震动,是节目组发来的消息:“苏老师,观众想看‘歪物件背后的人’,第二季能继续合作吗?”
他转头看向厨房,母亲正把蒸好的馒头摆进缺角的篾筐。馒头在筐里歪歪扭扭地挤着,热气从篾条的缝隙钻出来,在晨光里织成网。“妈,综艺想接着拍。”苏然倚在门框上,看母亲用抹布擦那只歪沿汤锅,“他们说好多人开始找老物件了。”
母亲把汤锅挂在墙上的歪钉子上,钉子是父亲当年随手敲的,歪得刚好能卡住锅耳。“拍呗,”她往碗里盛粥,用的还是那只歪口碗,“让年轻人知道,日子不是装在玻璃柜里的摆设,是磨出来的。”粥面在碗里斜出个温柔的弧度,米油凝在歪口处,像给碗沿镶了圈珍珠。
苏然抓起相机往门外走,镜头先对准了墙上的歪钉子。取景框里,汤锅的影子斜斜地投在白墙上,像片被风吹歪的云。他忽然想起综艺里那个片段:小花摸着歪木桶的铜丝说“这才是会过日子的样子”,原来镜头真的能把生活的褶皱,熨成人人都懂的暖。
(二)
老街的石板路被昨夜的雨洗得发亮,苏然踩着水洼往箍桶铺走。远远就听见“叮当”声,老师傅正给新做的歪木桶上箍,铁箍在他手里弯出的弧度,比上次拍的更不规则。“苏小子来啦,”老师傅头也不抬,木槌敲在铁箍上的力道分毫不差,“看我这新桶底,歪得比上次巧。”
桶底的木纹歪歪扭扭地缠在一起,像老树根在土里较劲。“这是枣木的,”老师傅用手指抠着木纹里的泥,“去年暴雨冲倒的老枣树,树干本身就歪,做桶底刚好,装热水不裂。”他的刨子还斜靠在墙角,刃口的卷边比以前更明显,“你看,这卷刃刨枣木才顺,新刨子早把木纹刨烂了。”
苏然蹲在旁边拍铁箍与桶底咬合的地方,铜绿混着木屑粘在木头上,像给木桶盖了枚印章。老师傅忽然停下手里的活:“前儿有个小姑娘来,说看了你的片子,非要学箍桶。”他指着墙角堆的歪竹片,“我教她弯铁箍,她总说要弄直,后来我让她看这歪木桶装水,她才肯跟着歪处走。”
正说着,铺子里进来个穿校服的姑娘,手里拎着只裂了缝的塑料桶。“张爷爷,能帮我改成歪木桶吗?”姑娘把桶放在地上,桶底的裂缝歪歪扭扭的,“我看了苏老师拍的片子,说歪桶底好用。”老师傅笑着摸出卷尺:“裂得巧,刚好能改成斜底,装水时裂缝朝上,还能当水位线。”
苏然的镜头追着姑娘的手,她摸着塑料桶的裂缝,眼里闪着光:“我奶奶总说,东西坏了别扔,修修更合用。”这话让苏然想起母亲补袜子时说的“补丁处更结实”,原来这些藏在日子里的道理,早被老辈人缝进了时光,只等某个瞬间,顺着镜头钻进年轻人心里。
(三)
从箍桶铺出来,苏然往扎扫帚的老两口家走。刚拐进巷口,就听见老太太的笑声:“这丫头捆的绳结,比蝴蝶还歪!”他加快脚步,看见院子里围了几个大学生,正跟着老爷子学扎扫帚。竹篾在他们手里歪歪扭扭地缠,捆出来的扫帚头一边高一边低。
“歪着才好,”老爷子拿着学生扎的扫帚演示,“你看,高的这边扫墙根,低的那边扫地面,比齐刷刷的得劲。”他的剪刀还是那把钝的,剪竹篾时总要歪着剪,“你们年轻人总说要对称,可扫地哪有对称的?墙角是歪的,门槛是斜的,扫帚得跟着它们的性子来。”
苏然蹲在石榴树下拍他们,镜头里,竹篾的青、麻绳的黄、学生们的白衬衫,在阳光下搅出团暖。有个戴眼镜的男生忽然举着扫帚跑起来,扫帚苗在地上拖出歪歪扭扭的痕,像条会动的青蛇。“真能把瓜子壳扫干净!”他惊喜地喊,“比我家电动扫帚好用!”
老太太端来凉茶,用的是粗瓷碗,碗沿歪得刚好能托住下巴。“苏老师,你拍的片子我们看了,”她给学生们分碗,“有个城里媳妇说,看了扎扫帚那段,回家跟婆婆学纳鞋底了,说歪针脚更合脚。”苏然喝着茶,凉茶顺着歪碗沿流进嘴里,比直口碗多了份妥帖。
临走时,老爷子塞给苏然一把新扎的扫帚,竹柄歪歪的,握在手里刚好贴合掌心。“这柄是照着你的手型削的,”老爷子拍着他的手背,“你举相机久了,手腕累,歪柄能省劲。”苏然试着挥了挥,扫帚苗在地上画出的弧线,像相机取景框里的构图,舒服得不用费心思。
(四)
中午回老街馄饨摊时,老板正给一口新汤锅换歪沿。旧汤锅的沿口被磨得只剩半圈,他用锤子把新沿敲得歪歪扭扭,“这样才够味,”老板擦着汗笑,“上次综艺播了之后,好多人来问歪沿锅,说煮馄饨香。”
摊子前围了不少人,有个穿西装的男人举着手机拍汤锅,屏幕上是综艺里的片段。“就要用这锅煮,”男人对老板说,“我女儿看了节目,非让我来买歪沿锅煮的馄饨,说漏出来的汤是精华。”老板笑着舀馄饨,歪勺在歪锅里搅出的漩涡,比直锅更有烟火气。
苏然坐在老位置,缺角的馄饨碗还放在桌上。老板端来馄饨,缺角处露着的那只,果然是最胖的。“苏老师,你看这个,”老板指着墙角的煤炉,炉口歪得厉害,“烧起来火往一边斜,刚好能烤烧饼,比正经烤炉还匀。”煤炉上果然放着个歪烧饼,芝麻在歪处堆得更厚,香得钻鼻子。
吃馄饨时,邻桌的阿姨正给孙子讲歪木桶的故事:“爷爷那时候挑水,就爱用歪桶,说水面斜着看,不会洒。”小男孩咬着馄饨问:“那歪苹果会结果吗?”苏然心里一动,想起窗台上的歪苹果,芽尖已经抽出了嫩叶,歪歪地朝着阳光,像只举着的小手。
(五)
下午去拍补锅的老两口,他们的摊子前摆了排歪铁锅,锅沿的铜补丁歪得各有模样。老太太正给一口锅补底,铜片剪得像片枫叶,“这锅是隔壁王婶的,”她用小锤敲着铜钉,“她说锅底歪处总先热,炒菜香,补的时候特意让我把铜片也歪着补。”
老爷子在旁边敲铁砧,铁块在他手里弯出不规则的弧度。“现在年轻人爱买新锅,”他擦了擦汗,“但总有老主顾来找,说歪锅用惯了,炒的菜有老味道。”他的铁砧缺了个角,敲起来声音却比新铁砧更浑厚,“这角是当年救火烧掉的,现在敲起来,铁块反而不打滑。”
苏然拍老太太补锅的手,皱纹里嵌着铜锈,像给岁月镀了层暖。有个姑娘拿着裂了的砂锅来补,砂锅的裂纹歪得像条河。“我妈说这砂锅炖鸡汤香,”姑娘摸着裂纹说,“看了节目才知道,裂了补补更能用,歪着补的铜片还好看。”
老太太给砂锅补铜片时,特意把铜片弯成波浪形,顺着裂纹走。“这样才牢,”她对姑娘说,“就像人过日子,顺着弯走,比硬撑着强。”苏然忽然觉得,这些补锅的铜片,就像生活的创可贴,歪歪扭扭地贴着,却把日子粘得更结实。
(六)
傍晚回家,父亲正坐在院子里编竹篮,用的是苏然带回来的歪竹片。竹片在他手里歪歪扭扭地缠,咬得比直竹片更紧。“这竹片好,”父亲编着说,“综艺里那个老木匠说得对,歪篾条咬得紧。”
母亲在厨房蒸馒头,歪案上的面团滚出的圈,比以前更歪了。“今天买了新面粉,”母亲探出头说,“用歪案揉,比新案更出筋。”苏然走进厨房,看见面粉在歪案上积的白,像给时光铺了层雪,母亲的手在雪里揉着,像在酿月亮。
窗台上的歪苹果又长高了,嫩叶歪向窗台的布鞋,鞋头的歪处刚好给它挡住晚风。苏然给苹果浇了水,水滴顺着果皮的裂纹渗进去,像给它喂了口甜。“这苹果要是结果,肯定是歪的,”父亲走进来,看着苹果笑,“歪苹果才甜,阳光照得匀。”
晚饭时,电视里在放综艺的花絮,爱豆正在学用歪扫帚,扫得满地是笑。“你看,”母亲指着屏幕,“这孩子握扫帚的姿势,跟扎扫帚的老爷子越来越像了。”父亲夹了块咸菜,放在歪口碟里:“这就对了,日子是学出来的,不是量出来的。”
(七)
夜里整理照片,苏然把补锅的铜片、扎扫帚的竹篾、歪沿锅的汤渍,都归在一个文件夹里,命名为“生活的弧度”。桌角的歪苹果发出细微的声响,他凑过去看,发现又抽出片新叶,歪得更厉害了,却透着股使劲长的劲。
手机响了,是那个大学生发来的视频。她的宿舍窗台上,摆着个歪竹篮,里面放着几本书,竹篮的歪处刚好卡住书脊。“苏老师,你看,”视频里的姑娘笑着说,“歪篾条真的咬得紧,书掉不下来。”竹篮旁边,放着个歪口杯,里面插着支歪茎的花,倒比直茎的更有精神。
苏然给她回消息:“歪处有韧性,像日子。”发完消息,他拿起相机,对着歪苹果和满桌的照片按下快门。取景框里,月光从歪苹果的叶缝漏下来,在照片上投下的影,像给每个歪物件都系了根银线,把它们串成了生活的项链。
他想起综艺里的一句话:“不完美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此刻看着这些歪歪扭扭的物件,忽然明白,所谓的完美,不过是日子磨出的默契——歪案记得面团的软,歪桶懂得水的性,歪扫帚知道地面的坑,就像母亲懂他的口味,父亲知他的心事,这些藏在歪处的懂得,才把日子粘得扎扎实实,暖得熨熨帖帖。
窗外的月光更亮了,苏然把相机放在枕边,镜头对着歪苹果。他知道明天醒来,芽尖又会歪向新的阳光,就像生活总会朝着暖的方向,慢慢长,慢慢弯,长出最舒服的弧度。而他的相机,会继续追着这些弧度,把藏在歪处的暖,都拍进时光里,因为这些不完美的瞬间,才是生活最动人的模样。
作者:3637尽力了
躺平失败:我在综艺当显眼包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致命情谜:我在豪门渣男图鉴里捡到真爱
- 《致命情谜:我在豪门渣男图鉴里捡到真爱》故事推荐在繁华喧嚣的星城,自由撰稿人女主,凭借着对真相的执着追求,一头扎进豪门女首富赵雅琴自杀疑云。......
- 6.5万字5个月前
- 长空霁阳
- 邓放✘程霁阳
- 6.4万字3个月前
- 罪爱迷局
- 简介正在更新
- 2.1万字2个月前
- 二分差
- [竹马+死对头]全能学神鹿亦珩×美术音律高手陈燃#进展快#双向奔赴#无障碍恋爱
- 6.0万字2个月前
- 生逢
- 0.6万字2个月前
- 锦锋侧颜,吴涛心底的月光
- 当十七岁的吴涛在美术教室的阴影里第一次看见锦锋低头画画的模样,他还不知道,那个被阳光斜切一半的侧脸,会成为他此后无数个夜晚辗转反侧的隐秘坐标......
- 6.7万字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