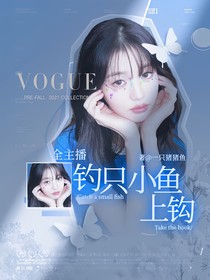无题
转眼又是一年冬,老街的雪比去年来得更缠绵些。苏然和白羽搬进了工棚旁的小阁楼,是老木匠退休后腾出来的,木窗棂歪得比从前更厉害,却总能在清晨接住第一缕阳光。
白羽把画室挪到了阁楼的向阳面,画架旁摆着苏然新做的歪木架,三层隔板都顺着木料的弧度歪着,最上层刚好能放下那方青石板章,中层托着那只歪笔搁,最下层的歪缝里,斜插着她画“歪处的牵挂”时用的铅笔。
“你看这雪,”白羽推开窗,伸手接住片飘落的雪花,“落在歪窗台上都比别处厚些,像特意给窗台织了条白围巾。”
苏然正蹲在地板上摆弄相机,镜头对着窗台上的歪陶罐——那是他们上次去山货市集淘来的,罐口歪得厉害,却刚好能插进一束干芦花。“刚发现去年那张‘刚好的歪’,雪花的纹路和今年的重合了两处,”他抬头时,睫毛上沾了点从窗外飘进来的雪沫,“老相机的镜头有点歪,倒把雪拍得像星星。”
白羽忽然想起什么,转身从画夹里抽出张纸,是幅水彩:歪窗台上的歪陶罐插着芦花,罐口的积雪把歪处填成了圆,窗玻璃上的冰花歪歪扭扭,刚好框住远处歪烟囱的顶。画的右下角,盖着两个并排的印——“然”字石章的蝴蝶翅膀,正挨着“羽”字木章的云纹,朱砂在雪色里红得格外暖。
“给阁楼的第一张画,”她把画贴在墙上的歪钉子上,纸张的边缘刚好和墙缝对齐,“就叫‘歪处的温度’吧。”
那天傍晚,雪下得紧了。他们窝在阁楼的旧沙发里,苏然翻着相机里的照片,白羽则用那方青石板章在信封上盖印。信封是给老街的孩子们准备的,里面装着他们画的歪动物明信片。
“你看这只歪耳朵兔子,”苏然指着屏幕,“上次教孩子们刻木牌,有个小姑娘把兔子耳朵刻歪了,哭着说不像,你当时怎么说来着?”
“我说歪耳朵才好呢,”白羽盖完最后一个印,指尖沾着点朱砂,“风能从耳朵缝里钻进去,兔子就能听见更远的故事。”她忽然倾身靠近,用沾着朱砂的指尖在他手背上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小太阳,“就像我们,歪处越多,越能接住彼此的光。”
苏然握住她的手,朱砂印在两人手背上晕开,像朵悄悄绽放的花。他忽然起身,从相机包最底层翻出个小盒子——里面是枚歪形的银吊坠,模样和当初那个笔搁上的麻雀一模一样,翅膀的歪处镶着颗小小的珍珠,是他攒了半年的工钱,请老银匠一点点嵌进去的。
“去年送你的是戴在手上的牵挂,”他把吊坠挂在她颈间,珍珠贴着她的锁骨,暖得像粒会呼吸的星子,“这个是藏在心里的。”
白羽低头摸着吊坠,麻雀的歪爪子刚好勾住银链,晃了晃,像要飞起来。雪光从歪窗照进来,落在她眼里,也落在他手背上那枚朱砂小太阳上,两个歪歪扭扭的暖,在昏黄的灯光里连成了片。
深夜时,雪停了。苏然被窗棂的咯吱声惊醒,看见白羽正趴在窗边,颈间的银吊坠在月光下闪着微光。“你看,”她回头朝他笑,“歪屋顶的雪滑下来,刚好堆在歪门槛前,像给我们的阁楼铺了条白地毯。”
他走过去,从背后轻轻抱住她。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被歪窗的格子切得七零八落,却紧紧依偎着,像幅拼不全却格外温暖的画。
“明年开春,”苏然的下巴抵着她的发顶,闻着熟悉的薄荷香混着银饰的清冽,“我们去老木匠的工棚,把那张旧木桌修修吧,桌腿歪了半寸,刚好能垫上你上次捡的那块歪石板。”
白羽转过身,颈间的银麻雀蹭过他的脸颊,像句温柔的应答。“还要在桌角刻上日期,”她踮脚吻了吻他的唇角,朱砂的余温混着雪的清冽,“就刻在歪缝里,让日子慢慢把它磨得发亮。”
窗外的雪地上,两串歪歪扭扭的脚印从阁楼门口延伸出去,又绕了回来,像条舍不得离开的线。苏然忽然明白,所谓圆满,从来都不是规规矩矩的方或圆,而是两个愿意为彼此弯腰的人,在时光里慢慢找到的那个平衡点——像歪罐配歪盖,像歪绳系歪结,像他和她,在这老街的烟火里,把每个寻常日子,都过成了刚好的模样。
后来,苏然的“歪处的圆满”文件夹里,又多了张照片:雪夜的阁楼窗台上,歪陶罐里的芦花沾着雪,颈间的银麻雀吊坠垂在陶罐边,珍珠的光和雪光融在一起,像句没说出口的晚安。照片命名为“歪着的永远”。
躺平失败:我在综艺当显眼包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我等了你好多年(双女主)
- 曾经看着她从恋爱到失恋分手,她明明是最心疼她的可是她不能说,时隔多年再次相遇等了这么多年她终于明白她心思
- 9.5万字8个月前
- 此曲赠与君
- 我们几个朋友,相约25岁到爱海琴寻死。人年轻时候想法就是这么欠揍。可后来我们都没兑现那个约定,选择自己热爱的事业……
- 1.2万字5个月前
- 戏子不简单(又名和我的军官上司谈个恋爱)
- 小甜饼民国林倾年刚回家就被他的朋友拖去了戏园,对于台上的人一见钟情。展开追求跟解冥悠相知相爱的故事。一起成长的故事
- 0.8万字3个月前
- 全主播:钓只小鱼上钩
- ⚠️后期有真顾客+跨赛道+妹宝无限宠+1vn+ooc严重+时间线混乱+文笔差钓系甜妹主播xN位大佬级主播·修罗场+互宠日常**【阅读指南】*......
- 1.5万字2个月前
- 假千金绑定神豪系统后,全球财阀跪求我继承
- 时晚,豪门鸠占鹊巢的“假千金”,在真千金林薇薇荣归、自己尊严扫地并被逐出家门之际,意外绑定【神豪逆袭系统】。系统核心规则简单粗暴:消费、投资......
- 8.9万字2个月前
- 叶皓然:我的命中注定
- 都是白日梦,请勿上升正主
- 2.8万字4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