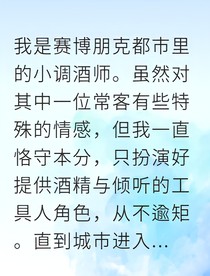无题
冬至那天,老街飘起细碎的雪,苏然和白羽踩着薄雪去给老木匠送新做的歪木勺。木勺的柄歪向右边,勺头却微微向左倾,刚好能稳稳舀起粥碗里的米。
老木匠接过木勺时,浑浊的眼睛亮了亮,用布满老茧的手摩挲着:“这弧度,是顺着你们俩的手型做的吧?”他指腹点了点勺柄的歪处,“你握勺时习惯往回收力,她却爱往外送半分,这歪处,刚好中和了。”
白羽忽然红了脸,想起每次一起吃饭,他递过来的汤勺总会不自觉往她这边歪半寸,而她接过来时,手指总会在同一处落下。原来那些没说出口的默契,早被木头悄悄记了下来。
回程时,雪下得密了些。苏然把围巾解下来,歪歪扭扭地绕在她颈间,两端故意留得不一样长,说这样风从左边钻进来,右边的布就能挡住。白羽被裹得只露双眼睛,看他睫毛上沾的雪粒,忽然伸手去接——指尖刚碰到他的睫毛,他就微微低头,让那粒雪落在她手心里,凉丝丝的,很快化成了水。
“老木匠说,”苏然牵着她的手往阁楼走,脚印在雪地里连成串歪歪扭扭的省略号,“明年开春教我们做木床,说床腿得歪三分,睡在上面才不容易落枕。”
白羽忍不住笑:“他是不是觉得所有东西都得歪着才好?”
“他说啊,”苏然停下脚步,替她拂去发梢的雪,“直来直去的物件看着规整,却经不住日子磨。反倒是这些歪处,像两个人的性子,磨着磨着就嵌在了一起,拆都拆不开。”
阁楼里的炉火正旺,歪柜上的镜匣被烤得暖烘烘的。白羽打开镜匣补口红,忽然发现铜镜里多了个影子——苏然正举着相机,镜头对着她。她刚要躲,他已经按下快门,笑着说:“这张该叫‘歪镜里的两个人’。”
夜里,他们窝在沙发上看老照片。翻到第一次一起刻笔搁的那天,白羽忽然指着照片里苏然的袖口:“你看,这里沾的木屑形状,和我今天围巾上的雪印一模一样。”苏然凑近看,果然,三年前的木屑和此刻的雪印,都是个歪歪扭扭的小爱心。
“可能从一开始,”他把她往怀里带了带,让她的头靠在自己肩上,“日子就替我们把路歪向了彼此。”
炉火“噼啪”响了一声,映得镜匣上的刻字明明灭灭。白羽忽然想起老木匠师娘的话,当年师娘总笑镜匣盖歪得不像话,却每天用它梳头发,一梳就是三十年。原来所谓长久,从不是强求规整的圆满,而是愿意在每个细节里,为对方歪一点点、让一点点,让那些不刻意的迁就,慢慢长成彼此最舒服的模样。
年初二那天,老街的孩子们来拜年,看见阁楼墙上新挂了幅画:歪镜匣摆在歪柜上,镜里映着两个交叠的影子,窗外的歪树枝探进来,刚好勾住窗台上的歪木勺。画的右下角,盖着两个并排的印,“然”字的蝴蝶翅膀,正轻轻搭在“羽”字的云纹上。
“这画叫什么呀?”有个孩子问。
苏然看了眼正在给孩子们分糖果的白羽,她无名指上的歪戒指在阳光下闪了闪,刚好和他袖口露出的歪笔搁连成线。他笑着说:“叫‘歪着的我们’。”
白羽回头时,正好对上他的目光,像那年在工棚里,他指尖碰到她铅笔的瞬间,像那年雪地里,他把歪戒指放进她手心的瞬间,像无数个藏在歪处的瞬间——不用说话,就知道彼此在哪,就知道下一步该往哪个方向歪半寸,才能稳稳接住对方递来的生活。
后来,苏然的相机里又多了许多这样的瞬间:歪木勺碰在一起的粥香,歪镜匣里交叠的晨光,歪屋檐下并排的雨伞,还有他和她,在老街的歪路上慢慢走,脚印歪歪扭扭,却始终朝着同一个方向。
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温润的歪物件,那些藏在不规整里的心意,终于在岁月里长成了最结实的模样——像歪根树紧紧抓住歪坡土,像歪石磨慢慢碾着歪粒谷,像他和她,在所有“刚好的歪”里,把日子过成了彼此最安稳的归宿。
躺平失败:我在综艺当显眼包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小豪:豪月千黎
- 小豪和原创女主(小说归小说,请勿上升真人)
- 2.0万字9个月前
- 一叶知湫:秋
- 1V1双洁叶知湫,是一个神奇的存在,成绩能够把校长气疯!茗逸一,是一个人人羡慕的存在,温柔有礼!初见就是二人互看不顺眼,心里暗骂!一次意外,......
- 1.6万字8个月前
- 浪漫为你耗尽
- 双男主/原创
- 0.7万字6个月前
- 我喜欢了很久的男孩
- 丁:“对不起”马:“都过去了,但不代表我原谅你了”丁:“别丢下我”马:“不是你先不要我的吗?”丁:“阿祺…对不起”马:
- 1.5万字5个月前
- 莳莳安安
- 原创虚构,欢迎大家交流觉得作者写得不错的点点赞点点关注如果有想看的情节可以在评论告诉作者或者私聊(联系方式在个人简介)
- 9.4万字3个月前
- 赛博酒保觉醒后我要打破世间规则
- 我是赛博朋克都市里的小调酒师。虽然对其中一位常客有些特殊的情感,但我一直恪守本分,只扮演好提供酒精与倾听的工具人角色,从不逾矩。直到城市进入......
- 1.6万字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