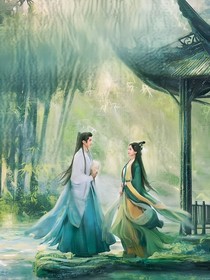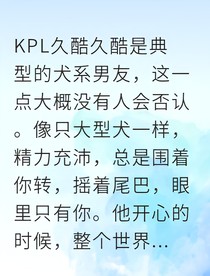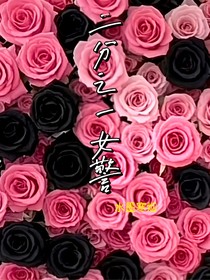无题
开春的时候,老街的歪桃树开了花,粉白的花瓣落了一地,像谁撒了把碎糖。苏然和白羽在树下搭了张旧木桌——正是去年说要修的那张,桌腿垫着白羽捡的歪石板,稳稳当当。他们要在这里办场小小的“歪物展”,邀请了老街的街坊们来看。
老木匠拄着拐杖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个布包,打开一看,是个歪形的木牌,上面刻着“歪处心安”四个字,笔画的弧度跟着木纹走,像溪水绕着石头流。“挂在桌前最合适,”他把木牌往苏然手里塞,“你们俩啊,就像这木牌,看着歪,心却齐得很。”
街坊们围着看那些歪物件:歪笔搁旁摆着歪镜匣,歪戒指和歪吊坠放在同个玻璃罐里,还有那叠印着“然”与“羽”的明信片,被风吹得轻轻晃,边角的歪痕碰在一起,像在说悄悄话。
有位老奶奶指着歪笔搁上的麻雀说:“这鸟儿歪着头,倒像是在看旁边的镜匣呢。”白羽笑着接话:“它呀,是在看镜匣里的人呢。”苏然正在给物件拍照,听见这话,镜头转过来,刚好拍下她眼里的笑,和颈间银麻雀的光。
散场后,夕阳把木桌的影子拉得歪长。他们收拾东西时,发现桌下藏着个信封,是个小姑娘留的,里面画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小人,手牵着手站在歪桃树下,旁边写着:“歪歪的人,在一起就是直直的幸福。”
白羽把信封夹进那本牛皮速写本,刚好卡在苏然画她的第一张速写旁边。“你看,”她举着本子笑,“连孩子都懂。”苏然从背后抱住她,下巴抵着她发顶,闻着桃花香混着薄荷香,像把春天揉进了怀里。
入夏时,阁楼的歪窗台上多了个新物件——是个歪口玻璃瓶,里面插着白羽种的太阳花,花茎歪歪扭扭,却硬是朝着阳光的方向长,花瓣边缘卷着点,像在歪着嘴笑。苏然给它拍了张照,存进“歪着的我们”文件夹,备注是“向光的歪”。
有天夜里下暴雨,阁楼的歪屋顶漏了点水,滴在歪木桌上,刚好积在桌角的歪缝里。白羽拿抹布去擦,却被苏然拉住:“别擦,你看这水痕的形状,像不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你捡的那片银杏叶?”白羽凑近看,还真像,歪歪的边缘,带着点自然的弧度。
他们就坐在漏雨的木桌旁,听着雨声打在歪窗上,看着那汪水痕慢慢晕开。苏然忽然说:“等雨停了,我们去河滩捡块歪石头吧,刻个‘家’字,放在门口的歪石墩上。”白羽点头,指尖在他手背上画着圈,那里还留着上次盖印时蹭的朱砂印,洗了几次都没掉,像颗长在皮肤上的痣。
雨停后,月亮从云里钻出来,照亮了河滩。他们踩着湿软的沙子往前走,脚印歪歪扭扭,很快被涨潮的水漫过,又很快生出新的。苏然捡到块青灰色的石头,边缘歪得像片荷叶,他把石头递给白羽:“你看这弧度,刚好能刻下‘家’字的最后一笔。”
白羽接过石头,指尖碰着他的,像触到了河滩的暖。她忽然想起老木匠说的“歪处的传承”,原来所谓传承,不是把物件留多久,而是把日子过成什么样——是歪笔搁接住画笔,是歪戒指贴着指腹,是两个人在歪处里,把彼此的名字,刻进“家”这个字的笔画里。
回到阁楼时,天快亮了。他们把歪石头放在门口的歪石墩上,苏然用刻刀慢慢凿“家”字,白羽举着灯照亮,灯光在石头上投下两个歪歪的影子,像在帮着扶着那笔画。刻到最后一笔时,朝阳刚好从歪窗照进来,落在“家”字的歪处,暖得像块融化的糖。
那天的照片被苏然存进新文件夹,叫“歪处是家”。照片里,歪石墩上的“家”字沾着晨露,旁边的歪木牌“歪处心安”在风里轻轻晃,而他和她的影子,正叠在石头上,把“家”字护得严严实实。
后来,老街的人总说,那对住阁楼的年轻人,把日子过成了老物件的模样——看着不规整,却越品越有味道,像歪口壶里的茶,初尝有点涩,慢慢就暖到了心里;像歪沿碗里的粥,看着稀,却稠得能粘住岁月的痕迹。
而苏然和白羽知道,那些被他们捧在手心的歪物件,那些藏在不规整里的心意,从来都不是“歪”,而是生活最本真的样子——就像老街的青石板,被踩得坑坑洼洼,却接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脚印;就像他们俩,在时光里慢慢磨出的弧度,刚好能把彼此的日子,托成最安稳的形状。
又到银杏叶落的时候,苏然举着相机,镜头里的白羽正蹲在树下捡落叶,无名指上的歪戒指,和手里的歪石头“家”字,在金叶里连成道暖线。他按下快门,这次的照片命名很简单,就叫“我们”。
躺平失败:我在综艺当显眼包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苏三:如果爱
- 温知俞v苏三(蒋子麟)“她说蒋子麟我一直都在”“他说除了你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 0.5万字6个月前
- 当戏精遇上神精
- 你说你是不是贱呢?闲得没事干非惹我,我动手了你还想要医药费,老娘一张精神报单直接拍你脸上.哈哈哈,老实了吧?老娘就凭一张精神报告单横扫天下人......
- 3.8万字3个月前
- 淮水竹亭:拯救意难平
- 意难平拯救场所阿滢:若只是牺牲我一人,换面具团全员安全,那便值得司瑶:神女本无情,可若人间值得……
- 2.3万字2个月前
- 久酷电竞男友的治愈手册
- KPL久酷久酷是典型的犬系男友,这一点大概没有人会否认。像只大型犬一样,精力充沛,总是围着你转,摇着尾巴,眼里只有你。他开心的时候,整个世界......
- 3.2万字2个月前
- 守你,一世情深
- 一场设计,让原本无交集的两个人相遇。一场得到,让原本相爱的两个人阴阳相隔。当再见面时,已成为别人的未婚妻。努力争取,想起曾经似乎回到原点。携......
- 18.1万字2个月前
- 二分之一女警
- 一场关于爱与救赎的谜局,等你入局!当开朗警花与冷酷探案人格共生,当娱乐圈甜妹恋上铁面队长,当豪门恩怨交织离奇命案,一场惊心动魄的悬疑故事就此......
- 126.5万字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