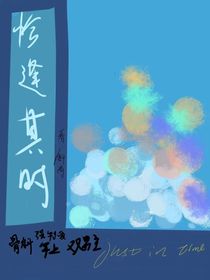无题
秋意渐浓时,老街的柿子树结了满枝歪扭的果子,红得像灯笼,却没一个长得周正。苏然搬来梯子摘柿子,白羽在树下铺了块旧布接着,布角磨破了个歪洞,偶尔有熟透的果子掉下去,刚好从洞里漏进旁边的竹筐,倒省了弯腰去捡的功夫。
他们把最红的那几个切成块,拌进糯米粉里做柿饼,模具是老木匠留下的歪木框,压出来的柿饼边缘总带着点不规则的弧度。苏然咬了一口,甜汁顺着嘴角流下来,白羽伸手去擦,指尖蹭到他的下巴,两人都笑了——她的指甲修剪得圆润,偏偏无名指上有道浅浅的月牙形疤痕,是初学刨木时不小心划的,而他的指腹上有块对应的茧,是总替她扶着木料磨出来的。
“你看,连疤痕都在凑对。”苏然捉住她的手,贴在自己手心里晃了晃,银镯子滑到手腕,撞在他的手表链上,发出清脆的响。
入冬后下了场雪,工棚的屋顶积了层白,歪烟囱里冒出的烟都是斜的。他们在工棚生了火,把那对歪木盘找出来,盛上温好的米酒,酒液晃悠着,刚好不洒出歪沿。老木匠留下的铜锁在门上来回晃,锁孔里积了点雪,阳光一照,像撒了把碎钻。
白羽忽然想起什么,起身从阁楼抱来个木箱,里面是他们这几年攒下的“歪物件”:歪沿的粗陶碗、缺角的木棋盘、断了根齿的木梳——哦,那是后来不小心摔的,苏然愣是找了块同色的木料,补了个歪歪扭扭的小牙,反倒比原来更顺手了。
“明年开春,咱们把这些修修,摆个小架子吧。”白羽摸着那个补过的木梳,“就叫‘歪物记’,怎么样?”
苏然正用歪笔在宣纸上写“冬暖”,笔尖歪了,笔画却格外有力:“好啊,再把老木匠的铜锁挂在最上头,当招牌。”
雪停时,他们并肩坐在歪门槛上,看巷子里的孩子追着歪脖子狗跑。苏然的相机镜头对着漫天飞絮,白羽的发梢沾了点雪,他伸手去拂,却被她按住手——她把脸颊贴在他手背上,冰凉的雪粒化在皮肤间,倒生出点暖来。
“你说,咱们算不算把日子过成了老木匠说的样子?”她轻声问。
苏然低头,吻了吻她发顶的雪:“你看这雪,落在歪屋顶上没滑下去,落在歪陶罐里没流走,落在咱们俩中间……”他顿了顿,指尖划过她腕上的银镯子,“刚好把缝隙都填满了。”
那天晚上,苏然整理照片,在“歪处的圆满”文件夹里新建了个子文件夹,命名为“雪落时”。里面存着三张照片:一张是歪烟囱的斜烟映着雪,一张是木箱里的歪物件被月光照得发亮,还有一张是他偷拍的——白羽坐在雪地里,手里攥着半块柿饼,嘴角沾着糖霜,眼睛弯得像她腕上的银镯子,而她身后的歪门虚掩着,铜锁在风里轻轻晃,像在替他应和那句没说出口的话。
日子就这么在歪歪扭扭里淌着,春有新绿爬满歪墙,夏有蝉鸣藏在歪树,秋有落叶堆在歪阶,冬有白雪盖着歪檐。后来老街翻修,有人劝他们换个周正的门,苏然却把那扇歪门拆下来,重新刷了漆,又装了回去。
“换了就接不住铜锁了。”他笑着说,手里正给白羽新做的歪木簪抛光,簪头刻了朵歪瓣的花,刚好能卡在她耳后。
白羽在旁边纳鞋底,针脚歪歪扭扭,却格外结实:“可不是嘛,就像这鞋底,针脚歪了才合脚,日子不也这样?”
夕阳透过歪窗斜斜照进来,落在他们交叠的手上。她的银镯子和他的歪戒指碰在一起,木簪的影子投在布上,像朵永远不会谢的花。苏然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林薇站在巷口的样子,那时的风里都是紧绷的执念,而此刻的风里,只有晒透的棉布香,和彼此呼吸交缠的暖。
他拿起相机,对着窗台上并排摆着的歪木梳和歪笔搁按下快门。照片里,阳光把它们的影子拧成一团,分不清哪段是梳齿,哪段是笔搁的雀尾,像极了他和她——从来不是规规矩矩的形状,却在所有歪处都找到了恰好的牵连,把日子过成了只有彼此才懂的圆满。
这张照片,他存进了“当下”文件夹,没设密码。因为他知道,最好的时光,从不需要锁着。
躺平失败:我在综艺当显眼包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恰逢其时(1)
- 双男(把时间线改了一下把哥哥的年龄调高了,改了哥哥名字。如果讨厌年龄偏高的会突然变成下勿看。这是双强文)
- 0.4万字9个月前
- 预谋邂逅bq
- “帅哥,我喜欢你!”“我叫什么你知道吗?”“……帅哥,我都在宿舍楼下等你这么多回了,我们真的不能加个vx吗?”“你今天是第一次在宿舍楼下见到......
- 0.7万字9个月前
- 盛在星语里
- 0.1万字9个月前
- 苏小姐独美
- 和渣男分手,拿了七千万分手费,走向人生巅峰
- 2.7万字8个月前
- 我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 屌丝男主
- 1.3万字2个月前
- 酒吧中的救赎
- 在酒吧,陆绍辰遇到了江明,从此,两人的世界多了一束光。他们互相救赎,不顾世俗的眼光,不顾他人的言语,做自己。
- 0.3万字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