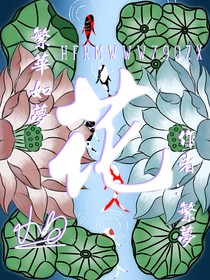第七十六章:教堂
卡车在暮色里颠簸着驶离里昂,轮胎碾过碎石路的声响里,望岁已经抱着那幅画在后座睡熟了。他的小手还攥着半块碎玻璃,月光透过车窗照在上面,折射出细碎的光斑,落在祁岁的手腕上,像极了当年马赛港那枚擦过他耳朵的子弹留下的灼痕。
祁岁低头看着那片光,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画框边缘。望岁画里的狐狸尾巴还沾着金粉,混着白日里晕开的颜料渍,倒真像辞年说的,炸开时会像向日葵。他忽然想起仓库坍塌的瞬间,辞年拽着他往外跑,那人掌心的茧擦过他虎口的旧伤——那是五年前在马赛港,为了抢一把能劈开仓库锁链的斧头,被铁屑嵌进皮肉里留下的。当时辞年蹲在码头的污水里,用牙齿咬着布条给他止血,血腥味混着海水的咸,像条滑腻的蛇钻进喉咙。
“在想什么?”辞年的声音从驾驶座传来,带着点漫不经心。他腾出一只手,越过副驾的靠背,指尖精准地落在祁岁后颈的疤上。那是三年前在柏林,为了护着发烧的望岁,被流弹擦伤的,当时血顺着衣领往下淌,染红了望岁裹着的大衣,辞年后来用刺刀把弹头从墙里剜出来时,说那形状像颗没长熟的向日葵籽。
祁岁偏头躲开他的手,抓起望安掉在地上的铁皮罐,罐底的铁钉晃出细碎的响。“在想老布朗说的发光花。”他把罐口对着月光,看那些磨尖的铁钉在阴影里泛着冷光,“望岁说要种在院子里,你信吗?”
辞年突然笑了,笑声撞在车厢板上,弹回来时带着点回音。“十五年前你说能靠一把撬棍抢银行,我也信了。”他打了把方向盘,卡车拐进条更窄的路,两侧的白桦树影像伸来的手,“结果你把炸药埋在银行后门的花坛里,说要给那些资本家的玫瑰浇点‘营养液’。”
祁岁的指尖在铁皮罐上划了道痕,声音低了些:“那次你差点被炸掉半条腿。”
“是你背着我跑了三条街。”辞年的拇指按在方向盘的磨损处,那里有个浅浅的牙印,是当年在柏林,望岁换牙时咬的,“子弹嵌在砖缝里,你非要抠出来当纪念品,说能给望安做弹弓的石子。”
后座的望安突然翻了个身,嘴里嘟囔着“向日葵”。祁岁回头时,看见他怀里的岁安正用尾巴扫着那幅画,金粉落在望安的睫毛上,像撒了把碎星。这只狐狸的耳朵尖还沾着仓库里的烟灰,却把下巴搁在望安的手背上,喉咙里发出轻轻的呼噜声——和五年前在红海的救生艇上一样,那时它也是这样护着两个发着高烧的人,自己舔着爪子上的伤口,血珠滴在船板上,晕成小小的红梅花。
“老布朗的牡蛎壳粉还剩多少?”祁岁突然问,指尖捻起一点画框上的金粉,“望岁说要给岁安的尾巴上撒点,这样晚上走路就不会被石头绊倒。”
“够撒到下一个镇子。”辞年从储物格里摸出个铁皮盒,扔给祁岁,“老布朗塞给我的,说混着煤油能当信号弹。他还说,当年在北非,他就是靠这个在沙漠里招来了商队。”
祁岁打开盒子时,一股咸腥味涌出来,混着颜料的松节油味,像回到了马赛港的鱼市。他想起那时辞年总爱偷摊主的牡蛎,撬开壳把肉塞进他嘴里,自己嚼着壳上的碎肉,说这样能补钙,免得下次背他跑路时腿软。有次被摊主追着打,辞年拽着他躲进货箱,两人在腥臭的海带堆里滚成一团,那人的血顺着额角往下淌,滴在他手背上,像颗温热的朱砂痣。
“前面有座桥。”辞年突然减速,车灯扫过桥面的木板,露出几个松动的缝隙,“图纸上说下面有暗流,当年雷蒙德的人在这里沉过货。”
祁岁探头望去,桥栏上缠着圈生锈的铁丝,和报亭门轴上的手法一模一样。他认得那铁丝的型号——是军用的,能承受三个人的重量,当年在柏林的废弃工厂,他们就是用这种铁丝把追兵吊在房梁上,看着那些人在月光里挣扎,像串挂起来的腊肉。
“望岁的帆布包呢?”祁岁突然摸向座位底下,触到个硬邦邦的东西,是那把刻着蛇的匕首。刀鞘上的乳牙还在,被望岁用红绳缠着,晃出细碎的响,“雷管别让望安摸到,那孩子总爱学你用牙齿咬引线。”
“在我脚边。”辞年踢了踢旁边的包,拉链上的银链叮当作响,“早上检查过,引线都换成了慢燃型的,烧完足够我们跑过三座桥。”他顿了顿,突然笑出声,“就像十五年前在马赛港,你算准了引线长度,让我有时间把追债人的车胎扎破。”
祁岁没接话,只是把匕首塞回包里。他想起那时辞年蹲在码头的阴影里,用牙齿咬着雷管的引线,火星在他唇间明灭,像只停在嘴边的萤火虫。后来爆炸声响起来时,那人正背着他往货轮上爬,子弹擦着耳朵飞过去,他却笑着说:“看,比烟花好看吧?”
卡车驶过桥面时,木板发出嘎吱的呻吟。祁岁看见桥下的水面泛着银光,像铺了层碎玻璃——和望岁捡的那块很像。他突然想起望岁说的“能照出坏人影子”,低头时,果然看见自己的倒影里,手腕上的疤正随着动作扭动,像条苏醒的蛇。
“前面有座教堂。”辞年的声音里带着点异样,“钟楼的形状和里昂的很像,只是尖顶上没有避雷针。”
祁岁抬头望去,教堂的尖顶在月光里泛着冷光,像把插在地上的匕首。他认得那建筑风格——是二战时德军建的瞭望塔,后来改成了教堂,地下室的结构和柏林的废弃工厂一模一样,有三条通道,其中一条直通后山的军火库。老布朗的侄子喝醉时说过,那里的保险柜还锁着当年没运走的金条,钥匙孔是用狐狸形状的模具做的,只有特定的钥匙才能打开。
“望岁的蜡笔还有红色吗?”祁岁突然问,指尖在画框上敲出节奏,“教堂的门牌号要是涂上红漆,会像块新鲜的肉。”
“够画满三个门牌。”辞年从口袋里摸出那支缠着银链的红蜡笔,笔杆上沾着点暗红色的粉,“望岁说要在门把手上画朵花,像老布朗种的向日葵。”
祁岁接过蜡笔时,指尖触到笔杆上的刻痕——是望岁用牙齿咬的,深浅不一,像串歪歪扭扭的密码。他想起昨夜这孩子趴在他膝盖上,用这支笔在他手背上画狐狸,说要给狐狸画上刀枪不入的鳞片,那时辞年正坐在旁边擦枪,枪管的反光落在望岁的睫毛上,像镀了层银。
“停车。”祁岁突然开口,指着教堂侧面的矮墙,“那里有个通风口,尺寸刚好能钻进去一个人。”
辞年把车停在树影里,望安和望岁还在睡,岁安却突然竖起耳朵,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咽。祁岁摸了摸狐狸的头,发现它的爪子正在发抖——和三年前在柏林的地下室一样,那时外面传来德军的皮靴声,这只狐狸也是这样,把鼻子埋在望岁的颈窝里,尾巴紧紧缠着望安的脚踝。
“我去看看。”祁岁推开车门时,辞年突然抓住他的手腕。那人的掌心很热,攥着他虎口的旧伤,像要把那道疤揉进自己的肉里。
“带这个。”辞年把那支红蜡笔塞进他手里,银链缠上他的手指,“望岁说这个能驱邪,比你当年在马赛港带的十字架管用。”
祁岁没说话,只是把蜡笔别在衬衫口袋里。他弯腰时,看见自己后腰的伤正透过布料隐隐作痛——那是去年在纽约码头,被雷蒙德的人用钢管打的,当时辞年抱着他滚进货堆,自己后背撞在铁架上,肋骨断了三根,却还笑着说:“这下我们都有新疤了,像对双胞胎。”
通风口比想象中窄,祁岁爬进去时,衬衫被铁皮划破,露出后背的旧伤。那些疤痕纵横交错,像张摊开的地图,标注着十五年的逃亡路。他想起辞年总爱用指尖沿着那些疤痕游走,说像在走迷宫,每次走到终点——也就是心脏的位置时,那人的呼吸就会变得很重,像头蓄势待发的兽。
通道里弥漫着灰尘和霉味,混着点淡淡的汽油味。祁岁掏出打火机,火苗窜起的瞬间,他看见墙壁上有串新鲜的脚印,鞋跟处有个三角形的缺口——是雷蒙德的人,他认得这种军靴,当年在红海货轮上,就是这种靴子踩断了望岁的蜡笔,那支红色的,望岁说要画狐狸眼睛的。
前面突然传来滴水声,很规律,像秒表在倒数。祁岁放慢脚步,看见通道尽头有扇铁门,锁孔上缠着圈铁丝,和桥上的一模一样。他从口袋里摸出那支红蜡笔,按照老布朗教的手法,把笔尖插进锁孔,轻轻一转——咔哒一声,锁开了,像十五年前在马赛港,他用一根发夹打开了追债人的保险柜。
铁门后是间密室,中央摆着个铁柜,柜门上的狐狸锁扣正闪着银光。祁岁走过去时,发现锁扣上缠着根银链,和望岁蜡笔上的一模一样。他突然想起望岁说的“给狐狸戴护身符”,指尖抚过锁扣上的刻痕,那是只尾巴着火的狐狸,眼睛是两颗红色的宝石,像极了望岁画里的样子。
“找到了。”祁岁对着藏在衣领里的对讲机说,指尖扣住锁扣,“狐狸的眼睛是红宝石,老布朗没骗我们。”
“别碰那些宝石。”辞年的声音带着点急,“雷蒙德的人在上面涂了磷粉,沾到皮肤上会发光,三天都洗不掉。”他顿了顿,语气软下来,“就像当年在柏林,你为了给望岁找退烧药,闯进德军的药房,回来时衣服上全是荧光粉,在黑夜里像只萤火虫。”
祁岁缩回手,从口袋里摸出块碎布——是望安的手帕,上面沾着向日葵的露水。他隔着布打开铁柜,里面果然堆满了金条,金条上印着狐狸的图案,眼睛处嵌着红色的宝石,在月光下泛着诡异的光。
“还有雷管吗?”祁岁突然问,指尖敲了敲金条,“老布朗说要炸掉这里,免得被其他人找到。”
“望岁的帆布包里有两捆。”辞年的声音里带着笑意,“那孩子非要在引线末端系上向日葵花瓣,说这样爆炸时会有花香。”
祁岁把雷管摆在铁柜周围,引线像条红色的蛇,蜿蜒着通向通风口。他摆到最后一根时,发现引线不够长了,还差一小截。正皱眉时,他摸到衬衫口袋里的红蜡笔,突然想起望岁说的“红色能让狐狸刀枪不入”,于是把蜡笔掰断,用融化的蜡把两段引线粘在一起,像十五年前在马赛港,他用口香糖粘住了炸断的引线。
“好了。”祁岁退到通风口,回头望了眼那堆金条,“狐狸该回家了。”
他爬出通道时,看见辞年正站在教堂门口,怀里抱着醒来的望岁,望安牵着岁安,手里举着那幅画。月光落在他们身上,像层金色的纱,把四个人一只狐狸的影子拉得很长,缠在一起,像个永远解不开的结。
“引线烧得快吗?”望岁揉着眼睛问,手指指向教堂的尖顶,“会像向日葵开花吗?”
“比向日葵还好看。”辞年把望岁举起来,让他骑在自己肩上,“会像你画的狐狸尾巴,拖着金粉飞上天。”
祁岁走过去时,辞年突然抓住他的手,把一枚东西塞进他掌心。是颗红宝石,从狐狸锁扣上掰下来的,沾着点磷粉,在夜色里泛着微光。“望岁说要给你当护身符。”辞年的拇指擦过他掌心的疤,“说这样坏人就找不到你了。”
远处突然传来爆炸声,很闷,像闷雷滚过天际。祁岁回头望去,教堂的尖顶正在火光里摇晃,那些红色的宝石随着爆炸飞向空中,像无数只狐狸的眼睛,在夜色里眨了眨,然后消失不见。
“回家了。”辞年拽着他往卡车走,望岁在他肩上欢呼,望安举着那幅画跟着跑,岁安的尾巴扫过他们的脚踝,金粉簌簌往下掉,“老布朗说下一个镇子有片向日葵花田,望岁可以种他的发光瓜子了。”
祁岁低头看着掌心的红宝石,磷粉的光映在他眼里,像两簇跳动的火苗。他想起十五年前在马赛港,辞年也是这样把一枚弹壳塞进他手里,说:“等我们找到安稳的地方,就用这个给望岁做个哨子。”那时那人的血正滴在弹壳上,晕开朵小小的红梅花,像极了此刻掌心里的光。
卡车重新启动时,望岁突然指着窗外喊:“看!狐狸在飞!”
祁岁探头望去,夜空中飘着无数金粉,随着风飞向远方,像只只尾巴着火的狐狸。他突然想起望岁画里的最后一笔——两只狐狸的尾巴缠在一起,在洒满金光的路上走着,永远不会分开。
“它们回家了。”祁岁轻声说,指尖握紧那枚红宝石,磷粉的光透过皮肤渗进去,像要在肉里开出花来。
辞年的手突然覆上来,握住他的。两人的疤痕在夜色里相触,像两块拼图终于找到彼此的位置。“我们也回家了。”辞年的声音很低,呼吸扫过他的耳垂,“回那个有向日葵、有星星、有我们的家。”
卡车驶进晨曦时,祁岁看见望岁画里的路正在前方展开,金色的,铺着向日葵的花瓣。岁安突然从望安怀里跳起来,扒着车窗往外看,尾巴上的金粉落在祁岁的手背上,像颗永远不会熄灭的星。
楼影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蘤
- 本片之前的名字《花》但由于一直打不出来,所以已《蘤》命名本篇文章是以一个穿梭在多重空间里的组织这个组织坐落在一道空间裂缝里名叫溟翼的神秘组织......
- 1.5万字8个月前
- 龙拳3:龙拳小子
- 【跆拳道运动员竞技+男暗恋女+团宠+无脑洞+慢节奏+宠妹+师父+教练+男强+无绿茶】 『受宠公主vs偏执傲娇跆拳道大佬』有成长是甜文女主视......
- 20.7万字6个月前
- 白痴我在结界当猎人
- 弑神,一切都是喜剧,世界永远也跳不出被控制的命运,我们都是演员。都是表演者,都是为了取悦他人,取悦那个控制我们的人
- 0.7万字4个月前
- 原来你是审判官?
- 正义,智慧,和平,战争。四大界地明争暗斗,最后赢家是谁?在这个时代,人民才是主导。推翻不义,推翻非现实统治!这是个和平年代,可天下分久必合合......
- 18.0万字3个月前
- 月绵
- 麓夜绵,皇城弃女,身负神血,手持轮回笔与清心铃,却不知自己正是三界动荡的钥匙。
- 4.5万字3个月前
- 盗笔综合
- 小哥吴邪他们从西王母宫回来后的一些事情。
- 0.1万字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