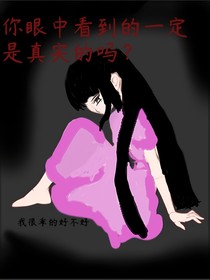第十九章 皮箱里的药香
整理爷爷的旧物花了整整三天。
陈默把木盒里的信纸按日期排好时,午后的阳光正斜斜地穿过纱窗,在地板上投下格子状的光斑。最底下那封没有信封的信纸上,钢笔字迹洇了水,“忠伯”两个字晕成了模糊的墨团,倒像是一滴凝固的泪。
“这箱子要不要扔?”姑姑抱着个褪色的皮箱从储藏室出来,箱子边角的皮革裂了缝,铜锁上长着层青绿色的锈,“你爷爷总说这是他行医时用的,我看里面除了些旧纱布,也没啥值钱东西。”
陈默接过皮箱,入手比想象中沉。他把箱子放在客厅中央,蹲下身去抠那把铜锁——锁孔里卡着些灰尘,用指甲剔了半天,“咔哒”一声轻响,锁舌弹了出来。
一股淡淡的药味混着皮革的气息涌出来,像忽然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门。箱子里铺着块深蓝色的粗布,上面摆着个锡制药罐,罐口缠着圈红绳,和守井人药箱上的那根一模一样。
“这药罐……”陈默的指尖刚碰到罐身,忽然顿住了。罐底刻着个极小的“禾”字,刻痕里嵌着些深褐色的东西,像是长年累月熬药留下的药垢。
姑姑凑过来看了一眼,忽然“呀”了一声:“这不是阿禾姑娘的药罐吗?当年她总来借这个罐子熬药,说锡罐熬出来的药不苦。后来她没了,你爷爷说啥也不肯扔,说等忠伯回来还给他。”
陈默的心轻轻晃了一下。他想起阿禾指甲缝里的粗布碎片,想起守井人药箱里那包没来得及用的草药,原来这些散落的碎片,早就在时光里织成了一张无形的网,把所有人都连在了一起。
箱子底层压着件叠得整齐的粗布褂子,袖口磨得发亮,胸口位置有块暗褐色的污渍,洗了很多遍也没洗掉。陈默把褂子展开,发现内衬缝着个小口袋,里面掉出半块青石板——不是他裤兜里那块刻着笑脸的,这半块上面刻着个“忠”字,边缘的断裂处和他那块严丝合缝。
“原来两块石板是一对。”姑姑的声音有些发颤,她指着“忠”字旁边的小缺口,“这是当年你爷爷跟忠伯打赌输了,用凿子敲掉的角,说等忠伯守满三生,就把这半块还给他。”
陈默把两块石板拼在一起,“忠”字旁边的笑脸刚好对着缺口,像个人在笑着点头。他忽然明白守井人为什么要把半块石板留给自己,那不是告别,是托付,是把跨越了三生的约定,交到了他的手上。
皮箱的夹层里还藏着本更旧的册子,纸页黄得像秋叶,封面上写着“杏林杂记”。翻开第一页,是爷爷年轻时的字迹,记录着各种草药的习性,翻到中间忽然出现一行不同的笔迹,力道很重,像是用炭笔写的:“三月初三,阿禾咳血,需取井台边的紫花地丁入药。”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是爷爷补上去的:“忠伯切记,地丁要带露采,沾了井水便无效。”
陈默的指尖抚过那行字,纸页上仿佛还留着炭笔划过的温度。他想起守井人背着药箱走过巷口的身影,想起阿禾站在井边等药的模样,原来那些被岁月掩埋的日常,藏着这么多温柔的牵挂。
“你爷爷总说,医者医病,难医人心,”姑姑坐在他身边,拿起那本杂记翻了翻,“当年忠伯非要守井,你爷爷劝了他三天三夜,最后没办法,把这箱子交给他,说啥时候想通了就回来。结果这一等,就是一辈子。”
窗外的阳光慢慢移到茶几上,照在那对拼合的青石板上,反射出淡淡的光。陈默忽然想把石板送回井边,让它们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就像那些埋在井边的往事,终究要在故土里才能安息。
他把青石板小心翼翼地放回粗布褂子的口袋,再把褂子叠好放进皮箱。锡罐里的药味越来越淡,混着午后的阳光,变成一种暖暖的香气。陈默知道,这香气里藏着的,是爷爷的遗憾,是忠伯的坚守,是阿禾没说出口的等待。
“姑姑,明天我想回趟镇子。”
姑姑抬头看了他一眼,眼里没有惊讶,只有了然的温柔:“去吧,把石板还给忠伯。你爷爷在天上看着呢,肯定盼着这一天。”
暮色漫进窗户时,陈默把皮箱锁好,放回储藏室。转身的瞬间,他好像听见箱子里传来轻微的碰撞声,像两块青石板在互相问候,又像谁在轻轻说“谢谢”。
客厅的灯亮了,姑姑端着刚炒好的青菜从厨房出来,围裙上沾着点点油星。陈默看着她手腕上已经换过新药的纱布,忽然觉得那些沉甸甸的往事,好像都变成了餐桌上的烟火气,暖烘烘的,让人心里踏实。
他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车水马龙。远处的霓虹灯次第亮起,像撒在地上的星星,却没有镇子老槐树下的路灯那么温柔。陈默摸了摸裤兜里的青石板碎片,忽然开始期待明天的旅程——不是为了探寻什么秘密,只是想把属于那里的东西,好好送回去。
夜色渐深,城市的喧嚣慢慢沉了下去。陈默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偶尔驶过的汽车声,想起守井人坐在井边哼的小调,想起阿禾井边的歌声,那些调子混在一起,像一首温柔的安眠曲。
他知道,明天的太阳升起时,又会是新的开始。而那些藏在皮箱里的药香,会像个沉默的约定,陪着他,慢慢走完剩下的路。
槐下红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双与云予
- 简介正在更新,正文先不写,以一人视角展开。正文沒多少思路了,先看一些作文或日记更好了解人物性格。有空写,本文算双女主,可能是be结局。
- 0.6万字6个月前
- 西伯利亚战俘营的典狱长
- 我穿越了,我来到了西伯利亚战俘营当监狱长。我做出的事情会让整个世界都在颤抖。我不停的壮大自己,我还要支援东方大国。我会将鹰酱国拉下神坛,成为......
- 4.5万字6个月前
- 汴京诡影录
- 北宋汴京,繁华之下命案突起。开封府尹包拯抽丝剥茧,从客栈离奇死亡的富商,到神秘的黑蝙蝠帮,追寻真相之路危机四伏。密道逃生、山谷激战、洞穴探秘......
- 6.6万字4个月前
- 谜案欲解
- 这篇确切来说应该是《步步入谜局》的上一番,大家顺序不要搞反哦~
- 0.7万字2个月前
- 你眼中看到的一定是真实的吗?
- 女主:王雨儿我眼中一片黑暗,听到的只有他们对我说的“莫回头”可是...我也怕它们呀本文是一个大女主,并无男主(禁止抄袭哦)
- 0.5万字2个月前
- 九门之厨神
- 怒刷四个诡异世界,省吃俭用,终于存够30万积分,兑换心仪已久的老九门旅游。什么脚踩张启山,怒压老九门,什么成为老九门白月光,陈皮的好朋友……......
- 2.9万字2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