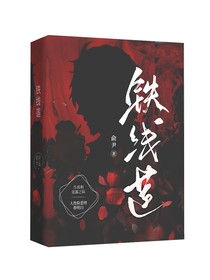钟声缺席之后
(顾生·续章)
塌陷的零点
雨在凌晨两点十七分突然收声,像被谁拧断了脖子。雾隐镇最大的铜钟悬在钟楼顶端,本该报时的“当”却哑成了空洞的“嗡”。嗡声里,顾生踩着邮差靴,靴跟钉着铜片,一步一响,从钟楼阴影里走出来。制服袖口磨得发白,编号“000”在雨里发亮,像一枚未点燃的灯芯。
失声的重量
顾生抬手,掌心托着一只黑胶唱盘。盘面无纹,却倒映出钟楼的影子——影子在唱盘里缓缓转动,时针倒走,分针逆行,秒针折成三段。第一段“咚”落在井底;第二段“当”钻进齿轮;第三段“叮”被风卷走。钟声的三段残音,成了今夜的谜面。
第三个见证者
街口,沈杳撑一柄旧油纸伞,伞骨是图书馆废弃的索引条,雨水沿索引滴落,在她脚边排成一排倒立的字:“缺席”。她穿墨绿旗袍,领口别着铜铃扣,短发被雨压出温柔的弧度。怀里抱着一本空白借阅卡,卡上只有一行预印日期:1975.7.19。她抬眼,看见顾生,像看见一封迟到多年的信。
井的第三重倒影
三人聚在第三口井旁。井口覆着一层薄光,像一面未干的镜子。顾生把黑胶唱盘平放在井沿,唱盘立刻融成一滩墨色的水,水里浮出钟楼的倒影——倒影里的钟舌缺了一截,像被谁剪掉的尾音。沈杳俯身,指尖探入墨色,倒影立刻爬上她的皮肤,在她腕内侧凝成一枚细小的铜钥匙,钥匙齿尚未开锋,却带着心跳的温度。
倒走的阶梯
井水开始上升,却不是水,而是一页页折叠的日历。日历上印着同一天:1975年7月19日,署名栏却空白。日历自动展开,变成一条向下的阶梯,阶梯由未干的墨迹砌成,踩上去会留下脚印,脚印立刻被雨稀释。顾生走在最前,邮差哨子挂在颈侧,每一步都吹出一声极轻的哨音,哨音像在给倒走的钟声指路。
地下室的留声机
阶梯尽头是一间圆形地下室,直径十米,天花板由倒立的钟声构成,每走一秒,钟声便倒着响一次。地下室中央,摆着一架巨大的留声机,留声机没有唱盘,只有一张未干的纸。纸面写着:“第二十五章 钟声缺席之后——请在此处写下尚未被命名的呼吸。”纸的右下角,盖着一枚邮戳:“寄往1975年7月19日”。留声机的唱臂由铜铃碎片拼成,唱针是一缕尚未燃尽的晨雾。
呼吸的缺口
顾生把邮差哨子放在纸上,哨子立刻生根,长出细小的铜芽。铜芽穿过他的掌心,沿着血管游走,最终在腕间齿轮刺青处停下。刺青发出细微的青光,像一盏被调暗的灯。沈杳把空白借阅卡放在纸上,卡片立刻生根,长出细小的纸芽,纸芽指向留声机的底座。底座上,嵌着一枚未开齿的铜钥匙,钥匙柄上刻着一行小字:“请在此处写下尚未被命名的呼吸。”
合唱的裂缝
留声机开始旋转,唱针落在纸上,发出第一声低音:咚——低音拖长,拖过整个地下室,拖过整个镇子,拖过整个1975年7月19日。低音所到之处,钟声开始倒着走,行人开始倒着走,日历开始倒着翻。倒走的钟声里,沈杳看见十年前的自己:她站在图书馆门口,怀里抱着一本空白的借阅卡,卡上写着:“沈杳,夜班管理员,失踪于1975年7月19日凌晨三点十七分。”她伸手,想抓住十年前的自己,却只抓住一缕风。
高音的裂缝
低音拖到极致,忽然拔高,变成一声清澈的高音:叮——高音不是结束,而是开始。高音所到之处,所有意象开始合唱:井口唱“咚”,钟楼唱“当”,喷泉唱“哗”,图书馆唱“沙”,编辑部唱“嗒”,第零页唱“嗡”,铜铃唱“铃”,齿轮唱“咔”,青草唱“呼”,空白唱“嘘”,风唱“风”。合唱汇成一句完整的句子:“第二十五章 钟声缺席之后——钟声已响,故事继续。”
折叠的尾声
合唱结束,地下室开始折叠。折叠的方式像纸飞机被重新展平:屋顶回到屋顶,街道回到街道,行人回到行人,影子回到影子。折叠到最后,整座地下室化作一张薄薄的乐谱,乐谱上只有一行字:“第二十六章 雨夜折叠”。乐谱飘向天空,飘向井底,飘向黑胶唱片,飘向尚未被写出的下一章。乐谱飘到之处,留下一行行空白,空白里回荡着钟声的余韵:咚——咚——咚——余韵未散,钟声继续,故事继续。
-------------------------------------------------------------------------------------
作者:又一篇存稿光荣牺牲
作者:~
寻找它的真相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