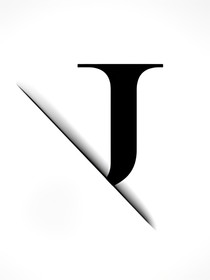第十四章:雨渍里的未寄地址
雨丝斜斜切过街角时,林小满正蹲在邮简旁数第三十七道锈痕。铁皮表面凹下去一小块,像被谁的指节反复碾过,积着的雨水里浮着半片枯黄的银杏叶,是上周秋意提前溜走时落下的。
“又来啦?”老陈的修鞋摊支着蓝白条纹的雨棚,锤钉子的声音混在雨声里闷钝发沉,“这邮简比我儿子岁数都大,早该拆了。”
林小满没抬头,指尖蘸了点雨水,在邮简底座的水泥台上画圈。她总觉得这铁皮箱子在呼吸,尤其雨夜,能听见里面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像谁在低声念信。
昨天傍晚收信时,她摸到最底下压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邮票,没有地址,只在封口处画了朵歪歪扭扭的玉兰花。拆开时掉出半张褪色的照片,穿的确良衬衫的少年站在邮简前,背后是还没拆的老百货大楼,楼顶上“为人民服务”的红漆字亮得晃眼。
“陈叔,您见过这人吗?”她把照片举过雨棚,雨珠顺着照片边缘往下淌,在少年的肩膀处晕开一小片水渍。
老陈眯眼瞅了半晌,烟斗在鞋楦上磕了磕:“这不是顾家小子吗?三十年前总在这儿等信,听说后来去深圳了,再也没回来过。”他忽然笑了,“那时候他跟隔壁裁缝铺的丫头好,天天往邮简里塞情书,有次还跟人打赌,说要让这邮简记得他俩的名字。”
雨越下越大,林小满把照片塞进衬衫内袋,指尖触到信封上的玉兰花,忽然想起今早开门时,邮简旁的石板缝里冒出株玉兰幼苗,不知是谁悄悄种的。她弯腰摸了摸新抽的嫩芽,冷不丁听见邮简里传来轻微的响动,像是有封信正从投递口慢慢滑出来。
她伸手去接,指尖刚碰到信封,就被烫似的缩回来——那信封上,赫然画着朵一模一样的玉兰花,收信人处写着:“给三十年后的小满”。
雨棚外的路灯亮了,昏黄的光透过雨帘落在邮简上,铁皮表面的锈痕在雨水中渐渐显露出字迹,像是无数人用指甲刻下的名字,层层叠叠,最终都融进这漫漫长夜里。林小满忽然明白,有些地址从来不需要邮票,就像有些时光,早被街角的邮简悄悄记在了心里。
林小满攥着那封新出现的信,指节因为用力泛白。雨珠顺着投递口的边缘往下淌,在信封右下角洇出一小片深色,倒让那朵玉兰花显得愈发鲜活,像是刚从枝头摘下来的。
“丫头,发什么愣呢?”老陈的声音从雨棚下传来,他正用抹布擦着湿漉漉的鞋油盒,“这天儿得下到后半夜,不早点回屋?”
她没应声,转身钻进邮筒旁的报刊亭。这亭子是她租来的,兼做收发信件的差事,墙角堆着半人高的旧信,都是投递失败后被退回来的。此刻那些信封在雨声里似乎都醒了过来,窸窸窣窣的响动混着窗外的雨,像谁在耳边絮絮低语。
台灯拧开时,暖黄的光立刻裹住了那封信。信封比普通的稍厚些,摸起来里面除了信纸,似乎还夹着别的东西。林小满用指甲轻轻挑开封口,首先掉出来的是枚黄铜钥匙,环扣处刻着个“顾”字,边缘被磨得发亮。
信纸是方格稿纸,字迹带着少年气的张扬,却在收尾处总不自觉地轻下来,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不知道三十年后的小满会不会怪我。那天你说要等我回来,我在邮筒上刻了咱们的名字,以为这样就能把时光钉在这儿。可火车开动时,我看见你站在百货大楼门口,手里攥着没寄出去的信,突然就怕了——怕深圳的风太大,吹走我答应你的日子;怕等我回来,邮筒还在,你却走了。”
林小满的指尖划过“百货大楼”四个字,忽然想起上周清理旧物时,在箱底翻到张泛黄的报纸,头版照片正是百货大楼拆除那天,起重机的吊臂下,有个穿蓝布衫的姑娘拼命往人群外挤,手里紧紧抱着个铁皮饼干盒。
信纸的背面画着张简易地图,用红笔圈出报刊亭墙角的位置,旁边写着:“如果你来,记得挖三十厘米深。”
雨势渐小的时候,林小满找了把旧铁锹。泥土被雨水泡得松软,铁锹插下去没费多少力气。挖到尺许深时,金属碰到硬物的闷响惊得她心跳漏了一拍。
是个锈迹斑斑的饼干盒,锁孔正好能插进那枚黄铜钥匙。打开的瞬间,整整齐齐的信滑了出来,足有几十封,每封的收信人都是“小满”,寄信人处画着玉兰花。最底下压着本日记,最后一页的日期停留在1993年深秋:
“今天在邮筒旁看见个小姑娘,扎着羊角辫,蹲在那儿数银杏叶。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亮得像你当年偷偷塞给我的橘子糖。突然就想,要是咱们的日子能重来一次,我肯定不登那列火车。”
窗外的雨停了,月亮从云里钻出来,恰好照在邮筒顶上。林小满忽然发现,那些被她数过无数次的锈痕,连起来竟真的是两个名字。她拿起最上面的那封信,借着月光读最后一句:“听说时光会老,但邮筒记得所有年轻的约定。”
远处传来早班公交车的引擎声,林小满把信放回饼干盒,重新埋进土里。转身时,看见邮筒旁的玉兰幼苗上,停着只萤火虫,亮闪闪的光在叶尖晃了晃,像是谁在说“我回来了”。
街角的时光邮简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相爱相杀的恶人
- 他们在恨意中发现自己都爱着对方,可能有什么办法呢?不常更新小短文很少
- 0.2万字10个月前
- 霸总的宠妻是大佬
- 哎呀呀,当男友和闺蜜双双背叛我,还联手把我推下楼后,没想到我居然“失忆了”,记忆回到了和他们相识的那天呢!嘿嘿,既然如此,那我可得好好地“报......
- 0.5万字10个月前
- 寻找消失的附近
- 明明生活在人口密度更高的环境里,城市却并没有让我们收获足够的亲密和温暖。为何“附近”会消失?我们还有可能找回“附近”吗?如今的社会,大家对自......
- 5.3万字7个月前
- 无解的救赎
- 程浒煜是出了名的外科圣手徐榆是小说作家他们一见钟情后来她死在了他的手术台上他的世界没有了徐榆初次与你相识就像在茫茫人海中发现了另一颗契合的灵......
- 0.6万字6个月前
- 大佬他对我有私心
- 【2024.07.27成功签约,原创作品,抄袭必究,禁转载、二改】两人在电竞的战场上并肩作战,又是怎样一步步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纽带?又是如何从......
- 20.2万字5个月前
- 亦苑盛夏
- 宋韵兮在校园和好朋友一起打闹,一个男生突然闯入宋韵兮的生活当中,掀起来一阵波澜,然而,宋韵兮在一个意外事故中,以为是男生救了他,开始了追求,......
- 2.0万字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