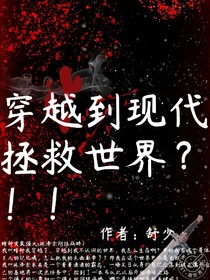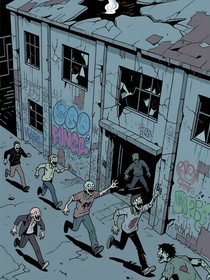第三十四章:流动的根系
天还没亮透,林野就被终端的提示音吵醒了。屏幕上跳动着一行新代码——是陈景明连夜写的,能让记忆数据流顺着地下管道的线路延伸,“就像给树盘根”,他附的消息里这样说,“昨天发现孤儿院的终端信号弱,这下能顺着水管爬到墙根下了”。
窗外传来铁锹碰石头的脆响。林野探头时,正看见瘸腿老人领着几个孩子在槐树下挖坑。老人的拐杖斜靠在树旁,裤脚卷得老高,露出脚踝上旧伤的疤痕,手里的铁锹却挥得稳稳的:“周老头说要种爬山虎,让藤蔓把档案馆的木板盖住,夏天能遮凉。”
孩子们举着小铲子跟着刨土,嘴里念叨着新学的名字——是记忆终端里那些“被找回来的人”。扎羊角辫的丫丫突然指着土块里的东西喊:“是蚯蚓!”那只暗红的小虫子在阳光下扭了扭,钻进刚翻的土里,留下条细细的隧道,像给土地系了根看不见的线。
“恒温箱的玉米种该移苗了。”母亲抱着育苗盆走过来,盆里的幼苗顶着嫩黄的叶尖,根须从盆底的小孔里钻出来,缠成一团细密的网,“你爸的笔记里画着图,说移苗时得带着原土,不然根会疼。”她说话时,指尖轻轻碰了碰幼苗的根,像在跟它们打招呼。
广场上的集市多了个新摊位。穿校服的男孩支起块木板,上面摆着十几本手写的册子,每本都记着终端里的故事——有陈景明被看守咬时的眼神,有老周修线路时哼的老歌,还有瘸腿老人讲的杂货铺往事。“周爷爷说机器可能会坏,但字写在纸上,能记更久。”男孩把册子递给来换故事的人,眼里的光和终端屏幕一样亮。
午后突然刮起风。记忆档案馆的木板被吹得哗哗响,陈景明正踩着梯子加固,白衬衫被风灌得鼓鼓的,像只展开翅膀的鸟。“昨晚扩容时发现个好东西。”他低头喊,手里的钉子敲得又快又准,“找到你爸藏的气象数据了,里面记着近五十年的节气,什么时候种豆子,什么时候收麦子,比终端预报还准。”
风里混着槐花的香。苏芮抱着终端跑过来,屏幕上正显示着新的记忆节点——是河对岸的农户连进来的,画面里他们在麦田边搭了个小木屋,墙上挂着用麦秆编的日历,每一页都画着不同的作物。“他们说要把种麦子的手艺存进终端,”苏芮指着画面里的老人,“那是当年教你爸辨认野菜的张大爷,他说终于能‘见’着老熟人了。”
老周蹲在档案馆前调试线路,听见这话笑出声,手里的螺丝刀在阳光下闪了闪:“哪是机器让咱们见着?是这些根缠在一起了——你帮我记着种地的法子,我帮你想着你爹的样子,缠得越密,越不容易断。”
傍晚的霞光把天空染成了橘红色。孩子们举着用麦秆做的小风车跑来跑去,风车叶上贴着从终端打印的照片——有丫丫妈妈编辫子的样子,有陈景明补屋顶的侧脸,还有父亲年轻时站在槐花树下的背影。风一吹,风车转起来,照片上的人仿佛也动了动,在霞光里对笑着打招呼。
林野蹲在玉米苗旁,看着母亲小心翼翼地把幼苗移入大田。带土的根须接触新土的瞬间,幼苗轻轻晃了晃,像是舒了口气。他忽然想起终端里那段修复好的影像:年轻的父亲蹲在田里移苗,母亲举着相机喊他看镜头,他回头时,手里还捏着株带土的幼苗,根须在风里轻轻飘。
“档案馆的爬山虎该浇水了。”苏芮的声音拉回他的思绪。她手里的水桶晃出些水,滴在刚栽的藤蔓上,水珠顺着茎秆往下流,钻进土里,像给新栽的生命系了根银线。
夜幕降临时,记忆终端突然发出一阵柔和的光。全息墙上的数据流不再是零散的光点,而是连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像地底蔓延的根系,把槐树下的新苗、河边的麦田、孤儿院的木板房都连了起来。每个节点都在发亮,像土壤里的星子。
老周把最后一段记忆存进终端——是他女儿小时候追萤火虫的样子,画面里的小女孩跑着跑着,突然回头对镜头笑,露出豁了颗的牙,和现在的老周一模一样。“这下踏实了。”他拍了拍终端,“根扎深了,风再大也吹不倒。”
林野靠在槐树上,看着全息网里流动的光。有片光点突然脱离主线,顺着地下线路往实验室飘去,落在恒温箱的指示灯上,像颗找到了家的星。他摸了摸口袋里父亲的笔记,纸页边缘被翻得发卷,上面画的根系图,和终端里的光网几乎重合。
风过时,爬山虎的新叶轻轻拍打着档案馆的木板,像无数只手在轻轻敲门。林野抬头时,看见丫丫举着风车从树下跑过,风车叶上父亲的照片在风里转着,和槐花、麦香、终端的光混在一起,成了这个春天最结实的根。
夜色渐深时,新栽的玉米苗在月光下舒展了叶尖。根须在土里悄悄生长,顺着记忆数据流的方向,往更远的地方伸去,像无数条看不见的线,把所有被记住的、被爱着的、被期待的,都紧紧连在了一起。
远处的终端还在低低嗡鸣,像大地的心跳,在裂痕深处,长出了绵延的力量。
回声代码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穿越到现代拯救世界?!!
- 睛舒贤良强大x陈泽余阴狠病娇)我叫晴舒我穿越了,穿越到我不认识的世界,我怎么生存啊?幸好我有这个身体主人的记忆咦,怎么把我的东西都带了?那我......
- 0.4万字8个月前
- 末日贼临
- 丧尸满城的城市。变异兽肆意的丛林。变异植物舞起的藤蔓,带走靠近的变异兽和武者留下亡者的遗骸。降临在这新世界,带着盗贼的角色力量划破黑暗,用手......
- 1.8万字6个月前
- 末日逃亡1
- 未知病毒扩散,末日逃亡
- 0.5万字6个月前
- 落日虹
- 2.2万字2个月前
- 汪汪队流浪地球
- 太阳正在急速老化,持续膨胀,太阳将会吞没整个地球,人类陷入惶恐......
- 0.8万字2个月前
- 核界:万核生存
- 2023年8月24日,日奔国向大海排到核废水。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
- 7.7万字3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