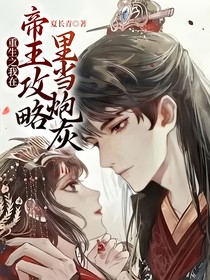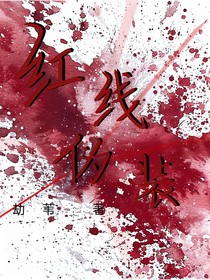第19章 晨露
我深吸一口气,整理着绛官袍的领口。
铜镜里的女子头戴银丝莲花冠,腰间蹀躞带上挂着典记印信——这行头比前世当皇后时的凤冠霞帔更让我指尖发颤。
"沈典记,时辰到了。"老宦官在门外轻叩。
太极殿前的汉白玉阶被晨露浸得微湿。我垂首跟在礼官身后,听见两侧官员的私语像毒蛇吐信般窸窣作响。
"女子为官,成何体......"
"听说她能背全《贞观政要》......"
朱漆殿门在面前缓缓洞开。鎏金蟠龙柱下,六部官员雁翅般分立两侧。当我的青缎官靴踏过门槛时,户部尚书郑禹的冷哼像块冰砸在脚边。
"臣沈棠梨,叩见陛下。"
御座上的青年天子抬手时,我瞥见他拇指上的翡翠扳指泛着熟悉的冷光。前世他就是用这只手,在鸩酒诏书上盖的玉玺。
"沈爱卿平身。"皇帝的声音比记忆中温和,"既任典记,今日便与诸位爱卿共议江南赋税之事。"
郑禹突然出列:"臣有一问。按《开元礼》记载,蚕桑税折算绢帛时,该当如何处置陈年积压?"他山羊胡翘得老高,"不知沈典记可曾读过?"
殿内骤然安静。这个问题藏在《唐六典》犄角旮旯里,分明是刁难。我余光看见几个年轻官员已经憋红了脸。
"郑大人问得巧。"我解下腰间锦囊,取出自制的黄麻纸册,"永徽三年曾有此例——"纸页翻动声惊飞了檐下的麻雀,"陈绢按市价七折折算,但须加盖'存'字朱印。"
皇帝突然轻笑出声。郑禹的脸色像被泼了隔夜茶汤。
"典记之职不在背诵,而在明辨。"我合上册子,"若大人需要,下官可誊抄贞观年间十二道相关敕令。"
退朝时细雨初歇。老宦官追上来塞给我一卷竹简:"前任林典记留下的账册,陛下命您重新勘合。"
档案库的霉味混着墨香。我摩挲着竹简上暗红的"甲"字标记,突然触到某处细微的凹凸。就着天窗漏下的光线,几行朱砂小字在潮湿处若隐若现:
"三月初七,兵部铁甲二百领记入乙库,实收......"后半截字迹被刻意晕染。我猛地攥紧竹简——前世边关失守,正是因为铁甲被换成了刷漆的竹片。
茶楼雅间的窗纸将暮色滤成蜜色。谢家大小姐的鎏金护甲叩着瓷盏:"家父说兵部最近在查军械账目。"
"谢姐姐可认得这种朱砂?"我蘸水在案上画出那个模糊的"甲"字。
她突然抓住我的手腕:"这是林典记的私印!她半年前坠井前,曾托我保管过一匣......"
楼下突然传来马蹄声。穿灰褐短打的仆妇慌张闯进来:"宫里来人传话,太后娘娘要见沈典记。"
铜镜中,我慢慢将密函藏进贴身的暗袋。镜外那个戴莲花冠的女子勾起唇角——这次,我要让那些吃人的账本自己开口说话。
我指尖一颤,青瓷茶盏在紫檀案几上磕出清脆的声响,几滴琥珀色的茶汤溅在谢大小姐绣着缠枝纹的袖口上。她鎏金护甲上的缠丝纹路硌得我腕间生疼,却仍不肯松手:"那匣子就埋在谢府后院的老石榴树下,用油纸包了三层。"
"沈典记,太后娘娘的鸾驾都到宣德门了!"仆妇在门外急得直搓手,粗布鞋底在松木地板上磨出沙沙的响动,像秋虫啃食树叶的声音。我瞥见窗外暮色里闪过绛色衣角——是宫里派来盯梢的。
我抓起茶壶将剩下的龙井尽数泼在案上,看着那个用茶水写就的"甲"字在木纹间晕开:"烦请姐姐今夜就派人把那匣子送去城南的笔墨铺子。"谢大小姐突然用护甲划破自己指尖,将血珠抹在我掌心:"以此为信。"
刚踏出茶楼,两个穿绛宫装的嬷嬷就像影子般贴上来。年长的那位掀开车帘时,我闻到她袖口飘出的沉水香里混着麝香——和前世太后赐死淑妃时熏帐子的配方分毫不差。年轻嬷嬷扶我上车时,我注意到她虎口有长期握刀磨出的茧子。
"娘娘这些日子总说梦话。"嬷嬷用金簪挑亮车内的羊角灯,暖黄的光照着她嘴角的细纹,"昨儿半夜惊醒,非说看见先帝在紫宸殿外淋着雨哭呢。"
她边说边往我手里塞了个鎏金暖炉,炉身上刻着双凤纹——是太后宫里独有的样式。
马车碾过雨后湿滑的青石板,我借着整理衣摆的动作摸了摸暗袋。竹简的棱角透过锦缎传来细微的刺痛,像在提醒我前世那场大雪——兵部送来的竹甲在箭雨中裂开时,也是这般扎手。宫墙上的琉璃瓦着晚霞,宛如凝固的血痕。
拐角处突然传来一阵银铃响,我掀帘看见几个戴帷帽的姑娘抱着账本从钱庄出来。
最前面那个掀开皂纱冲我眨眼——是上个月刚通过女官考试的张家三小姐。她腰间晃着的铜钥匙在夕阳下闪着光,那是我托人仿造的户部库房钥匙模样。
"沈大人可算来了。"守在宫门的小太监小跑着迎上来,他新换的靛蓝袍子下露出半截磨破的靴跟,"太后娘娘在暖阁里发了三回脾气,连最得宠的白猫都挨了戒尺。"他说着往我袖袋里塞了块温热的桂花糕,指尖沾着朱砂——是刚从批红的奏折上蹭下来的。
穿过垂花门时,我故意踩到块松动的青砖。趁弯腰整理官靴的功夫,我把那卷竹简塞进了砖缝。
抬头正对上嬷嬷探究的目光,我指着宫墙上新结的蛛网笑道:"您瞧,这网织得多像户部的鱼鳞册。"蛛丝间挂着的水珠颤巍巍的,像极了前世我见过的那些假账本上欲盖弥彰的墨渍。
重生之锦凰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仙缘尽
- 未曾想,顶天立地的顾玄之竟能被诬陷贬入凡间,身为他的左膀右臂,看在你我乃好友份上,这次我帮你一把。于是,燕钰也下了凡间。不过……瞧着,眨巴眨......
- 1.9万字5个月前
- 重生之我在帝王攻略里当炮灰
- 意外穿越,成为了男女主相爱路上的炮灰,为了尽快回到现实世界,女主听从系统安排,一路扶持男主登上皇位成功回家的故事
- 3.4万字4个月前
- 寒香入鼎
- ——以味破局,方知人间至毒不过人心永昌十七年冬,瑞王府招厨娘的告示贴着薄霜。云似捧着她的梅花扣肉踏进朱门时,不曾想过这方灶台竟是修罗场。庖厨......
- 0.3万字2个月前
- 寒月凝霜雪
- 更新中。禁抄袭,禁二转
- 5.3万字2个月前
- 流光明玉
- 孤女阿梨家遭大火,持婚书投奔未婚夫。相处中误会频生,游船落水后她心灰意冷远走。三年后重逢,爱与救赎的故事重新上演。甜美清醒女主V不懂得爱人冰......
- 1.7万字2个月前
- 红线伪装
- 一只努力工作隐瞒身份的小狐妖努力干好月老阴差阳错身份暴露卷走天庭重要资料三界追杀昔日侍从反目成仇
- 2.1万字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