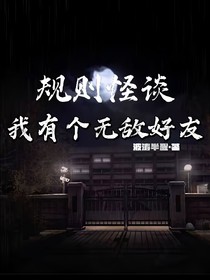铁锈根系
松林被砍伐后的树桩,在雨水浸泡下发黑腐烂。新种下的杉树苗细弱,杆上缠着防虫的草绳,在风里瑟瑟发抖。护林员老关头的红砖小屋彻底空了,窗户玻璃碎了半块,像被人打掉的门牙,黑洞洞地对着林间蜿蜒的土路。
再没人提起那个冬天枯河滩燃烧的黑烟,那仿佛被大地自身吞下的秘密。日子裹着冻硬的泥浆向前滚动,碾平了所有凸起的棱角。
村里唯一的变化,是村小学翻新了瓦顶。新瓦是从外地运来的,带着工业流水线上产出的统一灰色。施工队清理老屋基下的烂泥时,铁锹撞上一块硬物。挖出来一看,是个锈得几乎看不出原貌的铁皮箱子,棱角已经软塌下去,缝隙里塞满乌黑的淤泥和蜷缩的蜈蚣干尸。
“啥破烂玩意儿!”包工头一脚踹在箱体上,发出闷响,“扔坑里填了省事。”
箱子被丢在烂泥堆旁。夕阳给它染上一层短暂虚假的暖色。一个老校工,佝偻着背,默默走过来,用根废木棍在箱盖边缘撬了撬。“嘎吱”一声刺耳的金属撕裂声,扭曲的箱盖被掀开一角,露出里面层层叠叠的纸——或者说,曾几何时是纸的东西。如今只看见一大坨湿答答、黏糊糊的浆状物,颜色如腐烂的海藻,散发出浓烈的、混杂着铁锈和淤泥腥气的霉变气味。字迹早已被泥水浸透分解,无从辨认。几根细长、同样锈透的金属零件,半埋在这滩令人作呕的“纸浆”里,像淤泥里翻出的不知名生物骸骨。
老校工捂着鼻子退开了。没人多看一眼。
箱子最终被推入了垫屋基的大坑,和其他建筑垃圾一起,被新鲜的混凝土迅速覆盖、抹平。新瓦灰色的棱角,冰冷地立在曾经的废墟之上。
时光推进得无声无息,像一片巨大而沉重的铁锈,缓慢地覆盖侵蚀着一切。又几年过去,城里突然来了几个戴安全帽、臂章印着“文化遗产勘查”字样的年轻人。他们拿着奇形怪状的仪器,在村西那片早已看不出原貌的旧场地反复勘测,对着图纸低声讨论。领队的大学教授,姓秦,头发花白,鼻梁上架着银边眼镜,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常蹲在已被荒草和浮土覆盖严实的旧址边缘,长久凝视,像是要穿透地表,看到泥土深处蛰伏了数十载寒暑的东西。
“秦教授,这边探到明显异常。”年轻队员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激动。
那是松林边缘的一块低洼地,地表平坦无奇,只有几株顽强的酸枣刺,根茎虬结地抓着贫瘠的沙土。仪器读数在一处不起眼的酸枣刺根部下方突然飙升。
挖掘很小心。表层浮土被清理,渐渐显露出大片锈蚀、粘连的金属残片。它们深深嵌在深褐色、板结如岩石的坚硬土层里,与周围沉积多年的腐败枯枝败叶紧密纠缠。空气里弥漫开一股陈旧的铁腥味,如同某种沉疴多年的伤口被重新揭开。
“像是……结构件残骸,”一个队员用硬毛刷轻轻扫去附着其上的一层细密铁锈粉末,“有层叠构造……看这扭曲角度,像是巨大冲击力造成的整体变形……”
秦教授推了推眼镜,弯腰凑近。他戴着棉纱手套的手指,极其谨慎地抚过那片粗糙、冰凉的巨大金属表面。他的动作很轻,更像是一种触碰确认。铁锈如同粉尘,簌簌落下。
“注意下面那个凸起……嵌合物?”助手提醒。
在最深处一块巨大扭曲的金属断口下方,并非泥土。那里的土壤颜色格外深褐,粘稠板结得如同化石。众人小心翼翼地清理掉覆盖物,剥离表面的浮锈和顽固板结的泥土碎块后,赫然露出一个东西!
不是散落其上的零件。它深陷在那个巨大的、早已锈穿的破裂孔洞深处——像是有人以极大的力量,在金属尚呈炽热状态时将这东西硬生生按压、镶嵌了进去。
一枚葵花籽。
但早已不是植物形态。它完全炭化了,通体乌黑、坚硬、结构收缩变形得像个微型的、皱缩的干枯头颅。它紧紧卡在扭曲断裂的金属缝隙里,如同这庞大铁骸核心一颗无法撼动的心脏结石。
泥土下方似乎还有粘连物。教授用细长的毛刷和精巧的剔针,一点点剔除包裹着的深褐色硬泥。当粘连被最终分离,在场的所有人都倒抽一口冷气。
葵花籽并非孤悬。它纤细弯曲的尖端,连接着一截扭曲、短小的东西——一根极细的铜链,同样布满厚重铜绿,断裂处呈拉拽撕裂状。铜链的末端,深深没入下方更深处板结的泥土里。
“继续。”秦教授的声音异常沙哑。他手中的工具换成了更小型号的地质探针。
挖掘的耐心达到了极致。潮湿冰冷的土层被一层层细细分开。灯光聚焦下,浑浊的泥水里,终于显露出那铜链末端束缚的物体轮廓。
一小块断裂的金属物件,形制极其规则。
一个残损破碎的黄铜表盘。时针和分针在剧烈的冲击和漫长时光中早已不知去向,只留下光秃秃的表盘中央孔洞。唯一残存完好的,是边缘那枚纤细的秒针。它依旧被固定在断裂的轮轴结构上,孤悬着,针尖指着一个明确的刻度:九点十三分。
秒针停滞的痕迹,如同一个被时间本身刻意遗忘、又在死亡瞬间彻底凝固的姿态。
金属表面的黄铜光泽被厚厚的铜锈完全覆盖,呈现出一种幽暗的、病态的绿色。表盘边缘一圈极其细微的刻度环,大部分被泥土和氧化物糊死了,只有靠近秒针尖端指着的那个位置,硬泥被剔开,露出刻度的真容——那并非时间数字,而是一组极其微小的、精密蚀刻的花体英文字母缩写:S.T.2。
整个表盘连同停滞的秒针、断裂的铜链末端,与上方深嵌于金属断口的那枚炭化葵花籽,通过那截短小的、扭曲的铜链,构成了一种令人心悸的诡异连接。仿佛这粒坚硬的植物种子,曾是拴在这表盘指针上唯一的、最终的砝码。
“记录编号C-07。”秦教授对着便携录音笔说,声音里听不出情绪,“‘特定航材’(Special Airframe Materials)残件出土。核心异常:疑似微型计时器残片(疑似秒针组件)与未知坚硬种核(炭化植物种核)存在物理嵌合关联。嵌合深度……极深,判定为高强度外力瞬间嵌入……”他停顿了一下,镜片反射着探灯冷光,“……与历史推测的坠落瞬间力学特征高度吻合。”
拍照灯的白光闪过,将这凝滞于锈色泥土深处数十年的画面摄入冰冷的数码记忆卡。随后,技术人员用特殊的可塑树脂胶泥将这连成一体的怪异嵌合物整体封存下来。树脂是半透明的暗黄色,凝固后如同古琥珀,将这铁锈、铜绿与炭黑交织的死结,永恒地封存在一个时间胶囊里,隔绝了氧气。那一小段残存的、指在九点十三分的秒针尖端,在树脂下保持着最后的姿态,清晰可见。
清理工作持续到日头偏西。那堆庞大铁锈残骸被小心编号、分装。坑的底部,除了清理时带出的深层冻土湿泥外,再无他物。就在准备回填的最后一刻,助手发现了一个被遗漏的细节。
在坑壁紧靠那株酸枣刺盘曲根系的地方,泥土湿冷,颜色深得不自然。用小铲轻轻刮去一层浮土,露出的东西让年轻助手的手指猛地缩回。
一小片暗色的、边缘不规则的东西,不厚,质地既不像金属也不像石头,更像是朽烂的厚皮革或某种涂胶帆布的遗留物。表面粘满了淤泥,颜色黯淡,但隐约可见残存的花纹——几条褪色、粘连、边缘僵硬的线条,勾勒出某种抽象的五角轮廓的残余。红色的印记早已变成近乎黑色的铁锈色。
它紧贴着酸枣刺的根系下方生长,像是被植物的根紧紧抓住,包裹了不知多少年。帆布(如果真是帆布)纤维早已朽烂脆化,在剥离淤泥时稍一用力便碎裂开几道裂缝。透过裂缝,可以看见内侧同样被污泥渗透染黑的内衬,以及……内衬下夹着的、更薄的一层东西——几页几乎和泥土融为一体的暗黄色纸屑,纸上的蓝墨水字迹晕染扩散,如墨色的幽灵,完全无法分辨。
这片残破的碎片被单独取了出来,夹在两层特制的透气性保护海绵之间,放入一个扁平的硬塑料证物盒。
运输车沉重的引擎声撕裂了傍晚松林的寂静。后车厢密闭着,里面装着那具庞大扭曲的金属骨架、树脂封存的神秘嵌合物、以及那片紧贴树根的朽烂帆布残片。夕阳给它们镀上了一层短暂、虚假而沉重的血红色。车子沿着尚未完全硬化的土路颠簸着驶向远方城市的方向,车辙压出的深沟里很快蓄满了浑浊的泥浆水。
村庄并未恢复平静。那巨大的、带着泥土被撕裂伤口的深坑没有被完全填平。空气里残留着金属锈蚀的冰冷腥味,还有深层泥土被翻出后,那种混合着矿物质与远古腐败物质的、浑浊厚重的特殊气息。
夜里,风骤然转大,裹着枯叶沙石打着旋,撞击着村小学新换的灰色瓦顶,发出持续而枯燥的声响。住在村西头的人家说,他们在风声的间隙里,似乎隐约听到一种声音。
不是机械的碰撞,也不是哭泣的哽咽。
是像有什么极细、极薄的东西,在风力的撕扯下,一点点从根部崩裂开来的声音。极其缓慢,又极其坚持。声音里带着一种……枯脆的质感。
像是在啃噬一块彻底风干、硬如铁片的豆饼。咔嚓。咔嚓。
声音的方向,似乎正来自那片刚被挖开、又匆忙回填了一半的坑洼地。
夜色更浓时,酸枣刺紧挨着深坑的根部,在无人注视的黑暗中,无声地渗出了一点极微小的、淡黄色的树脂状树液,缓慢地、一点一点地,将坑边松动的新土再次粘合。
倒挂的钟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规则怪谈:我有一个无敌好友
- 在不为人知的某个角落,又有多少人遭受着诡异的侵袭……我只是个普通人,我没办法抵御这种强大的力量,幸亏有你……可你……是谁?!
- 1.4万字7个月前
- 我在749局当差那些年
- 人病且死,人死为鬼,那么鬼死了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世间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解开749局那些年办过的案子!
- 6.7万字7个月前
- 阴阳之间
- 冥界之人,人间之事,都是阴谋。
- 3.9万字5个月前
- 焰月无双
- 同人文,故事全部原创。对于原著会有一些互动,但不多
- 19.1万字5个月前
- 孤岛回声
- 他从最初的孤独、绝望,到逐渐找到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最终意识到孤独不是终点,而是重生的起点。这个过程充满了情感的张力和启示,展现了人性中最温......
- 1.0万字4个月前
- 杀破狼之镇北王
- [荼蘼园]荼蘼花开,故人归来『已签约』【小说同人】(标签打错了,签约改不了)日更,不拆长庚&顾昀cp。私设李晏三皇子还活着,剧情略微改动。李......
- 10.2万字4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