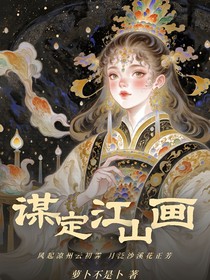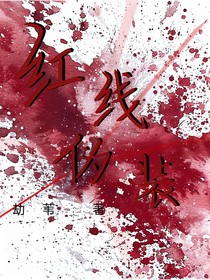繁荣与喜悦
“万里疆域的繁华底色”
天元三十七年的上元城,朱雀大街的青石板路被往来马蹄磨得发亮,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钟鼓楼的鎏金宝顶,将十二丈高的城墙染成金红。从城门口望进去,绸缎庄的蜀锦在晨光里流转着水纹,胡商牵着骆驼走进香料铺,驼铃叮当撞碎了巷弄的寂静,酒肆二楼的窗棂推开,杏花酿的醇香混着说书先生的醒木声漫出来,惊飞了檐角栖息的灰鸽——这是天元朝最寻常的清晨,却藏着百年难遇的盛世密码。
元景宴登基的三十七载,疆域已扩至东起沧海鲛珠岛,西抵昆仑流沙境,南接百越榕树寨,北达极寒驯鹿原。户部舆图上,新修的官道如银线穿珠,将两百州府连缀成网,驿站里的快马日夜不息,三日内便能将岭南的荔枝送到上元城的御膳房。江南的桑田连成片,蚕娘采摘的新丝能织出映雪的素纱;北境的牧场水草丰美,牧民的羊群漫过山坡,像流动的白云;连西域的商队都带着葡萄美酒和和田玉,在互市上用三匹骆驼换一匹中原的云锦——这是天元独有的底气,百姓兜里的铜钱叮当作响,市集上的吆喝声能掀翻半条街。
城根下的老茶寮里,说书先生拍着醒木讲《元景宴平南策》,说当年陛下亲率水师横渡琼州海峡,舰船上的龙旗被海风扯得猎猎作响,蛮族首领见了那阵仗,当场卸甲投降。茶客们听得拍案,穿粗布短打的汉子灌了口浓茶:"咱天元的兵,能把太阳都射下来!"旁边卖糖画的匠人手不停歇,铜勺在青石板上游走,转眼间就转出条鳞爪飞扬的龙,引得孩童们围着拍手,铜钱落进木盒的脆响,混着远处酒肆的猜拳声,热闹得像要把这盛世煮沸。
“朝堂与军防的稳固根基”
紫宸殿的梁柱上,"敬天保民"四个金字被香火熏得温润。元景宴推行的"三省分权制"已运转如精密钟表,中书省草拟的政令,门下省复核时挑不出半点错漏,尚书省执行时雷厉风行。每月初一的朝会上,寒门出身的御史敢指着世家勋贵的鼻子弹劾,而位列三公的老臣也会为了赈灾粮的运输路线争得面红耳赤——这是天元朝的朝堂气象,争论归争论,却从未有过党同伐异的倾轧。
兵部尚书的案头,北境舆图被红笔圈出十二处关隘,镇国公仇峰统领的"破虏军"就驻守在最北的雁门关。那支铁骑有八万之众,战马是西域进贡的汗血宝马,玄甲在日光下连成银海,冲锋时的马蹄声能惊起雁门关外的雁阵,黑压压一片掠过城头。每年霜降,仇峰都会带着长子仇惊弦在校场演武,少年将军银枪一抖,枪尖的寒芒能劈开飘落的红叶,身后亲兵齐声呼喝,声浪震得演武场边的梧桐叶簌簌落满青石地面。
元景宴常说:"有镇国公在,朕这龙椅下的基石就稳如泰山。"这话并非虚言,十年前草原部落趁秋汛南侵,仇峰带着三千轻骑奔袭三日,在狼居胥山追上敌军主力,他亲斩敌首的弯刀至今挂在镇国公府的正厅,刀鞘上的宝石在烛火下流转着冷光,像在诉说那场血战的惨烈。如今的雁门关外,互市上的胡商与中原商贩讨价还价,连部落首领的女儿都穿着中原的襦裙,鬓边簪着蜀地的珠花——这是铁血换来的安稳,是天元盛世最坚实的铠甲。
“梅下初见与深宫相守”
元景宴还是太子时,在皇家寺庙的梅林里遇见了上官奕。那时她是吏部尚书的庶女,跟着嫡母来上香,穿着件半旧的月白袄裙,正踮脚够枝桠上的落梅,发间别着枚素银簪,风卷着雪沫落在她肩头,像落了场碎玉。太子看得痴了,脚下踩着的枯枝"咔嚓"作响,上官奕回头望过来,眼里的惊惶比梅花还怯,拢了拢被风吹乱的鬓发,屈膝行礼时,发间的银簪晃出细碎的光。
后来他纳她为侧妃,在东宫的偏殿里,她为他研墨时总把墨锭磨得太细,他笑着夺过墨锭:"笨丫头,这样要磨到天亮。"她就红了脸,指尖绞着围裙上的流苏。夺嫡最凶险时,三皇子派人在她的汤药里下毒,想借她的手除掉太子,是她捧着药碗迟迟不肯喂,说"殿下今日龙体不适,这药太苦,臣妾去加些蜜",拖延间让暗卫抓住了下毒的侍女。那夜元景宴抱着她发抖的身子,在她耳边说:"奕儿,等我登基,必许你后位。"
可他终究没能做到。登基那年,太后以"庶女难母仪天下"为由,强立了丞相的嫡女为后。元景宴在御书房枯坐一夜,第二天去看上官奕,见她正坐在窗前绣一幅《寒江雪》,银针在绢上走得极慢,像在缝补破碎的月光。他握住她的手,那双手因熬夜绣活泛着冷意:"奕儿,委屈你了。"她抬头笑了,眼里的光却暗了些:"陛下是天子,当以江山为重。"
此后三十七年,皇后的中宫形同虚设,上官奕的瑶光殿成了元景宴最常去的地方。他处理政务到深夜,总会提着灯笼穿过长长的宫道,见她坐在灯下等他,桌上的莲子羹永远温着,是他最熟悉的甜。她从不争什么,却把他的喜好记得比谁都清楚:他不喜葱姜,御膳房的菜里从不见这两样;他读奏折时爱用陈年普洱,她就亲手在小炭炉上煨着茶;连他龙袍上的玉带扣松了,她都能拿出早就备好的新绦子——这是藏在规矩里的温柔,是元景宴在冰冷皇权里唯一的暖。
“岁月流转与心底缺憾”
瑶光殿的玉兰开了三十七次,元景宴的鬓角从青丝染成霜雪,上官奕的眼角也添了细密的纹路。他们会在傍晚沿着护城河散步,看夕阳把水面染成金红,像当年初见时的梅林落雪。他说朝堂上的趣事,说哪个御史又在奏疏里写了打油诗,哪个地方官送了新奇的贡品;她听着,偶尔插一句"那贡品若是吃食,记得给孩子们分些"——她指的是宫中年幼的皇子公主,却从不提自己没能生育的事。
太医院的院判换了三任,每次给上官奕诊脉都摇头,说当年她为救陛下挡过刺客的暗箭,伤了根本,怕是再难有孕。元景宴把那些送来"生子秘方"的官员都贬了职,说"贵妃的身子岂容尔等妄议",可夜深人静时,他会对着月亮祈祷,哪怕折损十年阳寿,也要给她一个孩子。
上官奕从未抱怨过,却总在绣活时不自觉地绣些胖娃娃。有次元景宴看到她绣的《百子图》,每个娃娃的眉眼都不一样,却都笑得眉眼弯弯。他从身后抱住她,下巴抵在她的发顶:"奕儿,没有孩子也没关系,有你就够了。"她转过身,把脸埋在他的龙袍里,肩膀微微颤抖,像只受了委屈的小兽。
天元三十六年的深秋,上官奕晨起时忽然干呕,侍女慌慌张张去请太医。白发苍苍的院判诊脉时,手指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诊了半晌突然跪地,老泪纵横:"恭喜陛下!贺喜陛下!贵妃娘娘有孕了!"
“意外之喜与举国欢腾”
消息传到御书房时,元景宴正握着北境大捷的奏报,闻言猛地站起来,手里的狼毫笔"啪"地掉在奏折上,晕开一团墨渍。他连龙袍下摆被门槛勾住都没察觉,踉跄着奔向瑶光殿,推开殿门时,上官奕正靠在软榻上,见他来了,眼里泛起水光,像落了场春雨。
"奕儿,是真的?"他扑过去握住她的手,声音都在发颤,指尖的凉透过衣袖传过来。上官奕点头,指尖抚过他眼角的皱纹:"陛下,太医说,已有三月了。"
这消息像长了翅膀,半日就传遍了上元城。户部尚书当即上奏,要减免来年赋税为皇子积福;礼部尚书连夜拟定庆典章程,连洗三礼的流程都细化到香案上该摆几样果品;最热闹的是民间,绸缎庄的红绸被抢购一空,酒肆推出"贺喜酒"买一坛送一坛,连城外的农夫都对着皇宫方向拜了三拜——在百姓心里,上官贵妃是出了名的菩萨心肠,她的孩子定是上天送来的福泽。
镇国公仇峰听说消息,亲自从北境赶回上元,带着长子仇惊弦跪在宫门外求见。元景宴在御花园见他们时,仇峰手里捧着个锦盒,打开竟是柄玄铁小剑,剑鞘上嵌着块暖玉:"陛下,这是臣让人特意打造的,玉能安神,剑能辟邪,愿小殿下平安长大。"他身后的仇惊弦也捧着支白玉长命锁,少年将军难得有些腼腆:"臣...臣祝小殿下将来...文武双全。"
元景宴笑着拍仇峰的肩膀:"有你们父子在,朕的止墨还愁学不到本事?"那时他已在心里为孩子取好了名字,却没说出口,想等上官奕身子好些再商量。
“孕期呵护与无微不至”
瑶光殿被元景宴护得密不透风。他让人把所有门槛都包上锦缎,连窗棂边角都裹了软垫;从江南运来最软的云锦铺成地毯,走在上面悄无声息;太医院的三名御医轮班值守,住在偏殿随时待命;御膳房每天换着花样做安胎吃食,燕窝要挑去所有绒毛,莲子羹必须去芯,连水果都要温过才端上来。
他推掉了大半宴请,每日朝会结束就往瑶光殿赶。看她吃饭时会亲自布菜,把鱼刺挑得干干净净;陪她散步时走得极慢,手里总攥着件披风,生怕她被风吹着;晚上亲自给她读诗,读错了字被她笑着纠正,就挠挠头说"还是奕儿读得好听"。
有次上官奕说想吃城西的桂花糕,那铺子在朱雀大街尽头,离皇宫有三里地。元景宴换上常服,带着两个侍卫就去排队。他站在市井里,听着周围的议论声——"听说贵妃娘娘怀了龙胎,陛下高兴得亲自给娘娘买糕点呢""咱天元要有小皇子了,真是天大的喜事"——心里甜得像揣了蜜。回来时满头大汗,把还温热的桂花糕递给她,自己先端起她没喝完的参茶喝了一口,说"沾沾喜气"。
薛钰也常来瑶光殿陪上官奕说话,带来亲手绣的小肚兜,上面绣着只麒麟,针脚细密得看不见线。"妹妹放宽心,"薛钰握着她的手,"我怀惊弦时也怕这怕那,其实孩子比咱们想的结实。"上官奕笑着点头,抚摸着隆起的小腹,那里正传来轻微的胎动,像小鱼在水里游。
随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上官奕夜里常会腿抽筋。元景宴就学着给她按摩,一开始手法笨拙,捏得她直皱眉,后来慢慢熟练了,总能准确找到酸痛处。他的手指常年握笔,指腹有层薄茧,按摩时却轻得像羽毛,她靠在他怀里,听着他哼的不成调的摇篮曲,总能安心睡去。
“产房内外与惊天啼哭”
预产期前三天,瑶光殿挂起了红灯笼,宫门口守着八名禁军,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元景宴让人在殿外搭了个小棚子,里面放着张躺椅,他就守在那里,批阅奏折时耳朵也竖着,生怕错过里面的动静。
生产那天来得突然。清晨的露水还没干,上官奕突然痛呼出声,稳婆赶紧让人去请太医,同时把备好的参汤、干净布巾摆好。元景宴冲进外间时,听到里面的痛呼声,心像被一只手紧紧攥住,疼得他直冒冷汗。
他想进去,被稳婆拦住:"陛下,产房阴气重,您是真龙天子,进去不吉利。"他只能在外面踱步,一步,两步,三步...地砖被他踩出浅浅的印记。太医们跪在旁边,大气不敢出,听着里面的动静,脸色比元景宴还紧张。
时间一点点过去,从清晨到正午,又到黄昏。上官奕的痛呼声越来越弱,元景宴的心也一点点沉下去。他抓住院判的胳膊,几乎是吼出来的:"到底怎么样?朕要进去!"院判满头大汗,哆哆嗦嗦地说:"陛下...娘娘年纪大了,怕是...怕是难产..."
话没说完,里面突然传来一声响亮的啼哭,像道惊雷劈开了沉闷的空气!紧接着,稳婆抱着个红布包裹的婴孩冲出来,满脸是泪,跪地高呼:"恭喜陛下!贺喜陛下!是位皇子!母子平安!"
元景宴几乎是踉跄着冲进产房。上官奕脸色苍白如纸,嘴唇干裂,见他进来,虚弱地笑了笑。他扑到床边,握住她的手,眼泪"唰"地掉了下来,滴在她的手背上,滚烫滚烫的。"奕儿...辛苦你了..."他哽咽着,说不出完整的话。
乳母把孩子抱过来,放在上官奕身边。那小家伙闭着眼睛,小脸红扑扑的,像个熟透的桃子,嘴巴还在咂巴着,仿佛在找奶吃。元景宴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指,碰了碰他的小脸,软得像棉花糖,那小家伙像是感觉到了什么,突然抓住他的手指,力道竟不小。
那一刻,元景宴觉得自己拥有了全世界。江山万里,不及怀中珍宝万分之一。
“定名止墨与洗三庆典”
皇子的名字,元景宴早就想好了。他坐在上官奕床边,握着她的手说:"奕儿,你常说愿这世间少些纷争,多些安宁。这孩子,就叫'止墨'吧,笔墨之处,便是心安之处。"
上官奕笑了,眼角泛起泪光:"元止墨...好名字。"她转头看了看襁褓里的孩子,轻声道:"止墨,娘的好孩子。"小家伙像是听懂了,小嘴动了动,吐了个泡泡。
洗三礼办得盛大而不失雅致。文武百官都送来了贺礼,丞相送的玉如意雕工精湛,上面刻着"长命百岁";仇峰送的长命锁用了赤金,嵌着东珠,沉甸甸的,据说能驱邪避灾;连远在江南的盐商,都派人送来一箱南海珍珠,颗颗圆润饱满。
元景宴抱着元止墨坐在上官奕身边,接受众人的道贺。他平时威严的脸上满是笑意,抱着孩子的姿势虽然笨拙,却透着小心翼翼的珍视。当仇峰上前时,元止墨突然睁开了眼睛,乌溜溜的,直勾勾地看着他,还咧开嘴笑了——那笑容像朵刚绽开的花,引得众人一阵欢呼。仇峰挠了挠头,粗声粗气道:"这小子...跟我投缘!"
庆典最热闹的环节是"添盆"。元景宴亲自舀了一勺温水,滴在铜盆里,然后是上官奕,接着是皇子的外祖父。当仇峰上前时,他特意多舀了些水,说"北境的水养人,让小殿下将来也能像雄鹰一样翱翔",引得元景宴朗声大笑。
瑶光殿的玉兰花香飘得很远,混着庆典的喜乐声,漫过宫墙,漫过朱雀大街,漫过整个上元城。护城河的画舫上,琴师弹起了新编的《盛世谣》,弦音里满是温柔的祝福。元景宴低头看着怀里的元止墨,又望向身边的上官奕,觉得这三十七载的等待,都值了。
“镇国公府的双喜临门”
镇国公府的喜事,与宫中皇子降生恰是同一天。
薛钰怀第三胎时,比寻常孕妇多怀了半月,府里上下都悬着心。生产前一夜,薛钰睡得不安稳,梦见自个儿站在开满木槿花的院子里,一只白狐衔来朵紫槿花放在她手心,转眼化作金光没了踪影。她惊醒时,窗外正飘着细雨,院中的百年木槿本已过了花期,此刻竟开得满树绚烂,紫莹莹的花瓣沾着雨珠,像落了满地星辰。
守夜的婆子们见了这奇景,忙不迭往前院报信。仇峰正在书房看军报,听闻后院木槿花开得蹊跷,心里咯噔一下——薛槿白日里说过胎动得厉害,莫不是要生了?他扔下狼毫笔就往后院跑,玄色常服扫倒了砚台,墨汁晕染了军报也顾不上。
穿过月亮门时,果然见那株木槿繁花似锦。他伸手摘了朵,花瓣软得像薛钰鬓边的绒花,鼻尖萦绕着清冽香气——这树是薛钰嫁过来那年亲手栽的,九年光景已长得比房檐还高。正看着,产房里突然传来稳婆的呼喊:"生了!是位小姐!"
仇峰冲进外间,乳母抱着个红绸裹的襁褓出来,只露颗毛茸茸的小脑袋。他接过时手都在颤,常年握枪的粗粝手掌托着那团软乎乎的小东西,生怕稍一用力就伤着。小家伙闭着眼,睫毛长卷如小扇,小嘴动了动,发出细弱的咿呀声,倒让他心头一暖,粗声笑起来:"这丫头,有劲儿!"
薛钰醒来时,天已微亮。仇峰还守在床边,怀里抱着襁褓,坐姿笔挺如松,却时不时低头瞅一眼,嘴角挂着罕见的柔意。"醒了?"他声音放得极轻,"给孩子取个名吧。"
薛钰看他掏出自个压在锦帕里的木槿花,花瓣依旧鲜润。"你说叫什么好?"仇峰想了想:"她伴着花开而生,就叫若渝吧。若木槿般坚韧,若渝水般澄澈。"
薛钰默念"仇若渝",指尖轻点女儿脸蛋:"好名字。"小家伙似是应和,突然睁眼,黑葡萄似的眼珠直勾勾看着仇峰,竟咧嘴笑了。
这时宫里信使到了,说皇上喜得皇子,名唤元止墨。仇峰听了哈哈大笑,抱着女儿对薛钰道:"瞧瞧,跟陛下的皇子同一天降生,咱们若渝,缘分不浅呢。"
墨渝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带着宗门拯救修真界
- 苍生唯义,万世太平.“少年意气风发,生命不息,拯救苍生成为现实,他们亦是世人所歌颂的英雄”
- 0.7万字6个月前
- 潇潇无声
- 女主转世轮回三世情缘,尝尽人世间的七情八苦
- 1.4万字5个月前
- 傲世长公主:谋定江山画
- 长公主楚凝霜,父皇宠溺、皇兄疼爱,自幼浸润权谋,睿智冷血。父皇崩逝,皇兄继位却生性懦弱,朝堂暗流涌动,奸佞林太师妄图架空皇权,蛇蝎美人苏妙音......
- 7.2万字3个月前
- 红线伪装
- 一只努力工作隐瞒身份的小狐妖努力干好月老阴差阳错身份暴露卷走天庭重要资料三界追杀昔日侍从反目成仇
- 2.1万字3个月前
- 凤梨素
- 【正文内容】长信宫的红烛烧到了第三根,烛油噼啪炸出星子,将明黄圣旨上的
- 2.4万字3周前
- 朝云夕雨
- 两人从小在一个私塾长大,并且互交为知己,十分的友好。在不知不觉间双方都爱着对方。在他们二十五岁那一年,正值边疆战乱朝廷里面没有武将可用,二人......
- 1.4万字13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