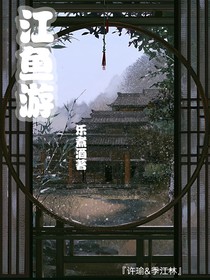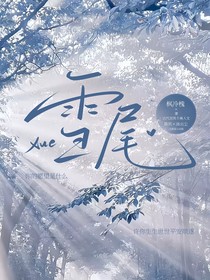上元灯影·惊鸿
永安二十三年的上元灯节,京城朱雀街被灯笼照得像条淌着光的河。朱红宫灯悬在飞檐下,琉璃灯串垂在巷陌间,连护城河边的柳树上都缠满了绢灯,风一吹,万千光点晃得人眼晕。空气中浮动着糖画的甜香、煮茶汤的醇厚、孩童手里糖葫芦的酸气,混着远处戏楼飘来的弦乐,织成一张热热闹闹的网,将整个京城裹在其中。
元止墨勒住缰绳时,胯下的“踏雪”刚从围场的旷野奔进这人间烟火地。马鼻里还喷着带着枯草气息的白汽,骤然被满街的喧嚣裹住,不安地刨了刨蹄子。他偏过头,看身后的内侍福安捧着件狐裘披风小跑追赶,帽檐上沾着的围场雪渣还没化,在灯笼光下闪着碎银似的光,忍不住嗤笑一声。
“殿下!慢些!”福安跑得气喘吁吁,袍子下摆扫过青石板,带起一串细碎的声响,“夜里风凉,仔细冻着——”
“冻着?”元止墨反手接过披风,却没往身上披,只随意搭在马鞍前桥,玄色骑装的袖口被风掀起,露出腕上磨得发亮的银镯子——那是母妃给他求的平安符。“本王在围场能赤膊斗熊,这点风算什么?”他说着,故意夹了夹马腹,踏雪立刻扬起前蹄,惊得路边几个提着兔子灯的孩童尖叫着躲闪。他哈哈大笑起来,少年人的野气比头顶的灯笼还要亮,袖袋里揣着的太傅戒尺硌着腰侧,像块调皮的石头。
十三岁的年纪,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仗着元景宴帝的偏爱,他在京城里向来横着走——前几日嫌礼部尚书奏对时啰嗦,趁人转身的功夫,把人家乌纱帽扔进了护城河里,气得老尚书在金銮殿上哭着要辞官;昨日太傅教他读《资治通鉴》,他嫌字太密像蚂蚁,竟把先生的紫檀戒尺偷揣进袖袋,此刻那冰凉的木头还在跟他的腰侧较劲。
“前面是灯谜棚!”随从兴奋地指着前方,那里攒动的人影比别处更密,“听说今年的头奖是支羊脂玉簪,雕了满工的缠枝莲!”
元止墨正想催马过去,街角突然窜出一辆青帷马车。赶车的小厮约莫十五六岁,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显然没料到会撞见疾驰的骏马,吓得手一松,缰绳在手里缠成了乱麻。踏雪被这突如其来的障碍惊得人立而起,前蹄几乎要踏上车顶的铜铃,清脆的铃声混着马嘶,在喧闹的街面上撕开一道口子。
“放肆!”护卫统领拔刀出鞘,寒光映着灯笼的红光,在地上投下晃动的影子,“给我拿下这刁民!”
“住手。”元止墨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慑。他稳稳坐于鞍上,左手紧扣马鬃,右手已抽出腰间的马鞭,鞭梢在空中划出道残影,却没有挥下去。目光越过躁动的马颈,落在被风掀起的车帘一角——
那一瞬间,周遭的喧嚣仿佛都被按下了静音。
车里坐着位少女。
她穿件月白绫袄,领口袖缘绣着细碎的缠枝纹,针脚密得像春雨织的网,在灯笼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许是被惊马吓着,她正抬手按着被风吹乱的鬓发,皓腕抬起时,露出半截羊脂玉镯,莹白得与衣袖几乎分不清。烛光从车窗的缝隙漏进去,在她脸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斑,衬得肤色莹白如瓷,连耳后那点柔软的绒毛都看得清晰。唇瓣没涂胭脂,透着点病气的淡粉,像早春刚绽的桃花瓣,沾着未干的露水。
最惹眼的是那双眼睛。
睫毛长得像蝶翼,此刻正簌簌地颤,显然含着惊惶。可眼底却清明得很,像盛着一汪刚融的雪水,映着窗外的灯笼,亮得能照见人影。那目光扫过他时,没有寻常闺阁女子的怯懦,甚至没有半分谄媚,只有一闪而过的审视,像小鹿撞见了猎人,却没忘了抬头看清对方的模样。
“殿下,这等冲撞仪仗的刁民……”护卫统领还想说话,被元止墨冷冷一瞥堵了回去。
元止墨的目光没离开那少女,语气里带着几分玩味:“你是谁家的?胆子倒不小,敢在朱雀街拦本王的马。”
车帘被一只素手轻轻掀开。那手指纤细,指尖因常年汤药浸润,带着点微凉的白,指甲修剪得圆润整齐。少女扶着丫鬟的手慢慢下车,屈膝行礼时动作轻缓,膝盖弯到一半,似乎还顿了顿,显然是身子不便。
“镇国公府,仇若渝。”她声音很轻,像落在梅枝上的雪,却字字清晰,每个字都稳稳地钻进人耳朵里,“惊扰殿下,是若渝之过。”
镇国公仇峰的嫡女?元止墨挑了挑眉。他倒是听过这名号。仇峰常年戍守北疆,京中只留家眷,据说这位嫡小姐打小体弱,三岁时得过场急病,此后便汤药不离口,连三年前元景宴帝的六十大寿宫宴都没参加,没想到竟是这般模样。
他正想说些什么,却见仇若渝抬起头,目光掠过他腰间的玉佩——那是元景宴帝赐的墨玉麒麟佩,边角还沾着围场的泥——忽然微微抿了抿唇,像是在憋什么话。
“想说什么?”元止墨饶有兴致地看着她,“本王赦你无罪。”
仇若渝的睫毛又颤了颤,终是抬起眼,目光落在他手里的马鞭上:“殿下的马鞭……缠了不该缠的东西。”
“嗯?”元止墨愣了愣,低头看向自己的马鞭。那是柄鹿皮缠柄的马鞭,他用了两年,此刻鞭梢果然缠着几圈细细的红绳,打了个歪歪扭扭的结,像是方才惊马时不小心勾到的。
“这是……”
“方才马惊时,许是勾到了街边的灯笼穗。”她指尖极轻地指了指鞭梢,像怕惊扰了什么,“红绳缠在鞭梢,挥起来容易打滑。”
元止墨捏着鞭柄转了转,果然觉得有些滞涩。这等细枝末节,连整日跟在他身边的随从都没发现,她竟一眼瞧出来了?他忽然觉得这少女比京里那些只会捻绣花针的姑娘有趣多了。
“你倒懂得不少。”他故意把马鞭在掌心拍了拍,目光在她脸上打了个转,“连马鞭打滑都知道,难不成镇国公还教女儿骑马?”
仇若渝垂下眼睫,长睫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家父寄来的家书中,常说军中要务,一马二鞭三甲胄。鞭子不顺手,纵是好马也难跑。若渝看得多了,便记下了。”
“哦?”元止墨往前走了两步,玄色骑装的下摆扫过青石板,带起一阵风,吹得她鬓边的碎发微微飘动,“那依你看,本王这鞭子该怎么弄?”
仇若渝显然没料到他会追问,愣了愣才道:“解开便好。”
“可本王懒得动手。”元止墨把马鞭往她面前递了递,眼里的戏谑藏不住,“仇小姐替本王解了?”
旁边的丫鬟郁灵脸都白了,忙上前一步:“殿下!我家小姐……”
“郁灵。”仇若渝轻轻按住丫鬟的手,抬头看向元止墨,目光里没了方才的疏离,反倒添了点无奈,像在看个耍赖的孩童,“殿下若不嫌弃,若渝便斗胆一试。”
她伸出手,指尖刚触到鞭梢的红绳,元止墨忽然觉得手心有些发烫。她的手指很凉,带着点草药的清苦气,与他常年握缰磨出薄茧的手截然不同。红绳缠得不算紧,她三两下便解开了,动作轻得像拈起一片羽毛。
“好了,殿下。”她将解开的红绳随手丢在旁边的垃圾桶里,对他福了福身,“不敢再叨扰。”
“急什么?”元止墨收回马鞭,却没让开道路,反而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她,“本王听说镇国公府的小姐常年养病,今日怎么有兴致出来看灯?”
“祖母说,灯节的烟火能驱邪。”仇若渝老实回话,“让若渝出来沾沾喜气。”
“沾喜气?”元止墨笑了,忽然从袖袋里摸出颗蜜饯,抛给旁边吓得还没缓过神的小厮,“给你家小姐压惊。这是御膳房做的杏仁酥,甜的,能压惊。”
小厮慌忙接住,手还在抖。仇若渝却对他微微颔首:“谢殿下。时辰不早,若渝先行告辞。”
“等等。”元止墨叫住她,目光落在被踏雪蹭掉块漆的车辕上,“这车本王赔了,明日让镇国公府的人去东宫领新的。”
仇若渝看着他,眼底闪过一丝无奈,却没再推辞,只福了福身:“那便谢过殿下。”
马车重新启动,青帷幔缓缓落下,遮住了那抹素白。车轮碾过灯笼投下的光斑,铜铃声“叮铃”远去,像串被拉长的省略号。
元止墨站在原地,手里还捏着那根刚解开红绳的马鞭。鞭梢的鹿皮被风吹得轻轻晃动,他忽然觉得,方才她指尖碰过的地方,似乎比别处更暖些。
“殿下,灯谜棚的头奖……”随从小心翼翼地问。
“去取来。”元止墨扬了扬下巴,目光还追着那远去的马车,“雕缠枝莲的玉簪,是吧?”
“是。”
“拿着。”他接过那支羊脂玉簪,簪头的莲花在灯笼光下莹白温润,花瓣上的纹路清晰得能数出瓣数。他忽然觉得,这簪子跟方才那位少女的气质,倒有几分像。
“殿下,还去逛灯吗?”福安问。
元止墨摇头,翻身上马:“回宫。”
踏雪似乎还在闹脾气,走得慢吞吞的。元止墨却没催,任由马缰松松地搭在手里。他想起仇若渝那双眼睛,清凌凌的,像北疆的雪水,明明看着弱不禁风,却偏生映出点不肯弯折的韧劲。她解开红绳时的样子很认真,睫毛垂着,侧脸的轮廓被灯光描得很柔和,像幅没干的水墨画。
他忽然摸了摸腰间的墨玉佩,那上面还沾着围场的泥。原来被人提醒的滋味,也不算太坏。
马车里,郁灵终于松了口气,拍着胸口道:“小姐,那可是三殿下啊!听说他最是混不吝,前几日还把礼部尚书的帽子扔河里了,您方才竟敢……竟敢碰他的马鞭!”
仇若渝拢了拢衣襟,指尖触到袖袋里的暖炉,那是出门前母亲塞给她的,此刻还温着。她望着车窗外掠过的灯笼,轻声道:“他不是混不吝。”
“啊?”郁灵瞪圆了眼睛,显然不信。
“他只是活得太自在了。”仇若渝笑了笑,眼底映着流动的灯火,像落了星星,“像没被缰绳拴住的马。”
郁灵还是不懂,只觉得自家小姐今日很奇怪。明明被皇子冲撞了,却半点不恼,还替人家解马鞭。她偷偷看了眼那枚杏仁酥,用油纸包着,方方正正的,透着点甜香。
仇若渝却没心思管这些。她想起元止墨递过马鞭时的样子,眼里的戏谑像小孩子举着糖逗蚂蚁,带着点幼稚的张扬,却没什么恶意。方才他说“本王赔你”时,语气里没有轻视,只有理所当然的坦荡,倒不像传闻中那般蛮不讲理。
车过护城桥时,她掀起帘角,看见那抹玄色身影正骑马往皇宫方向去,月光落在他的发梢,像镀了层银。他手里似乎拿着什么亮闪闪的东西,在灯笼光下晃了晃。
“小姐,您看什么呢?”
“没什么。”仇若渝放下帘,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腕间的玉镯,那是父亲从北疆捎回来的,说是和田玉能养人,“只是觉得,今晚的月亮,倒比往常亮些。”
东宫的夜很静,只有巡夜的侍卫脚步声远远传来。元止墨坐在书房里,却没像往常那样翻话本,只把玩着那支海棠玉簪。烛火跳动,映得簪身的纹路明明灭灭,莲花的影子投在墙上,像朵会动的云。
“福安。”
“奴才在。”福安捧着盏热茶,见他对着玉簪出神,心里纳罕。
“镇国公府的那位仇小姐,”他状似不经意地问,手指摩挲着簪头的花瓣,“你知道多少?”
福安愣了愣,连忙回话:“回殿下,仇小姐是镇国公的独女,今年十六,跟殿下同岁。听说生下来就体弱,三岁时得过场急病,太医说要静养,所以很少出门。镇国公夫人疼她,连府里的石子路都铺了毡子,怕她摔着碰着。”
元止墨挑眉:“这么金贵?”
“是呢。”福安又道,“不过听说仇小姐极聪慧,镇国公的家书里,常夸她过目不忘,连兵书都能背下来。前阵子兵部尚书还说,镇国公送来的军防图,旁边的批注比幕僚写得还周详,后来才知是仇小姐帮着看的。”
元止墨笑了,将玉簪放在案上:“有意思。”
他想起仇若渝说“家父常寄家书”时的样子,语气里没有寻常女子的娇怯,反倒带着点与有荣焉的骄傲。原来那看似柔弱的身子里,还藏着这些故事。她连马鞭打滑都知道,想来兵书是真的看进去了。
窗外的灯笼还在远处亮着,偶尔传来孩童的笑闹声,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元止墨拿起那支紫檀戒尺,本想随手扔了,却又放下。他忽然觉得,明日去给太傅赔个不是,似乎也不算太难——毕竟,那老头的戒尺,可比他的马鞭顺手多了。
而镇国公府的西跨院,仇若渝正坐在窗边看书。青禾端来汤药,苦气弥漫开来,她却面不改色地一饮而尽,连眉头都没皱。药碗底沉着几粒红枣,是母亲特意让厨房加的,可那股子黄连的苦,还是从舌尖一直苦到心里。
“小姐,您真要去东宫领马车?”郁灵不解,“三殿下许是随口说说的。”
仇若渝翻过一页书,是本《武经总要》,书页边缘都翻得起了毛,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批注,字迹清隽,带着点力透纸背的劲。“君无戏言,皇子亦然。”她轻声道,“明日你去一趟,不用领新马车,道谢便好。顺便……”她顿了顿,“问问东宫的内侍,三殿下常用的马鞭是什么尺寸,回头让管家照着做一柄,算我还他今日的情分。”
郁灵张大了嘴:“小姐!您这是……”
“只是谢礼。”仇若渝的目光落在书页上的“兵法”二字,“他帮我解了围,我总得回礼。”
郁灵应了,又想起什么:“小姐,那枚杏仁酥……”
“收着吧。”仇若渝的指尖划过批注,“或许以后用得上。”
烛火摇曳,将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单薄却挺直,像株在夜里悄悄生长的竹。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棂,落在书页上,照亮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八个字,墨迹被岁月晕开了点,却依旧清晰。
永安二十三年的上元灯节,就这么过去了。朱雀街的灯笼渐渐熄灭,护城河边的柳丝还缠着残灯,像系着未完的心事。巡夜的更夫敲过三更,梆子声在空荡的街面上荡开,惊飞了檐下的夜鸟。
谁也没料到,这场看似寻常的惊遇,会像投入湖心的石子,在往后的岁月里,漾开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元止墨后来常想,那日若不是踏雪惊了马,他大抵会像往常那样,抢了灯谜棚的头奖,再去酒楼喝得酩酊大醉,醒来后早把这灯节忘得一干二净。可偏偏,他遇见了仇若渝。
那个穿月白绫袄的少女,像一场落在惊蛰的雪,清冷,却带着唤醒万物的力量。她能看穿他马鞭上的红绳,能读懂他玩笑话里的孩子气,像面干净的玉。
墨渝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明月词
- 陈生,只是一颗灵魂。敬恨生,才是真正完整存在的一个人。前世今生,被缝补的伤痕再次撕裂,露出惨痛森森的触目惊心。“我不信命。”“阿生,带我回家......
- 0.4万字7个月前
- 摄政王掌心之物
- 我的爱人生命终结在了二十二岁,青春年少,生命的散去,独留我在往后经年抱憾终身
- 4.5万字6个月前
- 江鱼游
- 许家女子,绝不为情所困。救天下苍生为此生之志。许瑜遇知己季江林,二人目的相同,志向一致。先婚后爱
- 1.4万字6个月前
- 雪尾
- 陈玖拥有九世前两世受人虐待在第三世遇见了一个待他极好的人陈玖本以为的缘分却是那位君子用双眼换来的君子不求其他只求陈玖生生世世都能平安顺遂“野......
- 0.4万字5个月前
- 梦几回
- 天界有一规矩,凡天族成婚者需进入引情道历经磨难以求真情。
- 0.9万字5个月前
- 浴火凤凰:嫡女归来
- 丞相嫡女林晚惨遭庶妹陷害,身陷绝境时与幽冥虚影缔结灵魂契约,以命为引换取掌控生死的力量。从血染柴房到权倾朝野,她在朝堂之上以符术揭露太子叛国......
- 2.6万字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