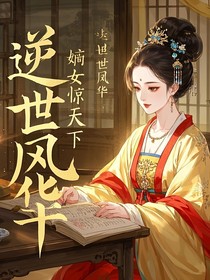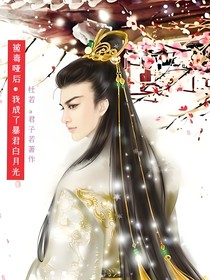冰雪聪明
皇宫的玉阶总染着朝露,太和殿前的铜鹤却似永远睁着警醒的眼。唯有御花园西北角的那方水榭,常年飘着酒香——那是三皇子元止墨的去处。此刻他正斜倚在临水的美人靠上,手里转着枚白玉棋子,看阶下锦鲤争食。内侍监的总管太监李德全远远站着,连大气都不敢喘,只因为昨夜这位皇子又把太傅的《资治通鉴》改成了话本,还在朝上念给了满朝文武听。
“李德全,”元止墨忽然开口,声音里带着刚醒的慵懒,“父皇今日歇在哪个宫?”
李德全忙趋步上前,弓着背回话:“回三殿下,万岁爷凌晨在御书房批了奏折,这会儿该去景仁宫陪贵妃娘娘用早膳了。”
元止墨嗤笑一声,将棋子抛进水里,溅起的水花惊得锦鲤四散。“知道了。”他起身时,月白锦袍扫过石桌,带落了半碟没吃完的杏仁酥,“告诉御膳房,把昨儿西域进贡的葡萄酿温一坛,送到水榭来。”
李德全脸都白了:“殿下,太医说您上月风寒刚好,不宜饮酒……”
“让你去就去。”元止墨挑眉看他,那双眼睛生得极像上官贵妃,眼尾微微上挑,却比贵妃多了几分桀骜,“难不成要我亲自去御膳房讨酒?”
李德全哪敢应这话,忙不迭地应了声“奴才这就去”,转身时衣襟都被冷汗浸得发潮。谁都知道,这三皇子元止墨是万岁爷和上官贵妃心尖上的肉,打不得骂不得,偏又活得比谁都自在,连太和殿的金砖都敢踩出响来。
景仁宫里,上官贵妃正用银签挑着燕窝粥里的红枣。她今日穿了件海棠红的宫装,鬓边斜插着支赤金点翠步摇,抬手时,腕间的翡翠镯子碰出清越的响。皇帝元景宴放下朱笔,看着她鬓边的步摇笑:“还是你这里清净,不像御书房,满案的奏折能压死人。”
“陛下又惯着止墨了。”上官贵妃嗔了句,却掩不住眼底的笑意,“昨儿太傅进宫哭诉,说三儿把《孙子兵法》批注得不成体统,还说‘兵者诡道也’不如‘酒者王道也’,您倒好,还夸他批注得有趣。”
元景宴拿起块芙蓉糕,慢条斯理地吃着:“那老东西就是死板。止墨说的没错,当年朕打天下时,若不是在军帐里和将领们拼了三坛酒,哪能让他们死心塌地跟着朕?”他忽然放低声音,指尖划过奏折上的墨迹,“再说,这满朝文武,谁有止墨那份通透?上月黄河决堤,各部尚书吵了三天都没个章程,他倒好,在水榭里钓着鱼,就让人递了张纸条,说‘堵不如疏,迁不如赈’,最后照着他的法子办,果然太平了。”
上官贵妃抿了口茶:“陛下也太夸他了。他那不过是歪打正着。”话虽如此,嘴角的笑意却深了几分。她还记得止墨三岁那年,抓周时越过满桌的玉玺、兵符,一把抓住了元景宴腰间的酒葫芦,当时元景宴就抱着他大笑:“这小子,随朕!”
正说着,殿外传来一阵轻捷的脚步声,元止墨掀帘而入,带着一身水汽和草木香。“父皇,母妃。”他没像其他皇子那样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只随意作了个揖,就坐到上官贵妃身边,伸手就去拈碟子里的梅花酥。
“没规矩的东西。”元景宴瞪了他一眼,眼里却没半分怒气,“刚从哪儿野回来?”
“在水榭看鱼呢。”元止墨含着点心说话,含糊不清的,“儿臣看那锦鲤傻得很,喂多少食都不嫌多,倒像户部的那些官儿,拨多少银子都不够贪。”
上官贵妃笑着拍掉他的手:“不许胡说。”元景宴却来了兴致:“哦?你又看出什么了?”
“前儿去户部查账,”元止墨拿起茶杯,给自己倒了杯凉茶,“见他们把江南的盐税记成了河工银,账面上倒做得干净,可库房的封条是上个月的,里面的银子却少了三成。儿臣让侍卫去查那管账的李主事家,果然在他家地窖里搜出了三箱银子,上面还贴着盐引的标签呢。”
元景宴放下茶盏,眸色沉了沉:“你怎么不早说?”
“说了您又要动气。”元止墨满不在乎地耸耸肩,“儿臣已经让李德全把银子送回库房了,那李主事嘛……”他故意拖长了调子,“儿臣看他女儿刚满月,就罚他去守皇陵三年,也算留了条活路。”
上官贵妃捏着帕子的手紧了紧:“你这孩子,怎么什么事都自己做主?万一出了差错……”
“母妃放心。”元止墨握住她的手,指尖带着水的凉意,“儿臣办事,什么时候出过错?”
元景宴看着他,忽然笑了。这儿子,性子像极了年轻时的自己,却比自己多了份不管不顾的潇洒。当年他为了帝位步步为营,连笑都要掂量三分,可止墨不一样,他敢在金銮殿上和御史大夫争辩,敢在祭天大典上嫌祭品太素,敢把西域送来的宝马骑到太液池边去钓鱼——偏生他做什么都透着股灵气,让人恨不起来。
那日下午,元止墨被元景宴叫到御书房。案上摊着份奏折,是兵部尚书递上来的,说北境的匈奴又在边境挑衅,请求陛下派兵征讨。元景宴指着奏折问:“你怎么看?”
元止墨扫了眼奏折,拿起旁边的狼毫笔,在“征讨”二字上打了个叉:“打什么打?劳民伤财。”
“你倒说说,不打怎么办?”元景宴挑眉看他。
“匈奴想要什么?不就是粮食和布匹吗?”元止墨蘸了点墨,在纸上画了个圈,“去年冬天北境雪大,他们的牛羊冻死了不少,自然要闹。儿臣听说,匈奴的小王子上个月偷偷来过大同,在酒楼里喝多了,说他们单于其实不想打仗,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你想议和?”元景宴追问。
“不是议和,是做买卖。”元止墨放下笔,语气轻快,“咱们把江南的丝绸、茶叶运过去,换他们的良马和皮毛,再在边境设个互市,让两边的百姓自由贸易。他们有了粮食和布匹,自然不会来犯境;咱们得了良马,正好充实骑兵。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元景宴看着纸上那个歪歪扭扭的圈,忽然想起止墨五岁那年,拿着他的兵符当玩具,说要给士兵们分糖吃。那时他只当是孩童戏言,如今看来,这孩子心里装着的,比那些只会喊“万岁”的大臣们要多得多。
“就依你。”元景宴拍了拍他的肩,“这事就交给你去办。”
元止墨却摇头:“儿臣不去。”
“为何?”
“北境风沙大,吹得人头疼。”他说得理直气壮,“儿臣让兵部侍郎去就行,他嘴皮子溜,定能把匈奴说动。”
元景宴又气又笑,拿起御案上的镇纸作势要打:“你这懒骨头!”元止墨却灵活地躲开,笑着往外跑:“儿臣去水榭等好消息!”
看着他消失在门后的背影,元景宴无奈地摇摇头,眼里却满是笑意。上官贵妃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手里捧着件狐裘披风:“陛下,天凉了,止墨穿得少,要不要让李德全给他送去?”
“不用。”元景宴拉住她的手,“这孩子,皮实着呢。”
三日后,兵部侍郎从北境传回消息,说匈奴单于答应了互市,还说要亲自来京城朝拜。满朝文武都惊得说不出话,谁也没想到,这棘手的边境问题,竟被三皇子几句话就解决了。元景宴在朝会上笑着说:“你们都学学止墨,别整天就知道喊打喊杀,有时候,一杯酒比一把刀管用。”
那日傍晚,元止墨在水榭里摆了宴,邀了几个相熟的侍卫和内侍。他没穿皇子的锦袍,只着了件青色布衣,和众人猜拳喝酒,笑声传遍了半个御花园。李德全远远看着,忽然想起去年冬天,这位皇子为了救只掉进冰窟窿的猫,亲自跳进水里,冻得发了三天高烧,上官贵妃哭得眼睛都肿了,元景宴却只是叹着气说:“随他吧,随他吧。”
酒过三巡,元止墨醉眼朦胧地靠在栏杆上,望着天边的晚霞。有侍卫问:“殿下,您就不怕陛下怪您不懂规矩吗?”
他笑了,拿起酒坛往嘴里倒了口酒:“规矩是什么?是给那些想当皇帝的人定的。我不想当皇帝,自然不用守规矩。”
“那殿下想做什么?”
“我想骑着西域的宝马,去江南看桃花,去塞北看飞雪。”元止墨的声音带着醉意,却格外清晰,“想喝最烈的酒,看最美的景,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元景宴耳朵里。当晚,元景宴去景仁宫,见上官贵妃正对着件刚做好的貂皮斗篷出神。“在想什么?”他问。
“在想止墨说的话。”上官贵妃叹了口气,“他真的不想当皇帝吗?”
“不想当才好。”元景宴坐在她身边,拿起斗篷看了看,“这天下,看着风光,其实是副枷锁。朕当了三十年皇帝,连好好睡个觉都难。止墨这性子,就该无拘无束地活着。”他忽然笑了,“再说,有他在,谁敢动朕的江山?那些想搞小动作的,还没动手,就被他用酒坛子砸回去了。”
上官贵妃被他逗笑了,眼角的细纹都舒展开来:“陛下就惯着他吧。”
“不惯着他,惯着谁?”元景宴握住她的手,目光温柔,“他是咱们的儿子,是这宫里唯一活得像自己的人。”
夜色渐深,水榭里的灯火还亮着。元止墨醉倒在石桌上,怀里抱着个酒坛,嘴角还挂着笑。月光洒在他脸上,柔和了他平日里的桀骜。李德全轻手轻脚地走过去,给她盖上件披风,心里忽然明白,为什么万岁爷和贵妃娘娘那么疼这位三皇子——在这规矩森严的紫禁城里,元止墨就像一阵自在的风,吹开了笼罩在龙榻之侧的沉闷,让这冰冷的皇宫,多了几分人间的烟火气。
第二日清晨,元止墨被一阵鸟鸣吵醒。他揉着发胀的太阳穴坐起来,见石桌上放着份奏折,是元景宴让人送来的。奏折上批着一行字:“北境互市之事,你办得很好。朕准你下月去江南巡查,顺便看看桃花。”
元止墨笑了,拿起笔在奏折背面画了个鬼脸,让人送回御书房。他知道,父皇懂他,母妃也懂他。这天下的规矩再多,总有一处地方,能让他活得自在潇洒——因为他是元止墨,是皇帝与上官贵妃最疼爱的儿子,是这紫禁城永远的例外。
御书房里,元景宴看着奏折背面的鬼脸,无奈地笑了。上官贵妃凑过来看了看,也笑了:“这孩子,都多大了,还这么孩子气。”
元景宴放下奏折,望着窗外的阳光,忽然说:“等朕百年之后,就让止墨去江南吧。给他一块封地,让他酿酒、种花、看风景,再也不用回这紫禁城。”
上官贵妃的眼眶湿了,却点了点头:“好,就让他做个自在王爷,一辈子开开心心的。”
风吹过御花园,水榭里的酒坛轻轻晃动,发出清脆的声响。那是属于元止墨的声音,是这规矩森严的皇宫里,最动听的自在之歌。
镇国公府的藏书楼总飘着淡淡的药香与墨香。仇若渝斜倚在铺着软垫的竹榻上,身上搭着件素色绒毯,指尖捻着枚白玉棋子,正对着棋盘凝神。廊外的风卷着落叶掠过窗棂,她肩头微颤了下,却没像往常那样缩进毯子里,只将棋子轻轻落在棋盘上,声音轻却稳:“二哥,这步‘尖冲’,你怕是没算到。”
仇惊砚盯着棋盘皱起眉。方才他还占着上风,不过片刻功夫,小妹这枚看似轻缓的棋子,竟像根细针,悄无声息地刺破了他的防线。他抬头时,见仇若渝正微微喘着气,苍白的脸颊泛着点薄红——那是凝神思索时攒下的气力,长长的睫毛上沾着点未干的药渍,是今早喝药时不小心溅上的,却丝毫不减她眼底的清亮。
“你这脑子,怎么偏对这些弯弯绕绕灵光。”仇惊砚挠了挠头,伸手想去挪棋子,却被仇若渝按住手腕。她的指尖微凉,力气却比看上去要大些,虽只轻轻搭着,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落子无悔,二哥忘了?”说罢轻咳两声,细弱的肩膀颤了颤,却仍稳稳地看着他,“你看这左下角的棋筋,被我这子一卡,气就紧了。”
仇惊砚凑近细看,果然见自己的黑棋像是被扼住了咽喉,不由得咋舌:“方才还觉得你落子慢,原来都在这儿等着我。”仇若渝浅浅笑了,想抬手揉下酸胀的太阳穴,却因久坐有些发麻,手腕在空中顿了顿才落下,轻声道:“我走得慢,正好能多算几步。”
乳母端着参茶进来时,见棋盘上黑白交错,已隐隐见出胜负,忙将茶盏递到仇若渝手边:“姑娘歇会儿吧,都下了一个时辰了。”她接过茶盏,指尖触到温热的瓷壁,轻轻蜷了蜷——方才捏棋子太久,指节有些发僵。呷了口茶,才缓过气来,指着棋盘对仇惊砚道:“你若在这儿补一手,还能撑住。”
仇惊砚刚要落子,却见仇若渝忽然蹙起眉,细弱的呼吸急促了些,忙道:“算了算了,我认输。”她却摇头,取过自己的白棋,在棋盘另一侧轻轻一点:“这样就能活了。”指尖在棋盘上划过,留下淡淡的痕迹,“棋要留活口,做人也一样。”说罢又是一阵轻咳,咳得眼底蒙了层水汽,却仍坚持把棋路讲完,“你看,退一步反而海阔天空。”
这时仇惊弦走进来,见妹妹正用帕子掩着唇轻咳,棋盘上却摆着一局精妙的收束,不禁笑道:“又赢了惊砚?”仇若渝放下帕子,脸色虽白,眼神却亮:“大哥来得正好,前日你问我的《曹娥诔辞》,那‘孝’字的捺笔,我想到个法子。”她想起身取纸笔,却被仇惊弦按住:“坐着说就好。”
“捺笔要像流水绕石,”她伸出食指,在棋盘边缘虚画,指尖因用力而微微发颤,“起笔要轻,行到中段再渐用力,收笔时带点回锋,就像……就像我那日看檐角的雨,坠到半空总要顿一下才落地。”话说得急了些,又引发一阵咳嗽,她却摆摆手示意无妨,等喘匀了气,又补充道:“你总说写得太硬,是因为没让笔锋‘缓一缓’。”
仇惊弦看着她苍白却认真的侧脸,忽然想起前日她看军防图时,也是这样,指着西城角楼的箭窗轻声道:“角度太陡,射出去的箭会飘。”那时她刚发过一场低热,说话都带着气音,却把箭道的弧度算得分毫不差。这妹妹身子弱得像株兰草,偏骨子里藏着股韧劲,病中也不肯把书放下,连咳得抬不起头时,还惦记着给账房改采买的方子。
午后薛钰来看她,见她正趴在案上抄《算经十书》,写不了几个字就要停下揉手腕,墨迹在纸上洇出小小的团,却依旧一笔一划不肯潦草。“又在费神了。”薛钰拿起她抄的纸页,见“割圆术”三个字旁,密密麻麻批注着演算过程,字迹娟秀却有力,像初春破土的芽,柔弱里藏着股钻劲。
“娘你看,这里的算法错了。”仇若渝抬头时,眼睛亮得惊人,浑然忘了方才抄书的累,指着其中一行道,“用徽率算才对,径一周三太粗糙了。”说罢想去翻原书佐证,起身时脚下一软,踉跄了下才站稳,扶着案沿喘了口气,却笑道:“你看我,又忘了自己走不快。”
傍晚时,吏部尚书家的李小姐来拜访,两人对弈时,李小姐见仇若渝落子极慢,每一步都要歇一歇,起初还觉得她力不从心,谁知下到中盘,才发现自己的棋子早已被悄悄围住。“这步‘倒脱靴’,我竟没看出来。”李小姐惊讶地睁大眼睛,见仇若渝正用帕子轻按唇角,咳得细弱却没停手,指尖执着棋子,稳稳落在关键处,“姐姐若走这里,还能活半盘。”
“你身子这样,怎么还能算得这么精?”李小姐忍不住问。仇若渝浅浅笑了,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韧劲:“我走得慢,便把每一步都想透了。就像走路,旁人一步跨三级台阶,我一步一级,虽慢些,却稳当。”说罢轻轻咳嗽着,却将棋盘上的后续变化一一讲来,条理分明,连李小姐这等棋力不弱的,也听得心服口服。
夜深时,仇若渝坐在窗边看月,案上摊着西域地图,她用朱笔在葱岭旁画了个圈,笔尖在纸上顿了顿,写下“驿站”二字。乳母来催她歇息,见她披着绒毯仍在微微发颤,心疼道:“姑娘,这些事自有大人操心,你何苦费神。”她却摇头,指尖轻抚过地图上的山川河流,轻声道:“我虽走不远,却能让商队走得稳些。”
风从窗缝钻进来,吹得烛火轻轻摇晃,她裹紧绒毯,细弱的肩膀却挺得笔直。这镇国公府的嫡女,就像株生在石缝里的兰草,看似柔弱得经不住风雨,根却深深扎在泥土里,用她独有的方式,在方寸天地间,活出了自己的坚韧与通透。棋盘上的智慧,书页里的乾坤,早已在她柔弱的身躯里,酿成了比金石更坚硬的力量。
次日晨起,仇若渝刚用过药,便让丫鬟取来昨日未看完的《水经注》。她倚在窗边的软榻上,阳光透过雕花木窗,在书页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那些记载着江河脉络的字句,在她眼中渐渐活了过来。看到“河水又东,迳砥柱间”时,她忽然抬手按住书页,睫毛轻颤着思索——前日大哥提过黄河漕运常有沉船,莫不是这砥柱暗礁在作祟?
正看得出神,忽闻院外传来马蹄声,接着是仇惊砚爽朗的笑:“小妹,你要的西域商路账册我取来了!”话音未落,他已大步跨进院门,怀里抱着厚厚的几本账册,见妹妹正捧着书卷出神,便放轻脚步走近,“又在琢磨什么?这账册我可是从户部好友那里好不容易借来的,上面记着近十年的商队损耗呢。”
仇若渝抬眸时,眼底还带着思索的清亮,伸手接过账册,指尖抚过泛黄的纸页:“多谢二哥。”她翻开最末一本,见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沙暴损驼队三”“雪山迷路折损七人”等字样,眉头不由得蹙起,“去年冬月那支去泉仪的商队,竟是全军覆没?”
“可不是嘛,”仇惊砚在她身边坐下,拿起桌上的蜜饯塞了颗进嘴,“听说在葱岭遇了雪崩,连尸骨都没找着。”仇若渝指尖在“葱岭”二字上顿了顿,忽然想起昨夜画的驿站,轻声道:“若在雪山脚下设个暖铺,让商队分拨过山,遇了风雪能暂避,或许能少些折损。”
“暖铺?”仇惊砚挠挠头,“那地方荒无人烟,谁肯去守着?再说粮草补给也难啊。”仇若渝却翻到账册前页,指着其中一行道:“你看,这十年间有八支商队都走的同一条山道,说明那是必经之路。咱们可以让过往商队分摊银钱,雇当地山民守铺,再备些干柴草药,既能避风雪,又能救急。”
她说话时,指尖在账册上划出路线,从龟兹到疏勒,再到葱岭山口,每一处险地都用指甲轻轻点过:“这里是风口,要建石屋;这里有山泉,可储水;这里……”话说到一半,忽然一阵头晕,她忙按住额角,账册从膝头滑落,仇惊砚眼疾手快地接住,见她脸色白得像纸,急道:“又不舒服了?都说了别总琢磨这些!”
“不碍事,”她缓了缓神,接过账册重新按住,“二哥你看,把这些险地标出来,让商队按时辰过山,避开风雪最烈的卯时和酉时,是不是更稳妥?”仇惊砚看着她指尖画出的时辰标记,忽然觉得这病弱的妹妹手里,仿佛握着支能指点江山的笔,那些旁人只当数字看的账册,在她眼里竟成了活生生的路。
正说着,仇惊弦带着位须发花白的老者走进来,正是钦天监的周监正。“若渝,周先生说你前日算的星象轨迹,比钦天监的历书还准。”仇惊弦话音刚落,周监正已拱手行礼:“仇姑娘,老夫今日特来请教,那‘荧惑守心’的异动,姑娘是如何算出偏移三度的?”
仇若渝忙要起身,却被周监正按住:“姑娘不必多礼。”她便倚着软榻,指着案上的浑天仪道:“先生您看,这北斗第七星的光度,上月比往年暗了三分,按《甘石星经》的算法,光度每暗一分,轨迹便会偏一度……”她指尖拨动铜制的星轨,细弱的声音里满是笃定,从星象运行到四季农时,竟说得周监正频频点头,连声道:“原来如此!老夫竟忽略了光度与轨迹的关联。”
周监正走后,仇惊弦拿起妹妹演算星象的纸页,见上面除了密密麻麻的算式,还在空白处画着小小的农具,旁注“芒种前三日播种,可避洪涝”。他忽然想起去年夏天,京畿暴雨,唯有镇国公府佃户的田亩因提前开了排水沟而未受损失,那时妹妹也是这样,对着农书算到深夜,咳得帕子都湿了大半。
午后,府里的账房先生来求见,手里捧着本皱巴巴的采买账册。“姑娘,这月的炭火钱总对不上,老奴算了三遍都差着三两银子。”仇若渝接过账册,见上面记着“初一买炭二十斤,付银五钱”“十五买炭三十斤,付银七钱”,眉头微蹙:“炭价是随市价浮动的,初一那日大雪,炭价该涨了,怎么还是五钱?”
她让丫鬟取来前五年的账册对比,指尖在纸页上划过,忽然停在某一行:“去年腊月十三也下了大雪,那日买炭二十斤付了六钱。按这个涨幅,初一的炭价至少该是六钱,这里记低了。”账房先生凑近一看,果然见初一的炭价被人改了笔迹,不由得咋舌:“定是采买的小厮做了手脚!姑娘真是神了,这都能看出来。”
仇若渝却轻轻叹了口气:“不是神,是账册会说话。”她指着那些数字道,“就像棋盘上的棋子,哪里不对劲,总会露出痕迹的。”说罢又咳起来,这次咳得格外厉害,乳母连忙端来汤药,她却摆摆手:“先让账房先生去查吧,别让小厮坏了府里的规矩。”
傍晚时分,薛钰带着新制的药来,见案上摆着账册、星图、商路图,还有半篇未写完的《算经》批注,不由得嗔道:“你呀,身子骨这样,倒把自己当三头六臂的神仙了。”仇若渝接过药碗,仰头饮尽,苦涩的药味在舌尖蔓延,她却笑了:“娘,我只是觉得,这些事若是算明白了,总能帮上些忙。”
她指着窗外渐暗的天色:“就像这月亮,每月十五总会圆,算准了它的规律,夜路就好走些。”薛钰看着女儿苍白脸上的认真,忽然想起她三岁那年,别的孩童还在学说话,她已能指着账本上的数字,咿咿呀呀说出“这个多了”;五岁那年生了场大病,高烧不退时,竟还惦记着要把未完的棋谱看完。
夜深后,仇若渝躺在榻上,却无睡意。她想起今日周监正
墨渝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逆世风华:嫡女惊天下
- 林若璃穿越醒来,正逢相府宴会,遭众人刁难,她凭借现代知识惊艳全场,初露锋芒,引得萧逸尘关注。此后,林若璃在府中与柳嫣儿多次交锋,识破其阴谋,......
- 12.0万字6个月前
- 美艳恶女每天都辗转于修罗场
- 无脑爽文,主写风月情事,轻权谋。桑窈是低微的庶公主,却生得一幅瑰丽艳绝的好相貌。上一世,她宫婢出身的母亲教她勾上嫡姐夫婿的庶弟,最后却被榨干......
- 0.9万字5个月前
- 被毒哑后:我成了暴君白月光
- 慕容铭翊是宸国冷酷无情的年轻暴君,以铁血手段镇压叛乱,朝堂上下人人自危,后宫空置无人敢近,登基后废除后宫。以雷霆手段登基,血洗反对势力,建立......
- 9.9万字2个月前
- 女失忆男重生农村生活多姿多彩
- 女主(失忆)男主(重生)
- 0.1万字4周前
- 三朝传
- 有多对情侣,偏权谋,有些小儿科,慎入!论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淮朝云聂,治国不当,然经三方努力,局部的统一必定能实现!
- 1.4万字4周前
- 魂穿古代大小姐之后
- 男主林墨魂穿古代大小姐苏瑶身上被坑爹系统引发的爆笑事件
- 3.1万字2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