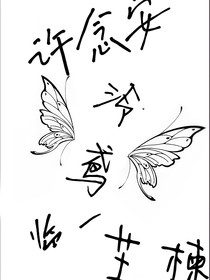第十七章 晨光里的归途
长途汽车在凌晨的薄雾里驶入服务区时,陈默正对着车窗呵气。玻璃上凝着一层薄霜,他用指尖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像裤兜里那块青石板上的刻痕。车窗外,国道旁的白杨树裹着霜花,在熹微的晨光里站成整齐的队列,像谁举着半透明的仪仗,护送着过往的旅人。
“休息十分钟啊!”司机扯着嗓子喊,拉开车门的瞬间,寒气卷着柴油味涌进来。陈默裹紧外套下车,脚刚沾地就打了个寒颤——镇子上的湿冷是缠人的棉絮,而这里的寒气是锋利的刀片,刮得脸颊生疼。
服务区的便利店亮着暖黄的灯,门口堆着半人高的煤堆,烟囱里飘出的青烟在风里拧成细麻花。陈默买了杯热豆浆,指尖攥着发烫的纸杯,忽然想起守井人总揣在怀里的粗瓷碗,碗里的药汤大概也是这样,能把寒气一点点从骨头缝里逼出去。
“小伙子,搭车啊?”隔壁桌的大叔啃着包子搭话,他面前摆着个掉漆的军绿色挎包,拉链上挂着枚褪色的五角星,“看你面生,不是这附近的吧?”
陈默点头:“嗯,从南边镇子过来。”
“南边?”大叔挑眉,“是不是有口老井的那个?前阵子听跑货运的兄弟说,那地方邪乎得很,半夜能听见井里唱歌。”
陈默的豆浆杯晃了晃,热液溅在虎口,烫得他缩了手。那点灼痛却不难受,倒像阿禾往他掌心塞过的那颗野山楂,酸里裹着点暖。“都是传言,”他笑了笑,“现在好多了。”
大叔咂咂嘴,没再追问,低头继续啃包子。陈默望着窗外的白杨,忽然发现最末那棵的树杈上,挂着个褪色的红布条,被风扯得笔直,像谁系上去的许愿符。他想起阿禾留在井底的玉兰花图腾,想起守井人胸口融进白光的伤疤,原来有些念想,不必说出口,也能顺着风,飘到很远的地方。
上车时,晨光已经漫过地平线,把天空染成淡橘色。陈默换了个靠窗的座位,阳光透过玻璃落在笔记本上,纸页里的草木香混着阳光的味道,变得暖暖的。他翻开本子,在写着“守井人”的那页停住——上次急着寄信,没注意到纸页边缘有行极浅的刻痕,像用指甲尖划的,歪歪扭扭凑成个“等”字。
车突然颠簸了一下,笔记本滑落在腿上,夹在里面的半张照片掉了出来。是爷爷年轻时的样子,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站在老槐树下,身后的井台边蹲着个穿粗布褂子的少年,手里捧着块青石板,侧脸的轮廓和守井人有几分像。
陈默的心跳漏了一拍。他把照片凑到阳光下,少年的手腕上隐约缠着圈红绳,和他裤兜里青石板碎片上的红绳印子一模一样。原来爷爷早就认识守井人,那些没说出口的往事,早就在时光里埋下了伏笔。
汽车驶离服务区时,陈默看见路边站着个放牛的老汉,手里的鞭子杆上刻着朵小小的玉兰花。老汉朝车挥了挥手,皱纹里盛着晨光,像守井人送他离开时的眼神。陈默忽然明白,有些守护从不是孤单的,就像井里的水会流遍整个镇子,那些温柔的执念,也会顺着时光的河,漫到每个需要的地方。
他把照片夹回笔记本,指尖抚过“等”字的刻痕,忽然想给姑姑再写点什么。不是“事已了”的简略,而是讲讲槐树下的信,讲讲井台边的草,讲讲那个绣着玉兰花的小姑娘——或许姑姑会懂,就像爷爷当年把笔记本交给她时,她眼里藏着的那些没说出口的了然。
车窗外的白杨渐渐稀疏,远处的村庄升起炊烟,像镇子上空那缕终于散开的黑泥。陈默摸出钢笔,这次没找空白的衬纸,直接在“阿禾”那页的指印旁,慢慢写下一行字:
“爷爷,我看见花开了。”
阳光落在笔尖,墨水干得很快,字里行间像是长出了小小的绿芽。陈默合上书时,裤兜里的青石板碎片轻轻硌了他一下,像谁在点头应和。
前方的路牌闪过“市区方向”的字样,陈默望着越来越近的高楼轮廓,忽然不那么慌了。那些埋在井边的过往,那些刻在石上、写在纸上的惦念,都变成了揣在怀里的暖,像爷爷说的,不是包袱,是能照亮前路的灯。
汽车拐过最后一个弯道时,陈默回头望了一眼。晨光里,来时的路像条闪着光的河,河对岸的镇子隐在薄雾里,只有那棵老槐树的影子,在记忆里站成永恒的模样。
他收回目光,摸了摸怀里的笔记本,掌心的伤疤已经不烫了,却像长了颗小小的种子,在心里生了根。或许到了春天,会开出朵和阿禾一样的玉兰花,在每个想起的瞬间,轻轻摇曳。
“下一站,终点站到了啊——”司机的喊声带着笑意,陈默拿起包,跟着人流往车门走。阳光穿过车窗,在他身后投下长长的影子,像条终于找到归宿的尾巴,稳稳地,跟着他走向晨光里的归途。
槐下红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人生之光
- 现实主义,映射当代大学生就业现实。
- 0.6万字6个月前
- 开局替身系统:我果然是真JOJO
- (JOJO同人+爽文+日常)论一个有着JOJO名字+★型胎记+替身能力的人究竟有多「HIGH」
- 2.0万字6个月前
- 关于我又穿越了这件事
- 我穿越了,穿成了一个奇怪的人。
- 0.6万字4个月前
- 我在火影忍者里修仙
- 阳泉意外穿越到火影忍者的世界里,在那时琳还没死,带土还没黑化,九尾之乱还没发生,水门和玖辛奈还在的年代,漩涡阳泉会以一己之力让忍界发生怎样的......
- 7.5万字4个月前
- 雾都——影噬
- 在终年被灰雾笼罩的雾都,人类被植入后颈的“情绪芯片”全天候监控:恐惧、愤怒、喜悦等情绪波动一旦超过阈值(红线60),就会被高压电流强制晕厥。......
- 2.2万字2个月前
- 国服四人寝
- 无限流无cp
- 0.6万字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