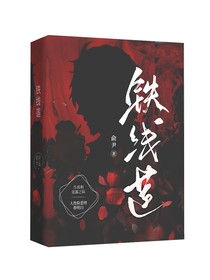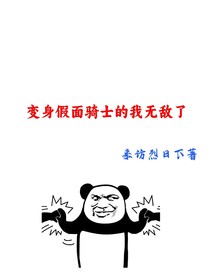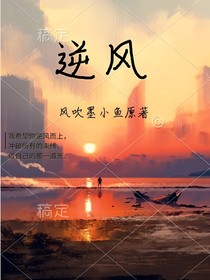梅痕绕指柔
第一场雪落时,新戏台的匾额被覆上薄薄一层白。陈砚踩着积雪去扫梅树,却见树干上的缠枝纹比往日更清晰,像有人用金线新描过。他伸手触碰的瞬间,指尖传来细碎的暖意,恍惚间竟闻见熟悉的胭脂香——与那年从沈玉茹戏服上沾到的,分毫不差。
展示柜前多了群研学的孩子。穿水红衫的小姑娘举着放大镜,正对着婚书的空白处细看:“陈先生,这里好像有字!”陈砚俯身时,忽见纸背的“茹”字在阳光下浮起,与“陈”字的墨迹渐渐相融,在空白处晕出朵小小的梅花,花瓣上还沾着点胭脂红,像谁害羞时的印泥。
开春那日,白发老人带了个锦盒来。里面是支银质梅花发钗,钗尾刻着极小的“砚”字。“这是祖母的嫁妆,”老人眼眶微红,“她说当年沈先生总借去戴,说钗尾的字和陈先生的名字正好一对。”发钗放进展示柜时,与那支带“茹”字的梅花簪相触,竟发出清越的轻响,像两段失散的旋律终于和鸣。
梅树抽新芽时,戏台来了位修古籍的老先生。他对着那叠戏本研究半日,忽然指着某页的梅花图:“这颜料里掺了胭脂和梅汁,是当年女子定情常用的法子。”他用棉签蘸了清水轻擦,淡粉色的笔迹慢慢显形——“待君九十九场戏毕,共赴梅下之约”,落款处的“茹”字,被圈在朵半开的梅蕊里。
台下的观众渐渐多了“老面孔”。有对金婚夫妇总坐在前排,说看《牡丹亭》时,总听见后台有女声跟着和,调子软得像浸了蜜。陈砚在整理旧麦克风时,发现线控里缠着根红绳,绳端系着颗褪色的珍珠,正是那双坤鞋鞋头缀的那颗,此刻在掌心温凉,像把岁月的念想焐成了珠圆玉润。
梅子黄时,小姑娘的奶奶拄着拐杖来了。老人颤巍巍从布包里掏出个青瓷碗,碗底烧着半朵梅花:“当年沈先生总用这个盛梅子汤,说陈先生唱完戏爱喝凉的。”碗沿的缺口处,还留着点淡淡的唇印,与戏本里沈玉茹画像的唇线,完美重合。
陈砚把青瓷碗摆在婚书下方,忽然发现展示柜的玻璃上,映出两个模糊的影子。穿青衫的男子正为红衣女子簪花,梅枝从两人肩头探过,花瓣落在婚书上,将那朵晕开的梅花染得愈发鲜亮。影子渐渐淡去时,有片花瓣飘落在陈砚手背上,竟留下个浅红的印记,与他衣襟上的梅痕终于连成一朵。
深秋的戏台格外热闹。新排的《梅下盟》首演,演到男女主角交换梅花笺时,台下忽然响起细碎的惊叹——满台的道具梅花竟在灯光下绽放,香气漫过整个戏园,与院外老梅树的芬芳缠在一起。陈砚站在侧幕,看见穿水红衫的小姑娘举着那支梅花簪,与白发老人衣襟上的半朵梅绣相照,忽然明白有些约定从不会过期,就像这梅树年复一年开花结果,把没说出口的圆满,都藏在了年轮与戏文里,等风过时,便轻轻唱给懂的人听。
碎镜中的她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金蝉九转世
- 你是否好奇唐僧前九次转世未能取得真经?你是否好奇孙悟空一跟头十万八千里,为什么不直接把唐僧带上西天?你是否想知道唐僧师徒初次见面,为什么三徒......
- 1.1万字7个月前
- 铁线莲
- 铁线莲--扼杀的希望危险悄然接近,究竟谁是凶手?被扼杀的希望是什么?
- 0.6万字6个月前
- 变身假面骑士的我无敌了
- 穿越成为假面骑士的林叶无敌了
- 3.7万字4个月前
- 逆风一
- 新人小警察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 0.7万字4个月前
- 火影:逆世瞳焰
- 鸣人携天生圣焰火莲,佐助觉醒黑轮眼,二者力量远超九尾与写轮眼,实力呈指数级暴增。自此,二人并肩闯忍界,以绝对的力量与不屈的信念,踏上独属于他......
- 3.2万字4个月前
- 亡者日记——遗书
- 这是写给自己的遗书,也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报复。是对善良之人的无端攻击,也是与恶人的同流合污是对至亲的无耻的背叛,也是针对自己的慢性自杀。打开......
- 2.2万字3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