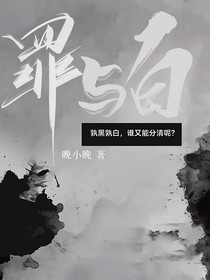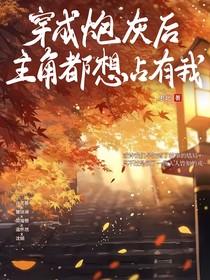摄政王的白月光:死了五年的他,竟藏在灾镇?
眨眼数个春秋已过,檐角的铜铃蒙了层薄锈,风过之时,再难发出清脆的响,倒像是谁在低低地叹息。
院中的那株海棠树又高了些,枝桠探过墙头,将斑驳的光影投在青石板上,恍惚间还能看见当年盛瑜倚着树干笑的模样——那时他总爱折一枝半开的海棠,塞进许宛手里,说这花配得上他眼底的光。
可如今,花开花落又几番,掌心再无海棠香。
深秋的雨缠缠绵绵下了整月,阶前的青苔吸足了水汽,在砖缝里疯长,像极了那些蔓延在心底的思念,扯不断,理还乱。
许宛独坐院中,指尖抚过石桌上那只盛瑜用过的玉盏,冰凉的触感顺着指尖漫到心口,惊起一阵细密的疼。
他望着檐外连绵的雨幕,恍惚间又看见盛瑜身披银甲,立于城门之下,回眸时眉眼带笑,声音穿透风雨:“阿宛,等我回来,陪你看这万里河山真正安定。”可那笑容碎在了那年寒冬。
城破之日,火光染红了半边天,他的尸骨混在万千忠魂之中,连块完整的墓碑都没能留下。而许宛,终究是独自坐在了权力的顶峰。
“呵……”许宛低低地笑了一声,笑声里裹着化不开的苦涩,“人死不能复苏,死去的人已经不在了。”他抬手按了按发紧的眉心,指腹触到一片冰凉,不知何时已沁了泪。“但活着的人,仍然要活着。”他曾不止一次想随他而去,可每当闭上眼,总能听见盛瑜最后的嘶吼——“守好这国,护好这民!”
想死?呵,也死不了。
他不是为了这所谓的盛世平安。这盛世之下,藏着多少白骨,他比谁都清楚。他是为了盛瑜拼死守护的那片国土,为了他剑指之处、拼死也要护住的百姓,也是为了那个坐在龙椅上的幼子——那是他亲手挑选的“傀儡”,却也是他必须护周全的象征,是他与盛瑜未竟之志的延续。盛瑜的血洒在了那里,他便要替他看着,看那片土地上的人安居乐业,看炊烟袅袅,岁岁平安。
雨停时,天已破晓。许宛起身拂去衣上的凉意,铜镜里映出一张清瘦却坚毅的脸,眼底的红血丝未加掩饰,下颌线绷得紧直,那是常年居于上位的冷硬。他随手将散乱的衣襟系好,换上一身玄色蟒纹朝服,腰间玉带扣得一丝不苟,推门而出时,廊下侍立的内侍们齐刷刷跪了一地,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太极殿上,百官肃立。户部尚书颤巍巍地出列,花白的胡子抖得厉害,声音带着难掩的焦急:“摄政王殿下,宁兴郡下属的清河镇遭了百年不遇的洪灾,堤坝溃决,良田尽毁,百姓流离失所,恐生民变啊!”
殿内一片寂静,连香炉里的烟都似凝固了。清河镇偏远贫瘠,洪灾过后必有瘟疫,谁都清楚这差事是块烫手山芋。更重要的是,如今朝政尽出摄政王之手,连五岁的小皇帝都得看他眼色,谁敢在这种时候触他霉头?
许宛站在龙椅之侧的蟠龙柱旁,比那金銮宝座更有压迫感。他眸光微沉,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玉带——清河镇,那是盛瑜的 一直想去却没去的地方 。
“本王,亲往清河镇赈灾。”他上前一步,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在空旷的大殿里掷地有声。
满朝文武皆是一怔,不少人偷偷抬眼打量他。谁都知道摄政王这些年深居简出,朝堂之事尚且由心腹代劳,如今竟要亲赴灾地?有人暗自揣测,是为了收拢民心,还是另有隐情?
龙椅上的小皇帝正把玩着手里的玉如意,闻言抬起头,奶声奶气地问:“宛哥哥要走吗?带上朕好不好?”
许宛回眸,脸上染上一丝复杂之色,小皇帝身上流的血无疑令他感到厌恶 ,但幼子无辜,又是他从小看到大的孩子 ,他既做不到对他特别亲近,但无法做到放任不管 ,便对着小皇帝微微颔首:“陛下乃国之根本,不可轻动。待臣归来,给陛下带清河镇的糖画。”
小皇帝立刻笑了,拍着小手道:“好!那宛哥哥要快点回来!”
“臣,遵旨。”许宛垂下眼,掩去眸底的复杂,转身时,声音已恢复了惯常的冷厉,“传本王令,调京畿大营五千兵力护粮,三日内启程。”
许宛的动作极快,三日内便点齐了人手,押着粮草药材奔赴清河镇。一路风雨兼程,抵达时,镇子已是一片狼藉,浊黄的洪水退去后,留下满地淤泥与腐臭,灾民们蜷缩在临时搭起的棚子里,面黄肌瘦,眼中满是绝望。
他勒住马缰,玄色披风被风掀起一角,露出内里银线绣的暗纹。看着眼前景象,他眉头未皱,只对身后的粮队扬了扬下巴,声音冷得像冰:“开仓,先让百姓喝上热粥。敢克扣一粒米的,斩。”
接下来的半月,他几乎是以命相搏,却也带着不容置喙的强硬。白日里踩着及踝的淤泥指挥加固堤坝,哪个士兵敢偷懒,他眼神扫过去便能让人脊背发凉;夜里在临时营帐中核对账目,发现有官员私藏药材,当即下令拖出去杖责四十,次日便挂在镇口示众,震慑得所有人不敢有二心。他沙哑的嗓音喊得发不出声,便用眼神示意,那目光比任何话语都更有威力;高烧到浑身滚烫,裹着厚毯仍在发抖,却硬是撑着不肯躺倒——他是摄政王,是这方天地的实际掌控者,不能倒下。
如此半月有余,清河镇的灾情总算稳住了。瘟疫未曾蔓延,百姓们有了吃食,眼中渐渐有了生气。许宛看着重建的雏形,紧绷的神经终于松了些,决定次日启程回京。
临行前夜,月色尚可。他带着两名随从在镇上巡察,走到街口时,忽有个约莫五六岁的孩童从巷子里冲了出来,一头撞在他腿上。孩童“哇”地一声哭了出来,许宛下意识地弯腰去扶,指尖刚触到孩子的衣角,就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阿念!”
一个女子的声音传来,带着几分急切。许宛抬头望去,只见一个身着粗布衣裙的女子快步走来,看着约莫二十出头,正是二十二岁左右的年纪。她头上裹着一块灰布头巾,脸上覆着一层薄薄的面纱,遮住了大半容貌,只露出一双眼睛。
那双眼……许宛不知为感到有些熟悉 …。
“对不住,对不住大人!”女子快步上前,将地上的孩子拉到身后,屈膝福了福身,声音带着歉意,甚至微微发颤——许宛身上的压迫感,即便是粗布麻衣也能感受得到,“小儿顽劣,冲撞了大人,还请大人恕罪。”
“无妨。”许宛的声音有些发紧,他盯着那女子的眼睛,试图从中找到更多熟悉的痕迹,“孩子没撞疼吧?”
“不碍事的,多谢大人关心。”女子说着,便拉着孩子要走,脚步急促得几乎踉跄,仿佛多待一刻就会引来祸事。
许宛看着她的背影,心中疑窦丛生。
他不动声色地对身旁的随从使了个眼色,那随从是他多年的心腹,立刻会意,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
回到临时行辕后,随从低声禀报:“殿下,属下跟着那妇人去了她家,是镇上最偏僻的一间破屋。她家里还有个男人,听街坊说,是个腿瘸眼瞎的货郎,前年逃难来的,夫妻俩平日里靠着给人缝补浆洗过活,看着倒是寻常百姓。”
“寻常百姓?”许宛指尖敲击着桌面,发出沉闷的声响,眉头紧锁,“再去查。查她的来历,查她何时到的清河镇,查她丈夫的底细,一丝一毫都不要放过。”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狠厉,“若有隐瞒,不必请示,先拿下。”
可三日后,随从再次回报,脸上带着难色:“殿下,查不到。那妇人像是凭空出现的一般,五年前突然带着男人来到镇上,孩子也是后来不知道从哪儿带来的 ,身份户籍全无,邻里只知她姓苏,其余一概不知。那男人更是常年不出门,据说眼睛是生下来就瞎的,腿是后来被砸伤的,除了她,没人见过他的样子。”
许宛沉默了。查不到任何痕迹,本身就是最大的疑点。尤其在清河镇——盛瑜一直想去的地方 ,五年前,正是盛瑜战死的那一年。
他望着窗外渐沉的暮色,指尖微微颤抖,那是极少有的失态。是他吗?真的是他妈?他还活着吗?
不可能。许宛用力闭了闭眼,再睁开时,眼底只剩一片冰寒。他向来看似温和可当年能弑君夺权,手段岂会手软?一旦触及与盛瑜相关的疑云,那蛰伏的狠厉便会瞬间出鞘。
他望着清河镇的方向,声音冷得像淬了毒:“备车,回京。”
只是这一次,他的行囊里,多了一份挥之不去的牵挂,更藏着一场即将掀起的惊涛骇浪。
晓流年:暗恋是带刺的救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拜见司尊:不如做本尊的药宠吧
- 【原创作品,禁止抄袭搬运】她本是苗疆的天才少女,也很快会成为圣女,可是一朝间,她的族人和至亲都死光了,从此便背负上了沉重的仇恨,使本就淡漠的......
- 6.0万字9个月前
- 罪与白
- 传说中,有一位神,神润泽众生,极其耀眼。可有一天,神犯下大错,被贬人间,世人本以为神会重回,却久久成了传闻,世人谴责神的错误,神渐渐成为阶下......
- 1.2万字6个月前
- 倾世双骄之冷少的掌心娇
- 陈国京都,繁华喧嚣。柳嫣,柳相府中不受宠的庶女,温婉灵秀,才情出众却隐忍内敛。冷逸尘,冷家大少,冷峻孤傲,手段狠辣,令人敬畏。一场花灯会,两......
- 1.1万字6个月前
- 穿成炮灰后主角都想占有我
- 意外穿书成炮灰后结果没曾想还是个狗血剧情大概就是女主是宗门小师妹而且是个万人迷的设定一个清纯小白花把我们的师兄和徒弟迷的神魂颠倒原主想了个自......
- 0.3万字5个月前
- 斩情锁缘
- 【首发平台,侵权必究❗️】作为小说迷的你,竟然意外穿书了?!(我*¥%…@$你…@$%¥****!)…由于现实世界的灵魂和肉身被毁,所以系统......
- 0.1万字3个月前
- 百惠子
- 本文以亲情宫斗为主
- 3.2万字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