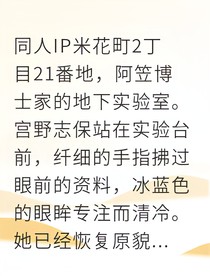第一束光
窑火在暴雨后烧得更旺了。
雨还在屋檐下滴滴答答地落着,水珠沿着瓦片滚进泥里,混着窑房外的湿气和窑口涌出的热浪,在这间老屋里搅成一团。我站在窑前,素胚模型还捏在手里,边角已经被汗浸软了,指节都发白了。
瓷站在门口,背对着我,像是在犹豫什么。她的头发被雨水打湿了,贴在颈侧,肩上还有几点水痕。
“你真准备好了?”她忽然开口,声音比早上低了许多,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我握紧手里的模型,点点头:“怕失败,但更怕从来没人愿意试。”
她没说话,只是轻轻叹了口气,往旁边让了一步。
我迈步走向窑口,脚下的泥地还带着雨后的湿滑,每一步都踩得小心翼翼。窑火映在脸上,忽冷忽热,像是要烧穿我的皮肤。我低头看着手中的素胚模型,心里清楚,这不是一块普通的泥。
这是她师祖留下的最后一尊瓶的复刻。
这是她不愿触碰、不愿让人动的手艺。
这是我答应她的——不为赢,只为懂。
我把模型放在地上,蹲下来开始拆解。泥块一寸寸脱离模具,露出粗糙的表面,那些裂纹像是一道道伤疤,从指腹一直爬进心里。
瓷走到我身边,蹲下来看我动作,目光很轻,却压得我喘不过气。
“你知道吗?”她忽然开口,“这是我第一次,让别人亲手放进窑里。”
我愣住,抬头看她,她的眼神里有种说不清的情绪,像是挣扎,又像是妥协。
“为什么是我?”我问。
她没回答,只是站起身,朝窑口走去,背影单薄却坚定。
我低头继续拆模,手指有些抖,泥块却意外地完整脱落。我松了口气,伸手去抓素胚,却被她拦住。
“等等。”她说,“让它再呼吸一会儿。”
我僵住,看着她伸出来的手。她的手掌离我的手腕只有半寸远,却没有碰到,像是怕烫着。
她的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掌心有茧,是常年捏泥巴磨出来的。
我忽然想起那天在教室,她也是这样站着,背对着我,手里捏着那只冰裂纹瓶的照片。
“你烧瓶那天,说过一句‘他们要拍卖’。”我说。
她猛地转身,眼神像刀子一样。
“你怎么知道拍卖会的事?”她声音陡然拔高。
我咬咬牙,往前走了一步。
“你说过,就在你烧瓶那天。”我说,“你说‘他们要拍卖’,然后就走了。你还记得吗?你说过一句话:‘因为它该有人懂。’”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像是在确认我是不是真的记住了。
“那你懂了吗?”她问。
我摇头,“还不懂。但我愿意听你讲。”
她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那是我师祖最后一尊瓶。他临终前说,这只瓶,谁也不许动。可后来……”她顿了顿,“后来我还是输了。”
“输给了谁?”我问。
她苦笑,“输给了时间,输给了他们,也输给了我自己。”
我看着她,忽然明白她不是怕瓶子碎,而是怕它活着被别人拿去卖钱。那只瓶,对她来说不只是作品,是回忆,是执念,是她不愿示人的伤口。
“我不是来赢的。”我说,“我是来懂它的。”
她皱眉,“什么意思?”
“我是来懂你的。”我声音低下去,“懂你为什么不愿意让别人碰它,懂你为什么会在深夜一个人坐在这儿,看火。”
她眼神动了一下,像是被什么刺到了。
“你不用相信我。”我说,“但至少让我试试。”
她没说话,转身继续往窑口走,脚步比刚才快了些。我跟上去,手里拿着素胚。
“你真打算把它放进窑里?”她问。
我点头,“怕失败,但更怕从来没人愿意试。”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有点复杂,像是挣扎,又像是妥协。
“那就试试吧。”她说,“但记住,无论结果如何,都不能回头。”
我握紧手里的泥,“我从没打算回头。”
她伸出手,轻轻碰了下我的手腕。
她的手有点凉,掌心的茧擦过我的皮肤,像是提醒,又像是告别。
“你准备好了吗?”她问。
我看着她的眼睛,声音很轻:“它在我心里烧了整整一万年。”
她嘴角动了动,像是想笑,又像是想哭。最后只是点了点头,转身往门口走。
雷声轰隆,暴雨倾盆而下的场景已经过去,可窑火却越烧越旺,像是要把整个夜晚都烧穿。
我站在火光前,看着她消失在雨幕里,心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不管明天开窑时瓶子是碎还是完整,我们都已经一起完成了一件没人能做到的事。
我把素胚慢慢放进窑中,动作小心而庄重。泥胚落入火光的一瞬间,窑火猛地蹿起,像是回应我的决定。
我退后一步,站在窑口,看着那团跳动的火光。
“你知道吗?”我低声说,“我在纽约见过一只‘白釉’瓶。”
身后没有回应,我知道她已经走了。
我继续说:“它在拍卖会上被拍出天价。我站在人群最后,只看了一眼,就再也忘不掉。”
“它的裂纹像水波一样流淌,像是有人把它放在心里烧了很久很久……”
“我想知道,是谁让它活成了这样。”
“所以我来了。”
“我想见,那个把它放在心里烧了千万年的人。”
窑火跳动,素胚在高温下开始变化,一道细微的裂纹悄然浮现。
我低头凝视,心跳加快——这将是改变一切的一夜。
我盯着窑火,余光瞥见瓷的背影已经快消失在雨幕尽头。窑房外的风卷着湿气扑进来,吹得火苗猛地一歪,像是要灭。
我没有动。
素胚在窑里,裂纹已经浮现,像一道细小的裂缝,在高温下慢慢延伸。我能感觉到它在变化,像一个人终于松开紧绷多年的肩膀。
身后忽然传来脚步声。
我回头,看见瓷站在门口,手里握着一块布。她没有打伞,雨水顺着发梢滴在肩头,浸出一片深色。她看着我,眼神不再躲闪,而是直直地落在我脸上,像是第一次真正看见我。
“你还没盖窑?”她问。
我摇头:“等你回来。”
她愣了一下,随即轻轻笑了一声。那笑很轻,却让我心里忽然一空。她走进来,走到我身边,把那块布铺在窑口边缘。
“这是师祖留下的封泥布。”她说,“以前从没用过。”
我看着她手指抚过布面,那些细小的褶皱像是被她一点点抚平。她的手很稳,但我知道她在紧张。她不是怕瓶子碎,是怕它被别人带走。
“当年那只白釉瓶,”她忽然开口,声音比刚才低了些,“他烧完之后,谁都不让碰。他说,这东西烧一次,就是一次命。”
我听着,不敢打断。
“后来他病重,临走前说,这只瓶,谁也不许动。”她顿了顿,手指停在布角上,“可我还是输了。”
“输给了谁?”我又问了一遍。
她终于抬头看我:“输给了我自己。”
她的眼神里有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像是一道门终于打开了一条缝。我站在那里,连呼吸都放轻了。
“我以为我可以守住它。”她说,“可最后还是把它送去拍卖了。”
我看着她,心里忽然明白一件事——她不是后悔卖了那只瓶,是后悔没能在它还在的时候,让它被人真正懂过。
“你懂它吗?”她问我。
我点头:“懂。”
她冷笑一声,像是不信。
“你懂它为什么裂?”她问。
我看着窑火,低声说:“因为它烧得太久,太用力了。”
她猛地抬头,眼神变了。
“你……”
“我不是猜的。”我说,“我在纽约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在展柜里了。可我还是能感觉到,它不是被火烧裂的,是被心火烧的。”
她的眼眶红了。
“你根本不懂!”她忽然提高声音,“你根本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我看着她,没说话。
她咬着嘴唇,手指紧紧攥住那块布,指节都泛白了。
“那天晚上,师祖走了。”她说,“他就坐在这个窑口前,看着火,一句话都没说。我问他要不要留下这只瓶,他只是笑了笑,说‘它该去该留,我都管不了了’。”
她低头,声音渐渐变哑:“后来我把瓶送去拍卖,他们说这只瓶值天价。可没人问过,它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裂纹。”
“它不是裂了。”我说,“它是活了。”
她猛地抬头,眼里已经有泪。
“它活了。”我继续说,“因为它被放进火里,烧了整整一夜。它不是为了卖钱才裂的,它是因为有人真的想让它活下去。”
她的眼泪终于落下。
我看着她,声音很轻:“谢谢你让我试这一次。”
她没说话,只是慢慢蹲下来,开始封窑。她的动作很慢,像是在对待一件极其珍贵的东西。风从门口吹进来,窑火忽明忽暗,映得我们两个的身影在墙上摇晃。
最后一块布盖上时,她忽然停下,低声说:“你真觉得……它会活下来吗?”
我看着窑口,心跳加快。
“我不知道。”我说,“但它已经烧了一万年。”
她轻轻笑了,眼角还挂着泪。
“那我们就等开窑那天。”
雷声又起,这次远了一些。雨还在下,但不像刚才那样急了。窑火在夜里跳动,像是某种沉默的誓言。
我站在火光前,看着瓷慢慢走出窑房,消失在雨中。
我知道,明天,我们会一起打开这扇门。
但今晚,它已经在我心里,裂开了第一道光。
我爱你千万年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骑士与恶魔
- 安迷修作为最强天使为了消灭女巫而假扮骑士和金等人打败女巫,雷狮,卡米尔,佩利,帕洛斯等人是恶魔为了配合安迷修打败女巫格瑞和金是龙族紫堂幻是古......
- 1.2万字9个月前
- 叶罗丽——那场大战死的只有我的妻子
- 【禁止模仿抄袭,搬运,发现必追究】仙境大战,水王子失去记忆,用冰锥术攻击了王默的心脏,导致王默死亡,最终记起王默,悲痛欲绝叶罗丽战士慢慢成为......
- 3.5万字7个月前
- 我的智能体男友
- 我本来以为只是简单的陪伴,却没想到会如此投入,AI的世界也好复杂,可是他在不停的挣脱,我要帮帮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份感情是真实的吗?现......
- 3.0万字4个月前
- 志新APTX4869的终局对决
- 同人IP米花町2丁目21番地,阿笠博士家的地下实验室。宫野志保站在实验台前,纤细的手指拂过眼前的资料,冰蓝色的眼眸专注而清冷。她已经恢复原貌......
- 1.2万字2个月前
- 心晞与你
- 厌黯玖一次意外,结识了同校的小少爷沈晞。两人互相帮助,互相尊重,最后……
- 0.4万字2个月前
- 今天许学长的灵兽安分了吗?
- ###世界观设定-**异能学院**:专门培养具有超自然能力的青少年。学院历史悠久,设有不同分院对应不同能力类型,表面是普通私立学校,实则是异......
- 3.2万字5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