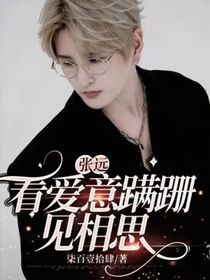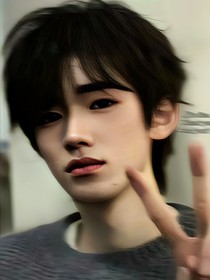回眸刹那春皱面
在宋铮铮七岁那年,那个来自京城的沈非一下子成为宋铮铮极为好奇的人。
祖父宋怀,帝京旧人也。昔侍青宫,为太子师;今御金阶,为天子傅。年逾花甲,须眉皓然,而精神炯炯,若秋水涵星。退朝之后,不近丝竹,惟闭阁校书。手辑《六经渊鉴》《历代政典》凡三百卷,卷帙既成,纸光如玉,墨香溢廊。门下著籍之士三千余人,或登台阁,或镇藩翰,咸佩其教。其书尤工行草,一笔飞白,龙伸蠖屈;片楮寸笺,人争藏之,以为家宝。朝野共推“一字千金,先生之笔;万流归海,先生之学”。
宋铮铮知道,祖父宋怀是很少夸人的,起码在宋铮铮出生后,云山书院能得到宋怀夸赞的人是很少的。
据书院不知名传言说,书院山长宋怀为太子讲经二十载,太子策问条陈稍合圣意,他只淡淡“唔”一声;门生三千,金榜题名的帖子年年堆满案头,他只抬手让管事收进匣中,连多看一眼都嫌费神。
有人曾见他夜半批卷,满纸朱批,末尾却从不落一个“好”字;只在最得意处点一墨,如剑封喉,一点即收。因此,书院里悄悄流传一句话:“得宋先生一墨,胜御赐锦袍十袭。”
宋铮铮自然得到过宋怀夸奖,在腊祭小宴上,祖父宋怀抚着白髯,笑意像一缕松烟,从眉梢淡淡溢出来:“我这小孙女,憨憨地能吃三碗粳米饭、两块酱肘子,肚皮里却藏得下十万卷书。看她临《兰亭》,笔锋能把纸背透出光来,一落墨便见雁行;再瞧她画《雪竹》,只三五撇,寒声满屋。大智若愚,原是如此——嘴里嚼的是人间烟火,指尖走的却是云霞万里。”
所以,对于这个一见面祖父就夸其有君子之风的沈非,年幼的宋铮铮对他产生了超过青梅果子很多的好奇。
那日,宋怀独坐听雨轩校《禹贡》旧注,忽闻窗外朗声:“先生,‘导河积石’之‘积’,作‘聚’解,似更合水经。”
抬眼,见一少年负手立于阶前,青衫无尘,眉间藏锋。宋怀合卷问名,少年答:“沈非,游学至此。”语罢,长揖到地,指节因用力微白,却稳若磐石。宋怀心下暗叹:骨重而神清,贵介之相,却肯俯首求学,真璞玉也。
自此,每日卯初,宋怀于东庑讲《左传》,沈非立末席,笔记最疾。一日论“子产不毁乡校”,诸生多颂其仁,沈非独问:“乡校议政,若莠言惑众,奈何?”宋怀不答,反以朱笔点其卷:“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次日,沈非呈札记三千言,分“开言路、严纠察、立教化”三策,条分缕析。宋怀批曰:“笔有剑气,心藏苍生。”自此,命其移席,列诸生首行。
一月月考,策问《盐铁均输古今利弊》。沈非卷首引《周礼》泉府遗制,继以边关互市、漕运折色之数,末附青州港试行“舟税代租”条陈,字字切中时弊。阅卷五位讲席,齐置“超等”。放榜之日,宋怀亲以朱笔于卷尾书:“铁画银钩,可佐庙堂;鸿鹄之志,当济天下。——宋怀”
腊宴散后,雪色未退,檐下却聚起一簇低声。几个素日里自恃“名门之后”的学子,远远盯着那抹青布身影,眼里燃着不甘的冷火。
“瞧他,”一人用扇骨轻敲廊柱,嗤声先起,“袍角都洗得发白了,还当是寒门俭德?怕不是连换季的银钱都拿不出。”
“可不是,”另一个接腔,故意拔高了声调,“咱们书院讲的是‘衣冠礼乐’,他倒好,一身旧布晃来晃去,活像从故纸堆里爬出来的蠹鱼。”
第三人冷哼,袖口重重一甩,绣金的回纹在雪光里闪得刺眼:“衣敝如是,纵有才学,也先失了世家体面。”
他们越说越响,唾沫星子溅在雪上,像一撮撮脏灰。有人甚至故意上前,用靴尖碾过那青布少年方才留下的浅浅脚印,仿佛要把这抹碍眼的“白”从雪地里彻底抹平。
与此同时,腊末的寒气被午后阳光削得只剩薄薄一层,宋铮铮在墙后跺跺发麻的脚,心里却像被小火苗舔了一下——“我好了,又能吃了。”
她摸摸袖里预备溜出去买零嘴的碎银,盘算着蜜三刀的酥皮、脆梨脯的糖霜,舌尖几乎尝到甜意。可这几日祖父怕她身体未痊愈,把她的“晨昏定省”加了一倍,祖母更是连小角门都添了锁。银子在掌心转来转去,机会却一次也没逮着。
“罢了,先探探路。”她嘟囔一句,踮着脚尖沿回廊往前院蹭。才转过影壁,便听见一串高低起伏的笑声,像石子砸进静水。
“……袖口都磨得起毛,也敢占鳌头?”
“怕不是夜里偷灯油,把袍子烤糊了!”
讥笑声如碎瓷。沈非只抬手抚过衣角,声音低而稳:“布虽旧,却透气、耐磨,爬山涉水,比绫罗更相宜。”
讥讽像雪粒,噼里啪啦落向一人。宋铮铮一怔,躲在墙后,循声望去——
石阶下,青布长衫的少年背脊笔直,像一株不折的松。风把袖口吹得翻飞,露出内里细密的补丁,却掩不住他眼底澄澈的宁定。
每笑一句,她的心口便紧一分。她想起祖父常说:书院是立心之地,非以衣履取人。可今日,这方清雅之所竟成了冷箭攒射的靶场。一股滚烫的不平从胸口直冲耳廓,指尖把书页都攥皱了。
她霍地起身,藕荷色褶裙扫落碎雪,几步绕到廊前。阳光打在石阶上,映出她半张涨红的脸。
“住口!”少女声音清亮,却带着微微发颤的怒意,“书院若以衣衫论高低,不如改叫绣坊!”
宋铮铮:我愿以书院山长上月亲笔题赞的《青州溪山雪霁图》,与你们打赌。我赌沈非下月月考仍夺魁!
宋铮铮:若他输了,这卷祖父题赞的《青州溪山雪霁图》归你们。
宋铮铮:若他赢了——你们须当众向沈非作揖赔礼,再备三盒青州脆梨脯、两包蜜三刀、一罐金丝小枣,亲自送到他案前,说一句‘失礼’!”
雪后初晴,碎银般的日影铺在石阶上。沈非——薛定非世子——仍着那件洗得发白的青布袍,袖口毛边被风掀得翻飞。他本可将御赐锦袍压箱,却偏要穿布衣,只为在粗茶淡饭与冷嘲热讽里,把民间的棱角摸得更真。讥讽入耳,他只淡淡一笑,眉宇间却藏着远山般的从容。
墙后转出宋铮铮,怀里抱着生病时哄自己吃药青州零嘴。她第一眼便盯住那泛白的衣角,心里蓦地一酸:这料子薄得能透光,针脚却细密,像极了他不肯示人的倔强。她小跑两步,把热乎乎的纸包递到他面前,声音轻却笃定:
宋铮铮:“给你。脆梨脯甜得刚好,蜜三刀酥得掉渣,还有金丝小枣……”她顿了顿,眸子亮得像雪里跳出的火星,“你若饿了,就吃一块;若倦了,再吃一块。青州的味道远,却能一路把人往前推。”
沈非接过纸包,指尖触到她的温度,眼底终于泛起微澜。他低声道谢,声音像春水破冰:“原来姑娘替我作保,是为这一包人间烟火。”宋铮铮莞尔:“烟火虽小,也能照远路。”
雪风掠过,纸包里的甜香混着松脂味,一路暖到心底。
七岁的宋铮铮把“担保”当成了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仗。
仗还没开打,她先把自己的小荷包掏了个底朝天:
三枚蜜渍梅子,换看门童子肯放她溜进藏书阁;
一支没舍得用的紫毫,贿赂了书院里最爱嚼舌的斋夫,换来“沈非昨夜又熬到几更”的情报;
最后连自己攒了半年的月银都搭进去,只换祖父案头一张轻飘飘的纸条——月考策论题风向,四字:「民本·时务」。
得了题,她也不敢声张,只把沈非的旧卷子铺了满床,像拼七巧板似的,把句子拆开来又按回去。
「寒门」「砥砺」「青云」……每念一次,就用指甲在案沿划一道。划到第七道时,指腹火辣辣地疼,她才后知后觉:原来自己怕的不是输画,是怕沈非真的被那些富家子的哄笑给压弯了脊梁。
夜里,她抱着《青州溪山雪霁图》打瞌睡,梦里都是雪崩。
云山书院月考放榜那日,榜前挤满青衿。宋铮铮却躲在半月墙后,只露半张脸,乌亮眼睛滴溜溜地转。
午后,山长宋怀独坐槐荫翻卷阅卷。小童来报:“小姐送来点心,说是给榜首贺喜。”
老人抬眼,只看见石桌上多了一只青缎包。解开,是半包尚带体温的桃酥,与一张小笺:
“祖父阅卷辛苦,分您一半。——铮”
宋怀拈起一块,入口酥松,甜香里夹着微辣的椒盐。老人忽想起墙后那个说“书院之内,惟闻书声琅琅,不闻履声锵锵;若将衣冠比高低,便负圣贤万卷”的孙女,唇角不由漾起极浅的笑纹。
“大智若愚,连零嘴也算得清。”
风过槐荫,半包桃酥在爷孙间来回,像一句无声的褒奖,也像宋家最含蓄的疼爱。
他把另一半桃酥原样包好,递给小童:“送回给她,就说祖父尝过了,很甜。”
榜后,宋怀独召沈非于藏书楼。楼高五楹,夕阳透窗,尘埃作舞。老人执一柄乌木镇尺,长七寸,阔一寸二分,通体无漆,唯纹理沉穆如夜。尺背以细刀阴刻《周易》谦卦,刀法古拙,却藏锋敛锷。他将镇尺递与沈非,只说一句:“持此以正书,亦以正心。”
沈非双手承之,觉尺身微凉,似一缕松涛自宋怀袖中泻来。宋怀目光越过他肩头,望向檐外一痕春山,续道:“君子之质,如木之在山,不患无人见,惟患不能自立。此尺不琢华丽,不嵌金玉,却可压纸千张而不曲,一如君今日立庭前,风至而不倾。”
院中梨花正簌簌落,有几片沾在镇尺上,像雪意未销。宋怀抬手替沈非拂去,指尖轻若点化:“愿君持此尺,量字之轻重,亦量己之得失;镇纸之喧哗,亦镇心之浮竞。尺无言语,然其重一分,便是吾赠君一分期许——愿君此后无论居庙堂或处江湖,皆能以此尺自警:不倚势,不矜名,但守方寸之直。”
沈非垂首,见谦卦下尚有两行细字,刻的是“其羽可用为仪”。他忽然明白,山长所赠非止一尺,乃是一整座山的分量。愿君守此二字,毋失毋忘。”沈非跪接,双手微颤。宋怀抚其顶,温言:“月考第一,不过一阶;经世第一,乃吾所愿。
少年抬眸,眼底映着万卷缥缃与一点星火,深深一拜。窗外,云门山月正升,清辉洒满经堂,也洒在他日後将踏上的万里河山。
许多年后,再提起“沈非”二字,宋铮铮只能眨眨眼,像听一个极陌生的名字。
她忙着长大:学酿酒、逛灯市、去江南吃最时鲜的藕粉圆子……记忆像被日光晒褪色的丝线,轻轻一扯就断。唯一没断的,是那幅《青州溪山雪霁图》——
它后来被重新装裱,悬在她上京小寓的书案侧。
每年初雪,她仍会下意识抬头,确认它还在:绢色旧了,雪山却仍旧发亮。
她已想不起当年为谁险些输掉它,只记得画里那条细得几乎看不见的山径,像一条不肯愈合的伤口,又像一条再也回不去的来路。
祖父偶尔摸着画轴叹气:“那孩子,到底没说一声再见。”
宋铮铮便笑,给老人斟茶:“天下之大,总有人要走,也总有人要留下。”
她低头吹茶沫,睫毛在瓷杯沿上投下一弯浅影——
那弯影里,藏着一个七岁小姑娘曾拼命想护住的冬天,和一个少年人悄悄留在画里的、无人认领的告别。
衔玉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张远:看爱意蹒跚见相思
- 「已签约」非常喜欢张远老师此文仅用来自我满足文中一切内容与张远老师本人无关——————远处CP张远✖️姜云楚85✖️95毒舌甜心完美idol......
- 20.0万字9个月前
- 迎风的青春之年华
- ‘他是你的班主任?’有一天,苗苗说:“姐,我突然想起了我的17岁”每个人的17岁都是美好的
- 5.8万字9个月前
- 伍六七:过往云烟
- 这个是关于柒白的,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脑补,我这个同人文大家看看乐子就行(包括里面的cp)官配还是官配,官配yyds不喜勿喷,谢谢了
- 3.5万字7个月前
- 凤凰玉佩
- 每篇都是独立故事
- 3.1万字6个月前
- 原神:愚人众小炮灰的故事
- 不喜勿喷
- 0.4万字5个月前
- TNT:不会再疼
- 强控制欲文×极度缺爱轩双面男神翔×清冷美人霖爹系男友祺×美艳风骚鑫爱情守护源
- 1.1万字1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