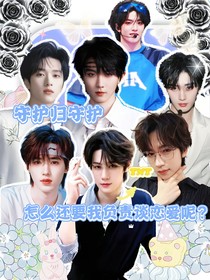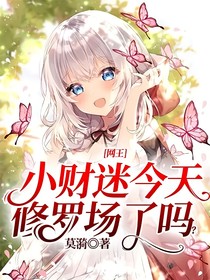第一章
民国二十五年,上海。
法租界霞飞路上的霓虹刚舔亮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一辆黑色奥斯汀轿车悄无声息地滑过街角。后座的费渡指尖夹着支未点燃的雪茄,车窗开了条缝,混着晚风飘进来的,有百乐门隐约的爵士乐,有黄包车上铜铃的叮当,还有远处码头隐约传来的汽笛声。
“先生,前面好像堵了。”司机老李放缓车速,朝前方努了努嘴。
费渡掀起眼皮。视线越过攒动的人头和洋车,落在街口那圈刺眼的白光灯上——是巡捕房的人。几个穿着藏青色制服的巡捕正围着什么,警戒线把看热闹的人群拦在外面,像圈起了一块淌着血的伤口。
“绕路吧。”他收回目光,重新靠回椅背,声音里听不出情绪。指间的雪茄转了半圈,烟草的醇厚气息在狭小空间里弥漫开来。
老李却有点犹豫:“好像是出了命案,听说是……是洋行里的人。”
费渡这才微微侧过头。他今天穿了件银灰色的乔其纱衬衫,领口松着两颗扣子,露出一点精致的锁骨,与这乱世里的烟火气格格不入。“哪个洋行?”
“好像是……法国人的那个利通洋行。”
利通洋行。费渡指尖的动作顿了顿。上周他还在沙利文咖啡馆见过该行的襄理,一个叫皮埃尔的法国人,据说正负责一笔从越南运来的“特殊货物”。
就在这时,警戒线里忽然走出个身影。男人穿着熨帖的深色中山装,没系领带,袖口挽到小臂,露出结实的手腕。他正低头跟身边的巡捕说着什么,侧脸线条硬朗,眉骨很高,眼神在夜色里亮得像淬了火的钢钉。
是骆闻舟。
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探长,以破案快、手段“野”闻名。费渡见过他几次,大多是在一些不怎么愉快的场合——比如某次军火走私案的现场,又或者是某个达官贵人的私人派对上,骆闻舟带着人来“例行检查”,目光扫过他时,总像在看一块需要掂量掂量成色的可疑古董。
此刻,骆闻舟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忽然抬眼朝这边望过来。视线精准地穿透车流,落在奥斯汀的车窗上,与费渡的目光撞了个正着。
费渡没躲,反而冲他极淡地勾了下唇角,像在打招呼,又像在嘲讽。
骆闻舟的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随即转回头,冲手下摆了摆手。那动作利落干脆,带着不容置疑的气场。
“开车吧。”费渡重新闭上眼睛,将雪茄凑到鼻尖轻嗅,“去静安寺路。”
老李应了一声,打转方向盘。车子缓缓驶离街口,费渡从后视镜里看到,骆闻舟正蹲下身,手指小心翼翼地拨开地上的什么东西,侧脸在白光灯下显得格外专注。
“先生,”老李忍不住多嘴,“利通洋行那案子,会不会……”
“与我们无关。”费渡打断他,声音依旧平淡,“法国人丢了东西,自有巡捕房去查。我们做正经生意的,少掺和这些。”
话是这么说,他指尖的雪茄却转得更快了些。车窗外,霞飞路的灯火如同流动的星河,映在他眼底,却没留下半分暖意。
而街角处,骆闻舟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地上躺着的正是利通洋行的襄理皮埃尔,脖子上一道深紫色的勒痕,眼球突出,表情狰狞。更奇怪的是,他怀里紧紧抱着个空了的木盒,盒底刻着一行模糊的梵文。
“头儿,”年轻的巡捕小张跑过来,脸色发白,“法医初步断定,死亡时间大概在两小时前,致命伤是窒息,但……但他手里攥着的这个,好像是……”
骆闻舟接过小张递来的证物袋,里面是半片撕碎的信纸,上面用钢笔写着几个潦草的中文:“货已到,老地方,费……”
后面的字被撕掉了,只剩下一个残缺的“费”字。
骆闻舟的目光再次投向方才那辆黑色奥斯汀消失的方向,眉峰拧得更紧了。
费渡……
这个名字,总像根细刺,时不时地从上海滩的浮华表象下冒出来,扎得人心里发慌。
“去查,”骆闻舟把证物袋丢给小张,声音沉得像压在云里的雷,“查利通洋行最近的所有交易,查皮埃尔接触过的所有人,尤其是……姓费的。”
费先生与骆探长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TF四代:乖乖怀里来
- “因为梦想相遇,那就一直陪着我吧”不是四代全员,但男主不会太少的后期也会加男主不怎么了解小四四,不对勿喷(⑉°з°)-♡“怎么了,跟哥哥说”......
- 2.3万字5个月前
- 守护归守护,怎么没跟我说还要负责谈恋爱呀?!
- 〖1ⅴ7;玄幻奇幻;TNT〗〖小说内容纯属虚构,请勿上升现实!〗她夏安,九尾灵狐,能够看透人心。深得天帝和天后的喜爱,三界的团宠。而她的任务......
- 1.3万字4个月前
- 网王:小财迷今天修罗场了吗?
- 一朝穿越,容绪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并绑定了一个好像没什么用但可爱的系统。她只想仰天长叹,感慨生活不易。算了,身为一个美女,她的目标是搞钱。然......
- 37.9万字3个月前
- 原乐的狐狸犬系男友使用手册
- 丁程鑫:姐姐,今天需要哪种模式?A.拆家哈士奇B.钓系萨摩耶C.绿茶博美
- 1.6万字2个月前
- 斗龙战士之弥补遗憾
- 当罗刹暗无被打败后,龙武族出现了一位少族长,还会有后面的遗憾吗?“那我也会尽力保护你们的,哪怕……”——“毕竟要打破宿命太难了”“难?难也要......
- 10.0万字1个月前
- 种地吧:玫瑰与夏
- 后陡门的夏迎来不一样的玫瑰。陪伴、努力、鼓励……一起度过我们热烈的青春~CP不定
- 13.2万字23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