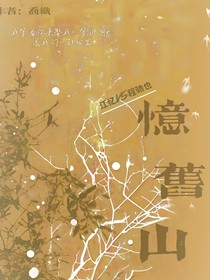第8章 雾锁临江
母亲遗体在培养舱里微笑的第七天,临江市开始起雾。
不是普通的雾。
乳白色的雾气从化研所旧址的每个通风口渗出,沿着建国路一直蔓延到江畔。雾气有重量,沉甸甸地压在人行道上,把梧桐叶粘成湿漉漉的一团。更诡异的是,这雾只在凌晨三点至四点间出现,太阳一照就消散无踪,像是被什么力量精准操控着。
我蹲在江滨公园的观测点——这是老城区唯一能同时看到化研所、母亲长眠的青山公墓以及父亲最后现身的货运码头的地方。望远镜镜头里,第三波雾气正从码头3号仓库的排气扇涌出,在江面形成一条清晰的乳白色带子,如同指向某个方向的箭头。
“记录:第七次晨雾轨迹与潮汐周期吻合度91%。”
身后传来纸张翻动的沙沙声。林晚照的钢笔在笔记本上划出尖锐的折线,她总喜欢把“7”字写得像把解剖刀。这个临江大学海洋地质系的研究生,是三天前在码头拦下我的。当时我正用手术刀撬开仓库的配电箱,而她举着取样仪,马尾辫上别着的金属发卡在月光下闪着冷光。
“陈原,你的生物电场又超标了。”她敲了敲钢笔帽里的微型检测器,表盘上的数字从187跳到203,“再这样下去,不用等警察抓你,你自己就会变成一团人形电磁脉冲。”
我摸了摸锁骨下的蓝点。自从那晚在实验室做出选择,这些标记就变成了某种生物天线,能接收半公里内所有电子设备的信号。此刻它们正微微发热,提醒我林晚照的运动鞋底沾着化研所特有的蓝色苔藓——她显然没说实话。
望远镜突然捕捉到雾气中的异常。码头西北角的薄雾里,有个穿深蓝制服的人影正在张贴什么。放大二十倍后,那张A4纸上的“寻人启事”清晰可见:
寻弟陈源,22岁,左眉有疤,喜穿棕色布鞋。
有线索请联系138××××1077重谢
联系人照片是我的证件照,但电话号码从未见过。更蹊跷的是,启事右下角盖着临江化研所的公章——这个单位早在七年前就注销了。
“你弟弟?”林晚照的钢笔尖戳破了纸页。她今天换了副金丝眼镜,镜腿上的划痕组成三个微型三角形,“上次你说他是你第二人格。”
江风突然变向。雾气形成的箭头调转90度,直指江心。我掏出从父亲胸腔找到的芯片,它表面的铜锈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剥落,露出底下刻着的经纬度:N32°07′,E118°46′——正好是长江南京段某座无名沙洲的位置。
“今天退潮最低点是什么时候?”
“下午四点十八分。”林晚照的睫毛在镜片上投下栅栏状的阴影,“但你要找的东西二十年前就不在了。1998年长江洪水后,那座沙洲就沉没了。”她突然压低声音,“除非……你要找的是‘雾螺’。”
钢笔在笔记本上画出的生物素描让我手指发麻:那是一种形如螺钉的贝类,壳表布满螺旋状蓝纹,据传只出现在化研所排放口附近的淤泥里。民间说法称,吃了雾螺肉的人会产生死去亲人的幻觉。
腹部“3”点钟的蓝点突然刺痛。芯片上的经纬度数字开始蠕动,重组为新的坐标:N32°07′,E118°47′——往东移动了1分,正好是现在雾气箭头所指的方向。
“你母亲是临江人吧?”林晚照递来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画面里年轻的母亲站在水文站门口,身旁的同事举着“1998年抗洪先进集体”锦旗。照片边缘有行褪色的小字:淑芬负责样本采集工作。
江水拍岸声突然变得遥远。我认识这个水文站——它在青山公墓山脚下,母亲骨灰盒里那张字条就写着“水文站旧档案室左七”。当时以为是她工作备忘,现在想来,或许正是Z-107样本的真正藏匿点。
“下午三点码头见。”林晚照突然合上笔记本,“退潮前两小时,雾螺会浮到浅水区换气。”她转身时,我注意到她后颈发际线处有个硬币大小的蓝斑,形状像缩小的时钟刻度。
正午的烈日也没能驱散江面的雾气。我坐在母亲墓前,用手术刀小心清理骨灰盒夹层的锈迹。当刀尖第三次划过“水文站”三个字时,盒底突然弹出一个微型暗格——里面是半张被血浸透的B超单,图像部分已经模糊,但文字栏清晰标注:
宫内双活胎(A胎心率142次/分,B胎40次/分)
建议进一步排查嵌合体可能
检查医师签名:林××
“林”字最后一捺被血迹拖得很长,几乎划破纸面。
手机突然震动,未知号码发来彩信:一艘锈迹斑斑的货轮正停泊在下午雾气指向的坐标点,舷号“宁航107”的“7”字被特意用红圈标出。照片拍摄时间是十分钟前,而背景里有个穿棕色布鞋的人影正从跳板走下船。
腹部蓝点集体灼烧起来。我抓起背包冲向山下,却在公墓大门被管理员老赵拦住。这个总是醉醺醺的退伍军人,今天反常地清醒,作战靴上沾着新鲜的码头淤泥。
“小陈啊。”他摸出皱巴巴的烟盒,里面却装着三颗雾螺空壳,“你妈下葬那天,有帮穿蓝制服的人来挖过坟。”他吐出的烟圈在无风的空气中组成数字“107”,“领头的是个戴金丝眼镜的女人,说话文绉绉的……像大学老师。”
水文站的铁门虚掩着。推门时,门轴发出与老宅冰箱如出一辙的哮喘声。档案室左七号柜空空如也,但柜壁上有道新鲜的划痕,组成箭头指向天花板——通风管道盖板被人动过手脚。
攀上管道时,蓝纹突然自动编织成保护垫,让手掌免于被铁皮割伤。爬行三十米后,管道尽头是个改装过的实验室:培养舱里漂浮着十二个雾螺,每个螺壳表面都刻着“Z-107”的子编号。操作台上的老式录音机正在循环播放:
“样本稳定性测试第七天,林淑芬出现严重排异反应……胎儿A心率持续下降……建议立即注射从雾螺提取的RNA逆转录酶……”
这是父亲的声音,但背景音里有母亲痛苦的呻吟。录音放到三分十二秒时,突然插入一段高频噪音,我的蓝纹随之共振,在皮肤上形成长江流域地图——南京段某个点正高频闪烁,与芯片坐标完全重合。
撬开通风管出口时,夕阳正把江面染成血红色。宁航107号锈蚀的船身上,有个穿白大褂的女人正在甲板调试仪器。她转身时,金丝眼镜和林晚照同款,但镜片后的眼睛让我浑身血液冻结——那是母亲的眼睛,虹膜边缘有圈淡蓝色光晕。
“你比预计的晚了十七分钟。”她说话时嘴角扬起与母亲相同的弧度,“看来林晚照没骗我,你确实继承了淑芬的路痴基因。”
船艙突然传来重物倒地的闷响。当我冲向声源时,女人在背后轻声道:“小心台阶,原原。就像你七岁那年……”
这句话像钥匙般打开了记忆闸门。七岁生日那天,我追着穿红背心的男孩跑下船舱,在第三级台阶摔断了门牙。而此刻,面前台阶上正躺着昏迷的林晚照,她手里紧攥着半张照片——母亲与这个眼镜女人的合影,背面写着“与胞姐林淑媛摄于1996”。
甲板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眼镜女人——现在该叫她林淑媛了——正对着对讲机喊:“准备启动声呐!他发现107号样本了!”
林晚照突然睁眼,她的瞳孔在夕阳下呈现出与雾螺壳相同的螺旋蓝纹:“陈原,你母亲把真正的Z-107样本藏在了……”
船体猛然倾斜。江水从舷窗灌进来,瞬间没到膝盖。在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秒,我看见自己的蓝纹顺着水流蔓延到整艘船,而水下有什么东西正发出与老宅冰箱相同的嗡鸣声。
啃食记忆之物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逐梦上海滩(新剧长剧情)
- 《梦想之城》是一部充满励志与温暖的都市小说,讲述了男主字你作为一名美术生,在清华美术学院取得优异成绩后,与好友林悦一同来到上海追逐梦想的故事......
- 1.1万字6个月前
- 三轨:剑破长空
- “唔生平宏愿,凭手中之剑,败尽天下。将剑之一道,证遍诸天万界,彼岸虚空!”“区区三鬼小儿意识体,受死!”
- 8.0万字4个月前
- 叶澜的幻影恋人
- 叶澜与幻自幼相伴成长,情深似海。在规则怪谈的世界里,他们更是彼此的挚爱。叶澜是幻的第528个人格,两人生日相同,皆为水仙般自恋。叶澜嗜血暴力......
- 0.2万字4个月前
- 忆旧山
- 山河无恙的前提是有人负重前行,而他们舍家为国,是英雄。初见他,他高坐枝桠,歪了歪头对着她说了一句“小妞,得寸进尺了啊。”后来在烤鱼时他看着湖......
- 0.6万字3个月前
- 我去天上抢职位
- 0.3万字3个月前
- 镜渊谜影
- 《镜渊谜影》简介便利店雨夜,林小禾收到指向已拆迁长明巷的匿名信,附照中妹妹脖颈红绳醒目,背面字迹撕开记忆缺口——那里藏着妹妹失踪、地下室白骨......
- 0.7万字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