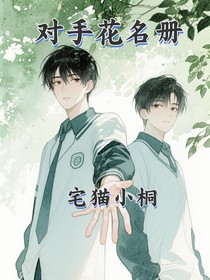第一章 巷口的槐花香
暮色漫过青石板路时,林砚之终于找到了那道被爬山虎半掩的巷口。
空气里飘着甜丝丝的槐花香,混着隐约的酱油香和煤炉燃烧的气息。她攥紧帆布包带,踩着被夕阳拉长的树影往里走。墙根下有阿婆蹲在小马扎上择菜,竹篮里的青菜沾着湿泥,见她探头便扬声问:“姑娘找哪家?”
“我找……周记卤味。”林砚之把那张揉得发皱的纸条递过去。纸上是外婆临终前颤巍巍写下的地址,字迹被泪水晕开了一角。
阿婆往巷深处指了指,竹篮里的水珠滴在青石板上,洇出小小的深色圆点:“到头左拐,挂红灯笼那家就是。周老板的卤味啊,熬了三十年的老汤,香得能勾走魂咯。”
巷子里比想象中热闹。斑驳的墙面上刷着褪色的“好好学习”标语,墙根摆着盆栽和旧藤椅,穿背心的大爷摇着蒲扇下棋,棋子落在搪瓷盘里叮当作响。有穿校服的孩子疯跑着掠过,裤脚带起一阵风,惊得趴在墙头的橘猫弓起了背。
林砚之走得很慢。她总觉得这巷子眼熟,像外婆相册里夹着的老照片——灰瓦屋檐下挂着腊肉,窗台上摆着玻璃罐,罐里泡着橘子皮和冰糖。外婆在世时总说,她年轻时候住的地方,夏天满巷都是槐花香,卤味铺子的老汤咕嘟咕嘟熬着,能香透整条街。
“吱呀”一声,前头的木门被推开。
林砚之抬头,看见那盏红灯笼在晚风里轻轻晃。灯笼底下是家不足十平米的小店,玻璃柜台里码着油光锃亮的卤味:酱鸭腿泛着琥珀色的光泽,猪耳朵切得薄如蝉翼,鸡爪蜷缩着,骨缝里都浸着酱色。柜台后站着个穿白褂子的男人,约莫四十岁,眉眼温和,正低头给顾客装袋,手腕上的银镯子随着动作轻轻碰撞。
“要只酱鸭,斩半只就行。”顾客是个拎着菜篮的阿姨,嗓门亮得很,“老周,今天的鸭好像格外香啊。”
“今天加了点新晒的陈皮。”男人的声音低沉,像老汤熬开时的轻响。他拿起菜刀,刀刃落下时又快又准,鸭骨断裂的脆响清晰可闻。装袋时,他多夹了两块卤豆干放进去,“刚卤好的,尝尝鲜。”
阿姨笑盈盈地接过来:“就你会做生意。对了,你家丫头今天没来看店?”
“在里头写作业呢。”男人朝里屋扬了扬下巴,转身时正好对上林砚之的目光,微微一怔,“姑娘要点什么?”
林砚之喉头发紧,把帆布包往身后藏了藏。包里是外婆的骨灰坛,她按外婆的遗愿,带她回这烟火巷来。她深吸一口气,闻到卤味里混着的八角和桂皮香,忽然想起外婆病床前的话:“阿砚,等我走了,就把我撒在周记卤味门口的槐树下……老周他娘熬的卤汤,是我这辈子闻过最安心的味道。”
“我……”林砚之攥紧了包带,指节泛白,“我想问问,您认识一个叫苏婉的人吗?”那是外婆的名字。
男人的动作顿住了。他抬手擦了擦额头的薄汗,灯光落在他眼角的细纹里,忽然就添了几分沧桑。“苏婉?”他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咀嚼一个尘封已久的名字,“那是我母亲的名字。她十年前就过世了。”
林砚之猛地抬头,撞进他带着惊讶的眼眸里。柜台后的风扇慢悠悠转着,把槐花香和卤味的气息吹得更浓了些。男人从柜台下拿出一个搪瓷缸,倒了杯凉茶推过来,杯壁上凝着细密的水珠。
“姑娘,你是……”
“我是她的外孙女。”林砚之的声音发颤,眼眶忽然就热了。她看着玻璃柜台上摆着的相框,照片里是个笑眼弯弯的阿姨,抱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背景正是这烟火巷,“我外婆说,这里有她最惦记的味道。”
男人望着她,忽然笑了。他从柜台里取出一小碟卤鸡爪,推到林砚之面前,鸡爪的皮皱巴巴的,却透着诱人的酱色。“尝尝?”他说,“这是我娘传下来的方子,三十年了,老汤每天都添新料,从没断过火。”
林砚之捏起一只鸡爪,指尖触到温热的质感。放进嘴里轻轻一抿,卤汁的咸香混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甜,从舌尖漫到喉咙里。那味道很熟悉,像外婆每年冬天都会卤的鸡爪,在煤炉上炖整整一下午,满屋都是暖融融的香气。
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砸在玻璃柜台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巷口的槐花开得正盛,晚风卷着花香和卤味的气息,漫过青石板路,漫过亮着灯的窗,漫过林砚之湿漉漉的眼眶。她忽然明白,外婆惦记的从来不是某一味卤味,而是这巷子里的烟火气,是那些藏在味道里的、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男人递给她一张纸巾,轻声说:“我叫周明远。以后常来玩,啊?”
林砚之点点头,看着柜台后那锅咕嘟冒泡的老汤,雾气氤氲里,仿佛看见外婆年轻的笑脸,正站在巷口,朝她轻轻挥手。
烟火巷里的味觉诗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决择……
- 豪门女主vs痞帅男主,作者文笔有点差大家别嫌弃
- 1.5万字7个月前
- 迟到了18年的人生
- 【无系统+变嫁】曾经生活无忧无虑的苏凌溪,在青春期遭遇了身体的微妙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异样的目光和无情的嘲笑。然而,一次偶然的事件彻底改变了苏......
- 13.4万字7个月前
- 双女主同人自写(顾曲)
- 双女主同人自写
- 4.2万字3个月前
- 真千金超级飒
- 做回真千金后在线打脸
- 1.1万字3个月前
- 叶皓然:我的命中注定
- 都是白日梦,请勿上升正主
- 2.8万字2个月前
- 对手花名册
- 原来最好的对手早成了藏在心底里的终极目标
- 2.9万字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