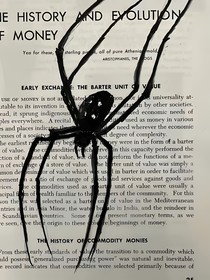第二章 老汤里的光阴
清晨的雾还没散,周记卤味的木窗就支了起来。林砚之被一阵规律的剁肉声吵醒,揉着眼睛推开门时,正看见周明远在巷口的青石台上处理排骨。
刀背敲击骨头的闷响在巷子里荡开,他左手按住排骨,右手举刀,每一下都稳准狠。骨缝里的血丝溅在白褂子上,他却浑不在意,只是时不时抬眼看看天色。雾里的槐树叶沾着露水,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水珠,落在他发梢上。
“醒了?”周明远侧头看她,刀刃在晨光里闪了闪,“锅里炖着白粥,配了酱萝卜。”
林砚之这才发现自己昨晚竟在里屋睡着了。窄小的隔间铺着碎花床单,墙角堆着半箱陈皮,空气里飘着淡淡的卤香,竟比酒店的羽绒被还要安心。她摸了摸发烫的脸颊,想起昨晚周明远说“里屋有床,不嫌弃就住下”,喉咙又有些发紧。
灶台上的白粥咕嘟着细泡,搪瓷碗里的酱萝卜切得极细,红亮的色泽裹着晶莹的糖霜。林砚之舀起一勺粥,米香混着萝卜的脆甜漫开,忽然想起外婆总说“好酱菜要晒足百日太阳,像做人一样,得经得住时光熬”。
“周叔,这萝卜是您自己腌的?”
“嗯,去年霜降收的白萝卜,用老坛腌了三个月。”周明远拎着处理好的排骨进屋,白褂子上的血迹已经干了,“我娘以前总说,腌菜和卤味一样,得有耐心。火候差一点,味道就偏了。”
林砚之看着他往大铁锅里添老汤。那口黑黝黝的铁锅比她还高,汤面上浮着层清亮的油花,八角、桂皮、香叶在汤里轻轻翻滚。周明远舀起一勺汤尝了尝,眉头微蹙,又往里面撒了把晒干的槐花粉。
“这是……”
“我娘的法子。”他用长柄勺搅着汤,“每年槐花谢的时候,就把花瓣晒干磨成粉,卤味的时候加一点,能去腻提鲜。她说槐花香是烟火巷的魂,少了这味,卤出来的东西就没了根。”
说话间,巷子里渐渐热闹起来。卖豆腐的推着板车走过,木梆子敲得笃笃响;收废品的三轮车叮铃哐啷碾过青石板;隔壁的张大爷端着搪瓷碗来讨卤汁,说是孙子要吃卤蛋。
“刚熬好的汤,您多盛点。”周明远给张大爷舀了满满一勺,“记得加两颗冰糖,孩子爱吃甜的。”
张大爷乐呵呵地应着,临走时瞥见林砚之,凑到周明远耳边小声问:“这是你家亲戚?眉眼瞧着跟苏婉年轻时有几分像呢。”
周明远的动作顿了顿,随即笑了:“是我远房侄女,来城里找工作,先在我这儿落脚。”
林砚之低头喝粥,假装没听见。她知道周明远是在替她解围,外婆和他母亲的关系显然不一般,可那些尘封的往事,她还没勇气去触碰。
上午十点,卤味刚出锅就排起了长队。林砚之被周明远拉去帮忙装袋,指尖触到温热的酱鸭腿,那层油光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泽,香气钻进鼻腔时,她忽然想起外婆的相册里,有张年轻女子站在卤味铺前的照片,怀里抱着个襁褓婴儿,柜台上的酱鸭正冒着热气。
“姑娘,来两斤猪耳朵!”排队的阿姨嗓门亮,打断了她的思绪。
林砚之慌忙拿起夹子,却被猪耳朵的薄脆惊到——每一片都切得厚薄均匀,边缘带着细密的刀花,显然是功夫活。她忍不住问:“周叔,这刀工练了多久?”
“从八岁开始学。”周明远正在给酱鸭淋卤汁,手腕翻转间,酱汁均匀地裹在鸭皮上,“我娘说,切卤味和做人一样,得稳、准、狠,还得有分寸。太薄了没嚼头,太厚了不入味。”
正说着,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背着书包冲进店来,扑到周明远腿边:“爸,我放学啦!”
“丫丫回来啦。”周明远弯腰摸了摸女儿的头,眼底的温和几乎要溢出来,“今天考试怎么样?”
“全对!”丫丫举起作业本,目光却溜到了柜台里的卤鸡爪上,“爸,我能吃一个吗?就一个!”
周明远笑着捏了捏她的脸,拿起一只最小的鸡爪递过去。丫丫踮着脚接过,跑到林砚之身边,仰着小脸问:“姐姐,你是我爸说的那个远房姑姑吗?你身上有槐花香呢。”
林砚之的心猛地一颤。她低头看着丫丫亮晶晶的眼睛,忽然想起外婆临终前说的话:“阿砚,你要记得,槐花开的时候,就回烟火巷去。那里有我们家的根。”
铁锅的老汤还在咕嘟作响,阳光透过木窗照进来,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林砚之望着柜台后忙碌的周明远,望着啃着鸡爪的丫丫,忽然觉得这烟火巷的光阴,就像那锅老汤,慢慢熬着,把思念、牵挂、温情都熬成了化不开的浓味。
烟火巷里的味觉诗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撩完不负责的小骗子就该被关起来
- 双阿尔法。双洁阶级的差距和那段不被世俗承认见不得人的恋情。让林序秋生出了逃跑的想法。他连夜递交了辞职报告,辞去了秘书一职。他以为他和裴谁之间......
- 1.6万字9个月前
- 马嘉祺:爱在无人处
- 以为是永恒,却是一箱情愿以为是意外,却是命中注定/一场恋爱的豪赌究竟要输几回才能清醒姐妹作《丁程鑫:昭昭我心》
- 6.3万字5个月前
- 愁雨夜
- bg
- 0.1万字4个月前
- 锦锋侧颜,吴涛心底的月光
- 当十七岁的吴涛在美术教室的阴影里第一次看见锦锋低头画画的模样,他还不知道,那个被阳光斜切一半的侧脸,会成为他此后无数个夜晚辗转反侧的隐秘坐标......
- 6.7万字3个月前
- 暗河少年
- 青春是一条暗河,汹涌、隐秘,充满未知的危险与抉择。尹旋光,一个被命运推入黑暗的少女,带着满身伤痕与倔强,踏入流星工业高中这所“恶名昭彰”的学......
- 3.5万字3个月前
- 霸总他有点暖
- 毕业当天,我被爸妈卖了!看着桌子上的卖身契,我心里很沉重结婚对象是个高富帅结婚对象总想对我好,但笨手笨脚
- 0.4万字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