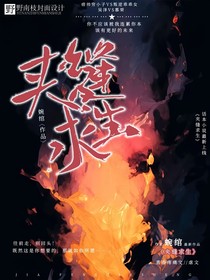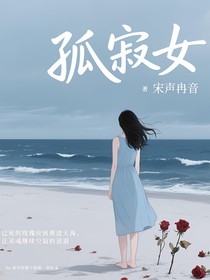第三章 老坛里的光阴
林砚之是被酸香唤醒的。
天刚蒙蒙亮,巷子里还浸着晨露的凉,那股子酸里裹着甜的气息就从窗缝钻进来,勾得她鼻尖发痒。她披了件薄外套跑到院里,正撞见周明远蹲在老槐树下,小心翼翼地搬开一口半埋在土里的陶坛。
陶坛黢黑发亮,边缘结着层厚厚的盐霜,坛口蒙着的棉布被麻绳勒得紧实。周明远解开绳结时,林砚之清清楚楚听见“啵”的一声轻响,像是封存已久的光阴突然醒了。
“这是……”她凑过去,看见坛里码着整整齐齐的白萝卜,表皮泛着温润的琥珀色,汁水在坛底轻轻晃。
“外婆的酸萝卜。”周明远指尖敲了敲坛沿,陶土发出闷闷的回响,“我娘说,这方子是你外婆当年教她的。”
林砚之忽然想起外婆的厨房。阳台角落总摆着几口玻璃坛,泡着萝卜、豇豆和生姜,坛口压着鹅卵石。每年霜降那天,外婆就会把晒得半干的萝卜码进去,撒上花椒和冰糖,最后浇上井水,说要“让萝卜在坛里好好睡个觉”。
“要先把萝卜晒三天,晒得表皮发皱才行。”周明远拿出竹片夹子,夹起根萝卜举到晨光里。萝卜片薄厚均匀,肌理间透着晶莹的光泽,“你外婆说,太水灵的萝卜性子急,泡不出绵长的酸。”
他把萝卜放进白瓷盘,浇了点坛里的汁水。酸香瞬间漫开来,混着晨露的清冽,勾得林砚之咽了咽口水。周明远递过筷子:“尝尝?你外婆总说,好的酸萝卜要‘酸得含蓄,甜得克制’。”
萝卜刚入口,林砚之就愣住了。
酸意先是轻轻漫过舌尖,像初春的细雨,带着点清爽的凉意。嚼到第二口,一丝甘甜从萝卜的肌理里渗出来,不浓不烈,正好中和了那点酸。咽下之后,喉咙里还留着点微微的辣,是坛底那把红花椒的功劳。
“和我外婆泡的一模一样。”她眼眶有点热,又夹了一片,“她总说,泡萝卜要等二十一天,多一天少一天都不成。”
“是二十一天。”周明远笑了,“我娘把这个写在账本第一页,每个字都描了三遍。”
正说着,巷口传来三轮车的叮当声。卖豆腐的张叔踩着晨光过来,车斗里的豆腐板冒着热气:“老周,今天的酸萝卜出坛了?给我来两块,配热豆腐吃。”
周明远用油纸包了萝卜递过去。张叔咬了一口,眯着眼直咂嘴:“啧啧,这酸劲儿,够味!比城东边那家网红泡菜强多了。”他往铺子里探了探头,看见林砚之,“这位是?”
“苏姨的外孙女,来住些日子。”周明远擦了擦柜台。
“苏姨的外孙女?”张叔眼睛一亮,“难怪看着面善!你外婆当年泡的酸萝卜,街坊邻里谁不惦记?那年她住院,整条巷的人轮流给她送汤呢。”
林砚之的心轻轻颤了一下。外婆从未跟她讲过这些,她记忆里的外婆,总是坐在阳台藤椅上,抱着相册慢慢翻,翻到某一页就停下来,对着泛黄的照片出神。
“对了,”张叔忽然一拍大腿,“你外婆当年教我媳妇做的糯米藕,今天正好蒸了,我给你送块来!”说着蹬起三轮车就往巷尾去,车斗里的铜铃铛叮铃铃响。
阳光渐渐爬过屋檐,照在玻璃柜台上。周明远把酸萝卜摆进盘子,放进柜台最显眼的位置。有早起的街坊路过,闻到香味就停下来:“老周,今天有酸萝卜?给我来半斤,配粥吃。”
林砚之看着周明远忙碌的身影,忽然明白外婆为什么非要来这里。
不是因为某一味具体的味道,而是这些藏在烟火里的牵挂——是二十一天的等待,是账本上描了三遍的字迹,是街坊邻里记了半生的惦记。这些东西像那口老坛里的汁水,慢慢熬着,把寻常日子熬出了滋味。
她走到柜台后,看见周明远正往卤汤里加陈皮。老汤在煤炉上咕嘟着,泛起细密的泡泡,把八角和桂皮的香都熬了出来。
“我能帮点什么吗?”林砚之挽起袖子。
周明远往灶膛里添了块煤,火苗“腾”地窜起来,映得他眼底暖融融的:“帮我把那边的鸭翅摆整齐吧,等会儿上学的孩子要来买。”
晨光漫过青石板路,巷子里渐渐热闹起来。卤味香混着酸萝卜的清爽,裹着豆浆的醇厚,在槐花香里慢慢酿着。林砚之摆着鸭翅,听着周明远和街坊们笑着打招呼,忽然觉得,外婆并没有离开。
她就藏在这坛酸萝卜里,藏在咕嘟的老汤里,藏在这满巷的烟火气里,等着她一点一点,慢慢找回来。
烟火巷里的味觉诗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想当你的猫
- 在恋爱中成长,在成长中遇见!
- 0.9万字7个月前
- 王威:你是威意
- “你是唯一”“你是威意”遇你如烟花映天下似冬雪遇暖阳.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比起一时兴起的新鲜感我更喜欢被坚定选择“我要的爱只在你身上存在”
- 1.1万字7个月前
- 夹缝求生
- 他们和普通情侣不同,他们俩不被所有人认可,不被所有人赞同。所有人所有事都在阻挠他们两个在一起。似乎他们相识就是一个错误……
- 1.7万字7个月前
-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 先声明,我不是小学生我已经初中差不多初三了。我只不过是我拿我记得很清楚的梦境拼凑出来的。有一些梦我是没做过的但是大多我都做过,里面会有有关后......
- 0.3万字6个月前
- 夏日淮安
- 女主在一场车祸中死去了但孩子活了下来,男主和孩子通过时光机穿越到了一个平行时空,并找到了她。
- 0.7万字5个月前
- 孤寂女
- 从小失去双亲的程雨荨,被叔叔奶奶一家收养长大,本以为到了新的家庭,可以无忧无虑的长大!可事实并非想她想得如此,就在她高中辍学毕业后,叔叔奶奶......
- 0.7万字3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