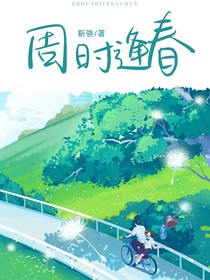第四章 暴雨里的酸梅汤
暴雨是后半夜泼下来的。
林砚之被砸在窗棂上的雨声惊醒时,窗外的槐树影已经成了模糊的一团。她摸黑摸到手机,凌晨三点十七分。隔壁周叔的卤味铺传来动静,铁锅碰撞声混着哗啦啦的水声,在雨幕里格外清晰。
她披了件外套推开门。巷子里的积水已经漫过脚踝,青石板缝里冒出细密的气泡。周记卤味的灯亮着,暖黄的光晕透过雨帘铺在水面上,像块融化的黄油。周叔正蹲在门口,用木板挡着门槛,裤脚卷到膝盖,小腿上沾着泥点。
“周叔,我来帮你。”林砚之挽起裤腿踏进水洼,冰凉的雨水瞬间浸透了帆布鞋。
周叔直起身,额前的碎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这点水不算啥,老汤没被淹着就好。”他往铺子深处指了指,那里架着几块垫高的木板,三十年的老汤坛子稳稳当当地坐在上面,“以前每年汛期都这样,早有经验了。”
林砚之却看见他手背擦破了皮,渗着血丝。想来是搬木板时蹭到的。她转身回屋翻出医药箱,蹲在周叔面前替他涂碘伏,指尖触到他粗糙的皮肤,像摸过卤味铺里那块用了十几年的木砧板。
“小时候我娘总说,这巷子的水是活的。”周叔忽然开口,望着雨幕里摇晃的红灯笼,“下再大的雨,天亮前准退。”他顿了顿,声音轻下来,“你外婆以前最爱在暴雨天来铺子里,带一小罐自己腌的酸梅,说要给老汤添点清冽气。”
林砚之的动作顿住了。她想起外婆的樟木箱里,总放着几个粗陶罐子,打开时酸香扑鼻,能把满屋的药味都压下去。那时候她总嫌酸,外婆却笑着说:“等你尝过烟火巷的酸梅汤,就知道这酸里藏着甜了。”
雨势渐小时,天边泛起了鱼肚白。周叔搬开木板,青石板上的水洼倒映着灯笼的红,像打翻了的胭脂盒。有早起的阿婆挎着篮子经过,见他们在收拾,便笑着打趣:“老周,今天该熬酸梅汤了吧?我家小孙子念叨好几天了。”
周叔应着好,转身从里屋翻出个陶瓮。揭开盖子时,酸香混着冰糖的甜气漫出来,林砚之凑过去看,瓮里的酸梅泡得发黑,核上还留着细密的牙印。“这是去年你外婆送来的,说留着等今年暴雨后用。”周叔拿起一颗,对着光看,“她说雨水最干净,用这天的水泡酸梅,才够清透。”
炉火升起时,巷子里飘起了酸梅汤的香气。周叔把酸梅连同汤汁倒进砂锅,又抓了把甘草和陈皮,说这是他娘传下来的方子,酸梅要选霜降后的,陈皮得晒够三年,甘草要去了芯的,这样煮出来的汤才酸甜得宜,带点回甘。
林砚之坐在小马扎上看他忙。砂锅在煤炉上咕嘟作响,热气模糊了周叔的眉眼,他手腕上的银镯子随着搅动的动作轻晃,那是外婆送的,说是当年两人凑钱打的,一个刻着“苏”,一个刻着“周”。
“尝尝?”周叔舀了勺晾温的酸梅汤递过来。
青瓷碗里的汤汁呈琥珀色,浮着几粒饱满的梅肉。林砚之抿了一口,酸意先漫过舌尖,紧接着是冰糖的甜,咽下去时,喉咙里泛起淡淡的甘草香。她忽然想起外婆临终前,拉着她的手说:“阿砚,日子就像这酸梅汤,得熬,得等,熬透了,等够了,酸里自然就出甜了。”
眼泪毫无预兆地落进碗里,荡起小小的涟漪。
阳光穿透云层时,巷子里的水已经退了。穿校服的孩子们背着书包跑过,裤脚沾着泥也不在意,吵着要喝酸梅汤。周叔忙着给他们装杯,林砚之站在旁边帮忙递吸管,看着孩子们捧着杯子吸得啧啧响,忽然觉得这画面格外熟悉——就像外婆相册里那张泛黄的照片,年轻的苏婉和周母坐在巷口,手里捧着同样的青瓷碗,笑得眉眼弯弯。
“姐姐,你的酸梅汤要加冰吗?”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仰着脸问她。
林砚之笑着点头,看周叔从冰柜里拿出冰块丢进碗里,碰撞出清脆的声响。阳光穿过槐树叶落在汤里,碎成点点金斑,像撒了把星星。
她忽然懂了外婆说的甜。不是冰糖的甜,是暴雨过后的晴空,是炉火上咕嘟的砂锅,是陌生人递来的一碗热汤,是藏在酸梅核里、要慢慢嚼才能尝到的那点回甘。
这大概就是烟火巷的味道,是外婆藏了一辈子的味觉诗。
烟火巷里的味觉诗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无声操作
- 林然打游戏有两绝:1.ADC操作秀翻全场2.骂人能让队友自闭直到某天,她激情开喷的游戏场景被直播出去——而那个全程沉默Carry的打野,正是......
- 1.7万字4个月前
- 周时逢春
- 双一见钟情但不说,身居高位者的喜欢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双方位高权重,更在于一个对视就能知道对方想的什么、要的什么
- 0.3万字4个月前
- 魔角侦探第四季同人续写
- 喜欢第二季的封面,所以用的是第二季的,我不会告诉你们,是我没找到其他的。更新时间不定,但是是会一直更新下去的。
- 0.3万字3个月前
- 未寄的告白
- 小说以男主与女主情感为线,展现青春美好与命运无常,凸显正义对抗邪恶的不屈,以及牺牲后的精神传承,强调正义必胜与美好精神不朽。
- 0.8万字2个月前
- 绛河秋
- “哥哥,你许下的这份承诺,可有千斤之重哦。”“没关系的,我承受得起,不用担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可是墨白燕没能等来这个答案......
- 5.2万字1个月前
- 鲸落于星海
- 失而复得、双向救赎、成长、娱乐圈侧写、海洋环保
- 5.2万字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