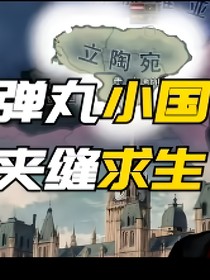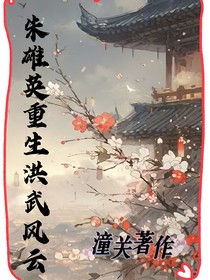无题
邯郸冬夜刺骨寒冷,北风呼啸着穿过屋檐下的青铜铃铛,发出阵阵凄厉声响。
赵姬蜷缩在质子府最偏僻的厢房里,手指深深掐进锦褥。
又一波剧痛袭来,她咬紧牙关,口中喃喃自语。
产婆的声音时近时远,“夫人,再加把劲儿!
”
赵姬望着窗外飘舞的雪花,思绪飞回到三个月前那个雨夜。
吕不韦的马车碾过青石板路,将醉醺醺的子楚载入她的生活。
那时,她刚刚跳完《九韶》,水袖还沾着淡淡的酒香。
剧痛突然变得模糊,婴儿的啼哭划破黑暗。
赵姬勉强撑起身子,看见产婆惊恐的脸庞。
鲜血浸透织锦被褥,顺着床沿滴落于地。
血泊中央静静躺着一枚青玉雕成的蝉,那是吕不韦随身携带的佩饰。
“政儿……”赵姬颤抖着抱起浑身青紫的婴儿,门外忽然传来杂沓的脚步声。
月光映照下,几名执戟士兵的身影投射在窗纸上,狰狞可怖。
六岁的嬴政蹲在巷口,用树枝拨弄冻僵的蚂蚁。
初春的风夹杂着冰碴子,吹得他耳尖通红。
忽然,一团雪球砸中后颈,他转身看到三个锦衣少年骑着骏马缓缓而来,金线绣制的赵国王室图腾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秦狗崽子!
”为首的公子迁挥舞马鞭,“学两声狗叫,本公子赏你块黍饼。
”
嬴政攥紧树枝,指甲嵌入掌心。
清晨母亲梳头时的话犹在耳边,“在赵国,你的眼神要像蒙尘的剑。
”他缓缓低下头,露出嶙峋的后颈。
冰冷的雪水顺着衣领渗入脊背,他默默数着青石板上的裂纹,直至那些笑声渐行渐远。
暮色笼罩下,破旧院落中飘出断续歌声。
嬴政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只见母亲正在井边浣洗衣物。
她总爱哼唱那首《秦风·蒹葭》,只是调子比真正的秦人柔和三分。
染血的里衣在暮色中轻轻摆动,宛若当年冬夜浸透锦褥的鲜血。“今日学了几个字?
”赵姬绞干最后一件衣物,手指冻得发紫。
嬴政从怀里掏出半块木牍,上面歪歪扭扭刻着一个“王”字。
油灯摇曳,将他们的影子投射在斑驳的土墙上,忽明忽暗。
吕不韦的马车在子时悄然而至。
嬴政蜷缩在里间,透过屏风缝隙注视着那个总穿玄色深衣的男人。
腰间玉佩相击的声音清脆悦耳,仿若邯郸冬日屋檐下碰撞的冰棱。
“公子已说服华阳夫人。
”吕不韦的声音轻柔如蛇信拂过耳畔,“三日后有楚国使团经过邯郸,这是最后的机会。
”
案几上的羊皮地图徐徐展开,嬴政的目光追随着母亲涂着丹蔻的指尖滑过黄河蜿蜒的曲线。
青铜酒盏倾倒,暗红的酒液漫延开来,宛如当年浸透锦褥的血色。
蓟县街头,两个男孩奔跑嬉戏。“政!快来抓我呀!
”身穿华丽服饰的燕国小男孩姬丹喊道。
嬴政奋力追赶,气喘吁吁地喊:“丹,别跑那么快!
”两人最终停下脚步,靠在街边墙壁上喘息。
姬丹笑着问:“政,你以后当了大王,可别忘了我。
”嬴政目光坚定,“自然不会,我定成就一番大业。
”
这时,一阵骚乱从街边传来,一群燕国士兵押解着几个看似秦国商人的男子走过。
姬丹低声说道:“听说秦国又在赵国边境挑事,咱们燕国可不能怕他们。
”
嬴政心中暗自思忖,秦国虽曾遭遇大败,但只要休养生息,总有东山再起之日。
就在此时,一位神秘老者缓步走近,低声说道:“两位小公子,天下之势变幻莫测,日后秦强还是燕盛,尚未可知啊。
”
老者说完便飘然而去。
嬴政与姬丹对视一眼,彼此眼中皆闪过一丝坚毅。
他们明白,未来的道路充满挑战,但也蕴含无限可能。
秦庄襄王初年,嬴政在赵国邯郸为质。
九原郡内寒风凛冽,赵括、廉颇、李牧、司马尚四位将军肃立于营帐前,面见新崛起的屠耆单于。
屠耆单于自幼随父征战赵地,却在“九原之战”一役惨败,匈奴十万人马尽丧,这血海深仇至今铭刻于心。
他目光如冰刃般扫视众人,低沉开口:“当年之耻,我从未忘怀。
今日重逢,匈奴必雪此恨。
”
赵括眉头微蹙,冷哼一声,“小小单于,莫要狂妄!
若再犯我赵境,定叫你有来无回。
”声音铿锵有力,在空旷之地久久回荡。
屠耆单于冷笑作答,“如今匈奴已非昔日可比,休要小觑。
”语气中满是傲然与笃定。
李牧神色凝重,拱手道:“单于,战国纷争不断,若两败俱伤,恐让旁人坐收渔利。
不如化干戈为玉帛,共谋和平。
”言辞恳切,带着几分理性思考。
屠耆单于沉默片刻,冷冷吐出一句:“和平?除非赵国割地赔款。
”
廉颇怒目圆睁,愤然说道:“痴心妄想!
我赵国寸土不让,若战,我等奉陪到底!
”话音刚落,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双方剑拔弩张,空气仿佛凝滞一般。
此时,嬴政静立一旁,默默注视着这一切,心中思潮翻涌,思索着这场对峙将如何落幕。
就在这时,他忽然开口:“终归都是我大秦囊中之物!
”
此言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投向嬴政,眼中满是惊讶与疑惑。
屠耆单于先是一愣,随即仰头大笑,“你这质子好大的口气,如今寄人篱下,竟敢妄谈大秦?
”
嬴政面色镇定,目光坚定,“天下大乱,唯有大秦有统一天下之雄心与实力。
赵国与匈奴之争不过是过眼云烟,最终都将归入大秦版图。
”
赵括等人虽心中不悦,却也不得不承认其言颇有道理。
屠耆单于收敛笑容,眼神警惕,“不管你们大秦如何,今日恩怨必须了断。
”
嬴政向前一步,朗声说道:“单于若执意开战,赵匈两败俱伤,大秦便可坐收渔翁之利。
若能罢兵言和,日后同为大秦效力,岂不更好?
”声音清晰洪亮,在场之人皆为之侧目。
屠耆单于陷入沉思,整个空间似乎都因这一瞬间的停顿而凝固。
未来走向,正悄然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赵国朝堂上关于是否与匈奴和谈的争论仍在继续。
赵括与廉颇主张备战,以防匈奴再度来袭;李牧则认为应稳住局势,等待更佳时机。
而在遥远的北方,屠耆单于亦在权衡嬴政所提之议。
他知道若与赵国死战,即便胜算不小,代价也必然沉重,或许与大秦合作方为上策。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战国千年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立陶宛之路
- 面对着苏联对立陶宛自绝权益的傲慢轻视;面对梅梅尔地区德国威胁的步步紧逼。身在夹缝的立陶宛一路之中必然不容易,立陶宛必须找到办法保卫他的人民,......
- 0.7万字10个月前
- CH:社会主义三部曲
- (各位审核大爹,不要屏蔽我的书,我只想让更多人了解历史,政治敏感话题我会尽量回避)以同人文的形式展示二战后三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纯历史向没......
- 0.7万字9个月前
- 朱雄英重生之洪武凤云
- 2.6万字6个月前
- 历史杂记
- 会议讲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传记。
- 1.6万字4个月前
- 念者
- 讲的是历史事迹
- 0.4万字3个月前
- 继汉
- “继,续也。”——《说文》,汉朝四百年之伟业,何至一夕间倾颓。后世之人一朝魂穿,附身于刘备之身,愿试手,补天裂。
- 1.2万字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