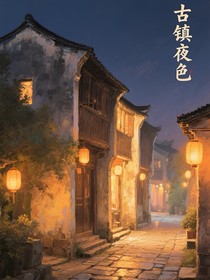春分与合卷
春分的风带着泥土的腥气,漫过回春巷的青石板。苏晚蹲在梧桐树下,看着去年埋下的“传针盒”旁冒出丛新绿,叶片的形状像极了她绣绷上常用的缠枝纹。“你看这芽尖,”她回头朝屋里喊,陈砚正给“城市记忆”长卷题最后的落款,“比画的还多了道弯呢。”
陈砚放下笔,手里还捏着支朱砂笔。他走到树旁,用指尖碰了碰新叶,转身从画案上取来宣纸,把叶片的形状拓了下来:“这是春天给长卷添的新纹样。”拓片边缘,他忽然想起什么,添了行小字:“甲辰年春,新叶合卷”,字迹的笔锋和苏晚绣线的弧度隐隐相合。
进阶班的年轻人带着各地手艺人的续卷来了。水乡的绣娘寄来片菱角纹绸布,布上的水纹用鱼线绣出粼粼的光;山里的竹编师傅送了段竹篾编的花边,纹路里缠着苏晚早年寄去的丝线;连邻市那位白发老先生,都托人捎来幅墨梅图,梅枝的末端留着片空白,旁边写着:“该让新枝接老干了”。
“我们想在长卷的末端缝个‘续卷扣’,”年轻人指着个银质的搭扣,“扣上刻着‘未完待续’四个字,谁想添故事,解开扣就能接上自己的布,让长卷像条没有尽头的河,流过一个又一个春天。”
苏晚选了块母亲当年没绣完的春桃布,布角还留着半截断线,她用新抽的蚕丝把断线接起来,接痕处故意留了点毛边,像春风拂过花瓣的绒毛。“老针脚不能全接死,”她对着光看接缝,“得让风带着走,才知道新绿长在哪。”
陈砚在续卷的空白处画了串小符号:有的像绣针,有的像墨锭,最末个符号是只衔着线头的燕子,翅膀的纹路和去年“归燕新篇”里的那只一模一样,只是羽毛更丰茂了些,像飞过了万水千山。“符号记着走过的路,”他给符号描边时说,“新添的布记着要去的地方,凑在一起,才是光阴的全乎劲儿。”
清明那天,长卷在回春巷的广场上合卷。滚动的卷轴缓缓展开,从最初的回春巷石板路,到后来的水乡菱角、山里竹篾,再到此刻新接的春桃布,人群里响起片低低的惊叹——春桃布的末端,已经绣了只振翅的蝴蝶,是念念踩着板凳绣的,针脚歪歪扭扭,却把翅膀的弧度绣得格外灵动,像真的要从布上飞出来。
“这哪是长卷,”修鞋匠摸着布上的针脚笑,“是把咱们这辈子的日子,都缝成了幅活画。”他让学生取来笔墨,在空白处题了行字:“针脚作舟,渡岁月河”。
机器人工程师带着机械臂来了,这次没让机器模仿人手,而是让它在合卷的边缘绣了圈细细的银线,银线的纹路里藏着所有手艺人的指纹——苏晚的、陈砚的、念念的,连那位白发老先生的指节纹都清晰可见。“机器学不会的温度,”他在旁边贴了张纸条,“就把指纹绣进去,让金属线也带着人的气。”
念念背着自己的小绣绷,在合卷的最末端绣了串小脚印,从布庄门口一直排到梧桐树下。“这是故事走的路,”她仰着脸对围观的人说,“以前的脚印浅,现在的深,以后我要让脚印一直走到天边,让所有没见过回春巷的人,都知道这里的针脚会开花。”
合卷仪式那天,布庄的人都来了。老手艺人轮流抚摸长卷的边缘,补伞的老太太用银丝在春桃布上添了滴雨珠,说“得让花沾点活气”;扎风筝的老师傅在蝴蝶翅膀上画了道气流线,笑着说“该让它飞得更远”。
苏晚把父亲的铜凿子轻轻放在长卷旁,凿头的纹路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她取来金线,在凿子印过的地方绣了个小小的“承”字,针脚一半是母亲的盘金绣,一半是自己的乱针绣,像两代人的手在字里相握。
“承得住才叫家,”她摸着“承”字的笔画,“不然长卷再长,也只是块没根的布。”
傍晚收卷时,夕阳把长卷的影子拉得很长,像条金色的河。陈砚把各地手艺人的续卷小心翼翼地收好,苏晚往收纳箱里塞了包新染的丝线,绿的像梧桐新叶,粉的像念念绣的桃花;陈砚则放了本空白的画稿,扉页上画了个简易的绣绷,旁边写着:“春风过处,皆可续笔”。
念念追着滚动的收纳箱跑,手里攥着片刚摘的梧桐叶,叶纹和长卷上的缠枝纹几乎重合。“叶子也要跟长卷走,”她把叶子塞进箱缝,“让它知道,回春巷的春天,会一直等着它回来。”
布庄的院子里,梧桐树下的新绿又长高了些。苏晚坐在绣架前,给“续卷扣”绣最后圈缠枝纹,陈砚则在旁边整理各地寄来的续卷,忽然发现某页空白处,有片被春风吹过的蒲公英绒毛,粘在“未完待续”的银扣上,像颗等着起飞的星。
“你看,”他指着绒毛笑,“连风都在说,这故事还得接着飞。”
苏晚笑着把绒毛吹向空中,针尖穿过绸布时,仿佛能听见老手艺人的咳嗽、年轻人的笑闹,还有长卷滚动时布料摩擦的轻响,都缠在“续卷扣”的银线里,随着风轻轻荡。而那棵老梧桐,正把满枝的新叶,悄悄铺在布庄的屋檐上,像给未完的长卷,搭了个永远向阳的架,等着新的布帛来接,新的针脚来绣。
檐下的风铃换了新的铜片,风一吹,声音里混着远处染坊的木槌声,咚、咚、咚,像在给合卷的长卷打拍子。苏晚放下绣针时,看见“续卷扣”的银线上,正缠着根细细的蒲公英绒毛,在春光里轻轻摇晃,像在说:别急,我们只是暂时合卷,下一个春天,还有更长远的故事要写呢。
锦绣记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在修改书名
- 简介正在更新
- 0.1万字8个月前
- 张仁霖:刚好合适
- 网络博主×知名舞蹈家的爱情生活。前期培养感情,后期养育宝宝
- 3.1万字3个月前
- lustsin(剧情有删或改不影响看)-d593
- 0.9万字3个月前
- 豪门风云传云澜传奇
- 豪门风云传云澜传奇古镇夜色豪门惊梦豪门归来云澜传奇瓷影药香玉骨茗茶玉茶茗骨雪顶寒翠豪门世家豪门千金豪门贵族豪门少爷豪门少主豪门公主皇家贵族欧......
- 50.4万字3个月前
- 他长得挺帅的
- 一年迟到的初雪,是余袅喜欢他的开始。次年即将来临的夏日,是余袅决定放下他的日子。“但是决定这个东西,我努努力不就可以改变了么”陈峥对自己的脸......
- 1.4万字1周前
- 江先生的贴贴指南
- 宠物咖啡馆老板江熠第一次见到绘本作家温眠时,怀里的布偶猫正踩在她的裙摆上——他盯着那截露出来的脚踝看了三秒,突然说:“你的裙子,比猫爪垫还软......
- 3.6万字23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