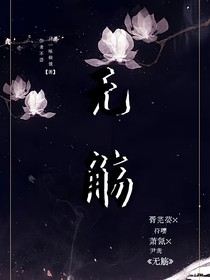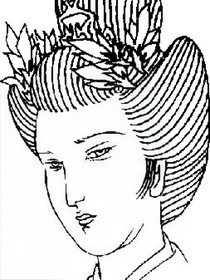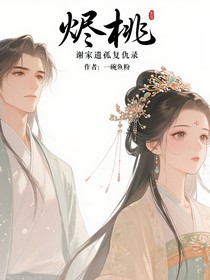税吏的马蹄声
第26章:税吏的马蹄声
矿镇的麦子刚抽穗,绿得像泼了颜料,风一吹,浪头滚到天边。赵夜蹲在田埂上,手里攥着把土,捏碎了,顺着指缝漏下去——是好土,含着腐叶的软,能养庄稼。
“赵先生,你闻这麦香!”周铁山扛着锄头过来,裤腿卷到膝盖,沾着泥,脸上却笑开了花,“俺爹说,麦香浓的年成,收成就差不了。”
赵夜没说话,耳朵却动了动。不是风声,不是虫鸣,是马蹄声,从镇口的方向来,很轻,却带着股生人味。
李根的伤早好了,正带着几个半大的娃在铁匠铺打铁,叮叮当当地打镰刀。听见马蹄声,他把镰刀往铁砧上一放,抄起墙角的燧发铳——虽然熔了不少火器打农具,但赵夜还是留了十支,藏在铺子里,防备万一。
“别怕,先看看。”赵夜按住他的手,指尖能感觉到李根的肌肉在绷紧,像拉满的弓弦。
镇口的瞭望哨跑回来了,是那个七八岁的娃,叫小石头,腿跑得飞快,鞋都跑掉了一只:“是……是官爷!穿蓝衣服的,骑着马,还带着刀!”
蓝衣服?赵夜心里一沉。是南明的税吏。听说南边的官府重新立了章程,不管是流民还是乡绅,见地就收税,号称“复明捐”,其实就是抢。
税吏的马蹄声越来越近,踩在镇子的土路上,“嗒嗒”响,像敲在每个人的心上。钱通把流民往铁匠铺里赶,老婆婆把娃护在身后,春丫则往火塘里添了根粗柴,手却在发抖——她见过税吏抢粮,连最后一把种子都不放过。
三个税吏骑着马,耀武扬威地站在镇口,为首的留着山羊胡,腰间的刀鞘擦得锃亮,目光扫过田里的麦子,像饿狼盯着肥肉。
“都出来!”山羊胡扯着嗓子喊,马鞭往地上抽,“奉南明巡抚大人令,征收‘复明捐’,熟地一亩交麦三斗,铁器按斤算,火铳……嘿嘿,得上交充公!”
没人动。周铁山把锄头往地上一顿,挡住税吏的马:“俺们这是荒地,自己开的,不交!”
“荒地?”山羊胡冷笑,马鞭指着铁匠铺,“那是什么?铁砧子都亮得反光,还敢说没东西?给我搜!”
两个跟班刚要下马,李根突然从铺子里走出来,手里举着把新打的镰刀,刃口在太阳下闪着光:“搜可以,先问问这刀答应不。”
税吏的马被吓得往后退了半步。山羊胡的脸色变了变,却梗着脖子喊:“反了你们!知道巡抚大人带了多少兵吗?三千!踏平你们这破镇子,跟踩死蚂蚁一样!”
赵夜慢慢走过去,手里还攥着把刚拔的草,草根带着湿泥。他没看税吏,只是蹲下来,把草扔回田里:“这地去年还是石头滩,弟兄们用手刨,用铳管撬,才开出这二十亩。三斗麦,是俺们半年的口粮。”
“管你们怎么开的!”山羊胡的马鞭几乎抽到赵夜脸上,“朝廷的规矩,就得交!”
“朝廷?”赵夜抬起头,虽然看不见,却像有目光落在税吏脸上,“洛阳城破的时候,朝廷在哪?清军屠村的时候,朝廷在哪?俺们自己种粮活命,倒成了‘规矩’该收的?”
他的声音不高,却让税吏的马鞭僵在了半空。周围的流民慢慢围过来,有拿锄头的,有握镰刀的,连小石头都捡起块土疙瘩,攥得紧紧的。
“赵先生,别跟他们废话!”钱通往手里吐了口唾沫,“俺们有铳,怕他个鸟!”
“把铳收起来。”赵夜低声道,然后转向山羊胡,“麦可以交,一斗,不能再多。铁器……可以给你们两把镰刀,算‘孝敬’。”
这是他能做的最大让步。真打起来,税吏虽然不经打,但南明的兵迟早会来,矿镇经不起再一次的战火。
山羊胡盯着赵夜看了半天,突然笑了:“算你识相。但一斗太少,两斗!再加一把火铳!”
“火铳没有,镰刀可以多给一把。”赵夜站起身,“就这些,要就要,不要……”
他没说完,但围上来的人往前凑了半步,锄头和镰刀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
山羊胡咬了咬牙,显然没料到这群流民这么硬气。他瞥了眼田里的麦子,又看了看铁匠铺里隐约露出的铁家伙,最终哼了一声:“两斗!后天我来取!少一粒,烧了你们的铺子!”
说完,调转马头,带着跟班扬尘而去,马蹄声在土路上越来越远,像条跑掉的蛇。
“真给他们?”李根把镰刀往地上一插,气鼓鼓的,“这就是明抢!”
“先给。”赵夜往田里走,继续拔草,“让周叔去通知瞭望哨,往南多派两个人,看紧点。钱通,把那支炸膛的旧铳找出来,修修,给他们。”
“给炸膛的?”钱通眼睛一亮,“妙啊!让他们拿去炸自己!”
赵夜没笑,只是摸着麦穗:“他们要的不是铳,是个面子。但这面子给了,里子得咱们自己攥着。”
他让周铁山带着人,在镇子周围的山道上埋了铁蒺藜,又让李根把留着的燧发铳擦亮,藏在铺子里的暗格里——防的不是税吏,是他们背后的兵。
夜里,春丫给大家煮了麦粥,里面掺了新摘的野菜。老婆婆端着粥,突然给赵夜跪下了,磕了个响头:“赵先生,俺们拖累你了……要不,俺们跟他们走,给你换点清静?”
赵夜赶紧把她扶起来,粥碗在手里晃出了汤:“说啥呢?来了就是一家人。兵来了,咱就往山里躲,地还在,人还在,总有回来的时候。”
李根在磨铳,擦得比自己的脸还干净。他突然说:“赵先生,俺想明白了,这税吏就是纸老虎。真来了兵,俺们的燧发铳也不是吃素的!大不了,再往南走,总能找到不收税的地方。”
“不往南走了。”赵夜望着窗外的麦子,月光洒在穗上,像铺了层霜,“要走,也是他们走。这地是咱的,凭啥让?”
他的声音很轻,却让铺子里的人都静了下来。钱通突然想起赵夜总在画的那张图,上面标着引水渠、仓库、甚至还有间学堂——他不是在躲,是在一点一点地,把这矿镇变成家。
第二天,赵夜让人把两斗麦装在麻袋里,放在镇口,又加了两把镰刀,却没给那支炸膛的铳。
税吏没来。
瞭望哨说,他们在十里外的山口打转,不知道是不是怕了,迟迟没敢进来。
周铁山扛着锄头往田里走,哼着小曲,脚步比昨天更稳。李根教娃们打铁,锤子落得有板有眼。春丫带着妇女们纺线,线轴转得飞快,像在织一张看不见的网,把矿镇的人都网在里面。
赵夜蹲在铁匠铺前,继续打犁头。铁砧声“叮当”响,和着田里的风声,麦子的拔节声,像支没谱的歌。
他知道,税吏还会来,南明的兵也可能真的来。但只要这铁砧还响,这麦子还长,这镇子里的人还在,就总有办法。
乱世里的家,从来不是等来的,是用手刨出来的,用铁敲出来的,用一口气撑出来的。
(本章完)
盲龙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无觞
- 大体内容还在构思哦
- 3.3万字6个月前
- 复相思:灵途复启相思劫
- “余景淮,我想起来了……全都想起来了……”“嗯,想起来了?”“我早就是你的人了。”“君已识,复相思”“莫忘你,但我还是……”“现在不是记起来......
- 2.8万字6个月前
- 感受中国传统女性故事
- 描述历史人物的故事。
- 1.5万字3个月前
- 衿生无悠
- 灵根分为六种:天品灵根、上品灵根、良品灵根、中品灵根、下品灵根和凡品灵根。女1、男1:林悠悠、沈子衿女2、男2:雪雯欣、季叶安“沈子衿在仙魔......
- 2.6万字3个月前
- 烬桃:谢家遗孤复仇录
- 本书以武将世家谢府覆灭为引,讲述谢砚与林婉这对
- 2.0万字1个月前
- 玉阶庶影,重生嫡女谋
- 前世,中书侍郎嫡女苏清沅惨死于定安侯府嫡子沈晏辰与穿越女林晚之手,闺中密友太子妃江若蘅亦含恨而终。重生归来,她誓要改写命运。表面温婉娴静的她......
- 2.0万字7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