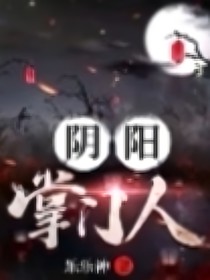画框里的针
雨停时,沈砚之站在《寒江独钓图》前,指尖抚过画框磨损处的字迹。“雪藏此画”——李建国说的“雪”,或许不只是隐喻,而是指李雪。他摘下画,画背贴着张桑皮纸,纸上用墨砂画着幅简易地图,标注着书房西墙的位置,与之前发现账册碎纸的砖缝完全对应。
“这画框里有东西。”沈砚之轻叩木质边框,听见空洞的回响。他用钢笔撬开嵌着画的木条,里面藏着根银针,针尾缠着圈细铁丝,铁丝上沾着银灰色粉末——正是掺了铅的墨砂。针身刻着极小的字:“正月十三,子时”。
“十年前的正月十三,正是李副镇长出事的日子。”老陈蹲在墙角,双手插进头发里,“那天夜里,我看见赵镇长拿着这画进了书房,出来时画框上沾着墨砂,他说是不小心蹭到的。”
沈砚之捏起银针对着光,针尖磨得极锐,针孔大小与书房窗玻璃上的孔完全吻合。“有人用这根针,从窗外往屋里注射铅砂。”他忽然想起李雪袖口的暗红色,“文竹的根须能吸收铅砂,可它的汁液氧化后会变成暗红色——你昨夜是不是剪过文竹的根?”
李雪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带着雨珠滚落的凉意:“我只是想看看,这花里藏了我爸多少冤屈。”她手里捧着个瓷瓶,瓶身上的兰花缺了块,正好能和井里捞出的碎瓷片拼合,“这是我爸的砚滴,他总说,好墨要配好水。”
瓷瓶里装着半瓶清水,水底沉着几粒墨砂。沈砚之倒出清水,发现瓶底刻着“账册在纸坊第三排桑皮纸中”。他忽然明白,李建国当年并未把所有账册藏在井里,而是分了两处——纸坊的桑皮纸里藏着正本,画框里的地图和瓷瓶的提示,是留给知情人的线索。
“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些的?”
“三个月前整理我爸的书稿时,”李雪的指尖划过瓶身的缺口,“我在《青瓦镇志》的夹页里找到这瓷瓶,还有张字条,说赵德发会在十年后的正月十三销毁最后证据。”她抬起头,眼里蒙着层水汽,“我没想要他死,只是想让他把账册交出来。”
沈砚之看向那支断尖的狼毫笔,笔杆里是空的,藏着张折叠的桑皮纸。纸上是赵德发的字迹,记录着十年前的经过:他挪用公款后,用伪造的报销单嫁祸李建国,又趁李建国在书房核对账册时,用浸了铅砂的文竹刺扎伤其手指,伪造了自杀现场。而那支刻着“赠建国”的笔,本是李建国的,赵德发一直带在身边,或许是为了提醒自己,或许是为了掩盖什么。
“昨夜你去书房,就是为了放这支笔?”沈砚之展开纸,边缘有新鲜的折痕,“你知道赵德发有翻旧物的习惯,故意把笔放在他会触碰的地方,让他被断尖划伤,接触到残留的铅砂。”
李雪没否认,只是把瓷瓶抱在怀里:“我爸当年被扎伤后,知道自己中了毒,急着把账册藏好,才在镇志上写下批注,又把线索藏进画里。他说过,赵德发贪财却胆小,只要让他看见这些,一定会自乱阵脚。”
沈砚之走到窗台,那盆文竹的根部缠着根细铁丝,铁丝一端连着窗外的老槐树。“你用铁丝把银针固定在窗玻璃上,趁雨夜从树上爬过去,往屋里吹铅砂。可你没想到,赵德发翻镇志时被文竹刺扎伤,已经中了毒,你的针只是加速了他的死亡。”
窗外的槐树叶上还沾着墨砂,与铁丝上的粉末一致。沈砚之忽然注意到,树叶间挂着片桑皮纸,纸上是李雪的字迹:“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老陈突然哭出声:“是我对不起李副镇长……当年他给过我工钱,让我别帮赵德发做坏事,可我……”他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几张完整的账册,“这是昨夜赵镇长让我烧的,我没舍得,藏在了灶台里。”
账册上的字迹清晰,赵德发挪用公款的记录、伪造签名的痕迹、与外乡商人的交易明细,一目了然。最后一页贴着张字条,是李建国的笔迹:“若我儿雪见此,当知父清白,勿以恶报恶。”
沈砚之把账册放进证物袋,阳光透过窗玻璃照进来,在地上投下银针的影子,像根悬着的线,一头系着十年前的冤屈,一头连着此刻的尘埃。李雪把瓷瓶放在书桌上,瓶身的兰花与钥匙、钢笔上的花纹终于拼合成完整的一朵。
“这墨砂,本是用来存字的,”沈砚之看着纸上渐渐干涸的字迹,“没想到最后存下的,是人心。”
青瓦镇的炊烟升起时,沈砚之走出镇长宅邸,桑皮纸的墨香混着雨后泥土的气息,在巷子里漫开。他回头望了眼西厢房的窗,那盆文竹的叶片上,正凝结着新的水珠,像滴未落的泪。
纸间魅影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文轩:垫垫脚尖
- /将进酒文社/【双男主】“那说好了,拉钩”刘耀文和宋亚轩一个长久的约定。
- 0.7万字7个月前
- 异样四楼
- 那晚回家电梯坏了,楼梯太黑,我让我妈下来接我。她带着我上楼时,我手机却响了,来电人居然是【妈妈】。我一接听,就听到我妈说:「我到楼下了,你跑......
- 1.1万字5个月前
- 斩神之代理三千混沌魔神
- 【大道神殿+九转玄功+混元道经+混沌魔神】天宇穿越斩神世界,成为林七夜同学,觉醒了大道神殿,开局获得修仙之法。大道神殿内每苏醒一位魔神,天宇......
- 2.3万字3个月前
- 郁优瀛天下第一
- 1-19话的郁优瀛的瀛写成赢了有三点水,是郁优瀛,不是郁优赢我被小鱼仔本人拍私了,但是他也差不多两兄弟写到19话才发现字打错了
- 8.8万字3个月前
- 无声奏鸣
- 音乐天才的陨落:周沉曾是备受瞩目的钢琴天才,因一场车祸失去听力,从此陷入绝望深渊,放弃音乐梦想,在酒吧当调酒师度日。神秘顾客:酒吧常客林教授......
- 1.2万字2个月前
- 阴阳掌门人:降魔
- **本座**乃**玄门正统**,执掌阴阳,号令五行,专诛邪祟、镇妖魔!
- 2.0万字6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