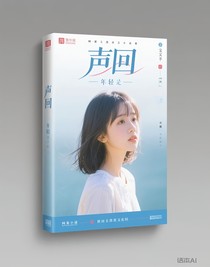纸坊的余烬
青瓦镇的晨雾裹着水汽,在巷子里漫成一片白茫茫。沈砚之踩着青石板上的水洼往镇东头走,鞋跟敲出的声响被雾吸走大半,倒显得纸坊方向飘来的桑皮纸浆味愈发清晰——那味道混着草木的青涩与石灰的微苦,像极了李建国留在书稿里的批注字迹,看似平淡,细品却藏着千斤重。
纸坊的木门挂着把铜锁,锁孔里塞着半片桑皮纸,纸边还带着新鲜的撕裂痕。沈砚之认出那是李雪常用的纸,纤维里嵌着点墨砂的银灰,和画框里的铁丝上沾的粉末如出一辙。他轻轻抽出纸片,锁“咔嗒”一声开了,像是有人特意为他留的门。
“后生来得比我想的早。”
墙角的竹椅吱呀作响,守坊的老头从烟袋锅里磕出灰,火星落在潮湿的地面上,洇出个深色的圆点。老头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袖口磨出了毛边,倒让沈砚之想起李建国书稿里夹着的老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同款褂子,正蹲在纸浆池边,手里举着张刚捞起的桑皮纸,笑得露出白牙。
“您认识李副镇长?”沈砚之目光扫过墙上的旧物,最显眼的是张泛黄的奖状,“青瓦镇桑皮纸技艺传承人 李建国”几个字被虫蛀了边角,却依旧看得清笔锋里的力道。
老头往火盆里添了块炭,炭块炸开的火星映亮他眼角的皱纹:“何止认识。当年这纸坊是他拉着大伙建的,说桑皮纸能写字,更能记良心。”他指了指第三排木架,“那排的桑皮纸用的是镇西的泉水泡的,他说水好,纸里就带着股硬气,能存住真东西。”
沈砚之走到第三排木架前,指尖刚碰到最底层的纸卷,就觉出不对劲。别的纸卷都用细麻绳捆着,唯独这卷用的是红绸带,绸子边缘磨得发亮,像是被人反复解开又系上。他解开绸带时,指尖触到一点黏腻的湿意,凑到鼻尖闻了闻,是草木汁液混着血的腥气——和李雪袖口那抹暗红如出一辙。
“昨夜后半夜,有个姑娘来这儿翻纸。”老头的烟袋在火盆沿上磕了磕,“穿件灰布衫,头发上还沾着槐树叶,一看就是刚从镇长家那边过来的。她翻到第三排时,被竹架上的倒刺划了手,血滴在纸上,红得发黑,跟当年李副镇长滴在纸浆里的血一个色。”
桑皮纸一层层展开,最里面裹着本蓝布封皮的账册。封皮上烫着个“正”字,边角却泛着焦黑,像是被火燎过又匆匆摁灭。沈砚之翻开第一页,墨迹深黑如漆,是李建国惯有的小楷,一笔一画记着青瓦镇的收支:“三月初二,购桑树苗五十株,支银二十两”“五月十五,修镇西石桥,支银一百五十两”……翻到中间,字迹突然变得潦草,纸页边缘还沾着点暗红的印记,像是写字人握笔的手在剧烈颤抖。
“七月初三,赵德发取公款三百两,称购赈灾粮,实与王老板私分”“八月十五,镇西林地过户文书存疑,赵德发伪造签字”……沈砚之的指尖停在最后几页,这里的墨迹洇得厉害,有些字几乎要晕成一团:“赵德发与王老板交易,以镇西林地抵押,得款三万,账册副本已寄县纪委……”后面的字被烧得只剩个残缺的“火”字,边缘卷成焦黑的弧度,像是被人用烛火匆匆燎过。
“十年前正月十三夜里,这纸坊着过场小火。”老头往火盆里又添了块炭,火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忽明忽暗,“就烧了第三排的纸,别处一点火星都没沾。李副镇长第二天就没了,谁也说不清是巧合还是……有人故意烧账册。”他顿了顿,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层层打开,里面是半块烧焦的桑皮纸,“这是我当年从火堆里抢出来的,上面有李副镇长的字,你看这‘德’字的写法,跟赵镇长平日里写的是不是有点像?”
沈砚之把两块残纸拼在一起,烧焦的边缘严丝合缝。李建国写的“赵德发”三个字里,“德”字的中间少了一横,而赵德发笔杆里那张桑皮纸上的签名,“德”字同样少了一横——这不是笔误,是李建国在悄悄留下标记。
“那姑娘拿走了另外半张烧残的纸。”老头指了指墙角的灰烬堆,里面还能看到点没烧透的纸渣,“她说要去镇西林地看看,那里的松树去年死了一片,开春后有人看见赵镇长带着铁锹去过好几回,树根底下怕是埋着东西。”
沈砚之刚把账册塞进证物袋,手机就突然响了,铃声在空旷的纸坊里显得格外刺耳。是老陈,声音里带着哭腔,还有种抑制不住的惊慌:“沈先生,你快来镇政府!赵镇长的办公室里……发现了王老板的尸体,手里攥着半张桑皮纸,跟你说的账册纸一模一样!”
挂了电话,沈砚之回头看那排木架,第三排最顶层的桑皮纸不知何时被风吹开一角,露出后面藏着的东西——是半截文竹的枝条,断口处还在往外渗着黏糊糊的汁液,氧化成暗褐色,滴在地上,晕开一个个小小的圆点,像谁在纸上点的墨。
老头突然站起身,往纸坊深处走:“李副镇长当年在纸浆池底下藏了个东西,说要是他出事了,就把这东西交给敢查到底的人。”他掀开池边的石板,下面露出个锈迹斑斑的铁盒,打开时,里面的东西让沈砚之瞳孔一缩——是枚公章,青瓦镇政府的公章,章底沾着点银灰色的粉末,和针上的墨砂同色。
“这章十年前就该在赵镇长手里,怎么会在这儿?”沈砚之指尖抚过公章上的裂痕,“李副镇长当年是发现有人用假章盖章,才藏起了真章?”
纸间魅影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极夜捍卫者
- “狩猎者”的故事已经落幕,但“极夜”的历程仍未走到终点。先前的一切终将是要后人捍卫的,而捍卫的背后也隐藏着无数的杀机。紫色激情的首领蜘蛛......
- 13.4万字6个月前
- 吾期顽妻
- 正剧,背景大学校园,单男单女主,施雅墨✕风鹤行,强强联手,全员恶人。非传统意义恋爱文,作者小白一只。架空,类死亡谷世界,伏笔一堆又一堆,另类......
- 2.2万字5个月前
- 我的重生(妹妹所写)-d848
- 简单讲述女主重生把男主杀掉
- 0.3万字4个月前
- 吃瓜群众,在线粮仓
- 1.为本人各种类型文字收集册2.经常调整整理分卷、目录3.不喜勿入
- 0.4万字3个月前
- 回声声回
- 徽章被卡在他的校服里面,只漏出半只展翅的鹰。
- 1.6万字7天前
- 忆起君破焓
- 江泽源小时候和小姨玩捉迷藏,却因小姨被鬼杀了,在寻找小姨被杀线索途中。遇到了催忆阳,并加入了归墟小队,在途中催忆阳恢复了前世记忆,并想方设法......
- 1.3万字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