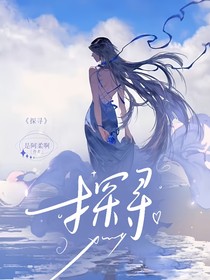第十一章:孤帆系归舟
处暑的晚风带着咸涩的潮气,漫过渔港的每一寸石板路。令秋踩着退潮后湿漉漉的码头时,听见系船柱上的缆绳发出咯吱的声响,混着远处归航渔船的马达声,像是新旧时光在低声絮语。栈桥尽头泊着艘半朽的木船,船身的桐油早已褪成灰白,甲板上的渔网纠缠如蛛网,唯有船头雕刻的鲤鱼跃龙门纹样,仍在残阳里透着几分当年的精气神。
“王,”令秋将往生簿垫在潮痕未干的礁石上,纸页边缘沾着细碎的贝壳屑,“林望潮,男,四十二岁,民国三十六年秋殁于台风。在此渔港捕鱼二十载,水性冠绝百里,最后一次出海,为救同船的三个年轻渔民,被巨浪卷走。魂魄被他常年系在船头的红绸带缚着,每逢月圆,就会驾着虚影渔船在近海徘徊,渔网撒下又收起,像是在打捞失落的光阴。”
南川立在防波堤的青石上,玄色衣袍被海风掀起,衣摆处的幽冥纹在水光里明明灭灭。他望着那艘木船的虚影——穿粗布短打的汉子正蹲在甲板上补网,指间的麻线在残阳里划出银亮的弧线,后腰别着的酒葫芦随着动作轻轻晃动,发出细微的碰撞声。此人肤色黝黑,手掌布满老茧,唯有双眼亮如星辰,望向前方时,仿佛能穿透浓雾,直抵鱼群洄游的深海。
“是哪个后生忘收网了?”虚影忽然抬头,声音带着海风打磨出的粗粝,目光扫过空荡的码头,最终落在南川身上,“这鬼天气要变了,不收网等着喂鱼吗?”
“林大哥,”令秋将魂灯往栈桥边送了送,暖黄光晕在潮湿的空气里晕开,驱散些许海腥味,“您已在此守了七十七年。民国三十六年那场台风,您救下的三个渔民,后来都成了渔港的船老大。他们在您出事的海域设了座航标灯,灯柱上刻着‘望潮归’三个字,说要让您无论漂到哪里,都能看见回家的路。”
林望潮补网的手顿在半空,麻线从指间滑落,在甲板上缠成个松散的结。他望着防波堤外的浪花,那里翻涌的白浪像无数破碎的镜子:“柱子他娘还在等他吃饭吗?那小子总爱跟我抢咸鱼,却不知我特意多晒了一串,就等着他出完这趟海……”
“柱子后来开了家渔货铺,”南川的目光落在船头的红绸带上,绸面虽已褪色,却依旧系得紧实,“铺子里总挂着两串咸鱼,他说一串是给活人的,一串是给海里的林大哥留的。每逢您的忌日,他都会划着小舢板,在航标灯下多放一碗酒。”
林望潮忽然抓起酒葫芦往嘴里倒,却什么也没倒出来,只有虚影的喉结徒劳地滚动着。“那小子当年偷喝我的米酒,被他爹追着打,还是我把他藏在船舱里。”他忽然笑出声,笑声里混着海风的呼啸,“他总说要学我的本事,却不知渔民的本事不在网里,在浪里。”
“柱子的儿子现在是海洋研究所的博士,”令秋将魂灯往船边挪了挪,光晕里浮出些微虚影——穿白大褂的年轻人正蹲在航标灯下,将一个装着字条的玻璃瓶投入海中,瓶身的反光在浪尖跳跃,像颗流动的星,“他说要替爷爷和林爷爷,弄明白台风的脾气,让这片海少吞些人。”
林望潮望着那些虚影,补网的麻线从掌心滑落,魂体周围的空气泛起涟漪,带着咸涩的水汽。他望着远处的航标灯,灯光在暮色里忽明忽暗,像只永不闭合的眼睛:“我爹就是被台风卷走的,”他声音低了些,带着海雾般的沉郁,“我总说要让这片海怕我,到头来还是没斗过它。”
“现在它怕了。”南川从袖中取出枚贝壳,贝壳内壁泛着珍珠母的虹彩,“这是去年深海探测船捞上来的,上面刻着的‘林’字还清晰。他们在航标灯旁建了座海洋博物馆,里面摆着您当年的渔网,旁边写着‘勇者的渔具’。”
林望潮接过贝壳,指尖的魂体穿过那层薄薄的壳壁,触到刻字时忽然愣住。海浪在此时变得温柔,轻轻拍打着船身,像是在哼一首古老的渔歌。“我娘说,贝壳能听见海底的声音,”他忽然将贝壳贴在耳边,嘴角扬起久违的弧度,“你听,它们在说,今年的带鱼要丰收了。”
令秋将魂灯举到船舷边,暖黄的光晕如潮水般漫过他的魂体:“跟我们走吧。地府在忘川渡口新造了艘‘渡魂舟’,缺个识水性的舵手。您去了,既能摆渡魂魄,也能时时看着这片海——那些后生说,要让‘望潮归’的灯,永远为晚归的渔船亮着。”
林望潮最后望了眼渔港——码头上的吊臂正吊起满舱的渔获,鱼腥气里混着人声的喧闹,年轻的渔民们扛着渔网奔跑,汗水在夕阳下闪着光,像极了当年的自己。他将那枚贝壳轻轻放在舵盘上,红绸带忽然被风吹起,缠上魂灯的提杆,像是在主动告别。
“告诉柱子,”他的声音在光晕里渐渐远去,却带着浪涛般的厚重,“起网时别太急,让鱼儿多留些子,明年才有的捞。”
魂灯被收入怀中时,令秋听见船舵发出轻微的转动声,仿佛有人在最后校准一次航向。他看向南川,见这位鬼王正望着归航的渔船,玄色衣袍在暮色里与海面的霞光交融,衣摆的幽冥纹竟泛出温暖的金芒。
“王,这渔民的魂魄,倒比浪花还坦荡。”
“民国三十六年秋,我在这片海域收过七个渔民的魂,”南川转身离开防波堤,礁石上的水渍在他身后连成串,“他们都说,跟着林望潮出海,哪怕船翻了,心里也踏实。”
暮色四合时,航标灯忽然转得急促,光束在海面上划出明亮的弧线,像是在为某位晚归的亲人引路。令秋望着怀中的魂灯,忽然明白,有些勇气从不必挂在嘴边,一张修补的网,一盏不灭的灯,就足以在时光里竖起航标;有些牵挂也从不会被海浪冲淡,就像这船头的红绸,这贝壳里的海声,永远都在诉说着“渡”与“归”的深意。
白露的霜花缀满了古宅的黛瓦,将屋脊上的吻兽染成一片素白。令秋推开那扇嵌着铜环的木门时,门轴发出“咿呀”的长吟,像是老者在诉说往事。庭院里的石榴树早已枯朽,却仍有一枝倔强地伸向天空,枝桠间挂着个褪色的风筝,竹骨在风中轻轻颤动,宛如欲飞的蝶。正房的窗台上摆着几枚瓦当,纹样有卷草、有云纹,边缘虽已残破,却依旧能看出当年的精雕细琢,日光透过瓦当的孔洞,在青砖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是散落的星子。
“王,”令秋用麂皮擦拭往生簿上的薄霜,纸页已泛黄发脆,“顾景明,字叔言,男,五十八岁,民国二十五年冬殁于战乱。在此宅居住三十载,是位研究古建的学者,收藏的瓦当能装满整整两箱,城破时,为保护一幅宋代《营造法式》手稿,被炮弹碎片击中。魂魄被他最珍爱的那枚饕餮纹瓦当缚着,每逢霜夜,就会在庭院里徘徊,指尖抚摸过每一处墙缝,像是在为古宅诊脉。”
南川立在正房的廊下,玄色衣袍上落了层霜,却未融半分。他望着庭院里的虚影——穿藏青棉袍的老者正蹲在墙根,手持放大镜细细查看砖缝里的苔藓,袖口沾着些尘土,鼻梁上架着副老花镜,镜片后的眼睛专注而明亮,仿佛能穿透砖石,看见千年前的营造匠心。他手中的锦盒里,正躺着那枚饕餮纹瓦当,纹路狰狞却威严,是汉代遗物。
“是哪个孩子在踢瓦当?”虚影忽然抬头,声音带着书卷气的温和,目光落在满地的光斑上,“这些老物件脆着呢,碰不得。”
“顾先生,”令秋将魂灯往廊下送了送,暖黄光晕在霜地上晕开,融开一小片暖意,“您已在此守了九十年。民国二十五年那场战乱,您保护的《营造法式》手稿,现在藏在国家图书馆的恒温柜里,旁边摆着您收藏的瓦当拓片,说明牌上写着‘守护者顾景明’。”
顾景明抚摸砖缝的手顿在半空,棉袍的下摆扫过枯石榴树的根部,带起些微尘土。他望着正房的梁柱,声音轻得像霜落:“东厢房的斗拱该修了,那年我就说过,榫卯松了会塌……还有西窗的雕花,被白蚁蛀了个洞……”
“东厢房的斗拱,去年修古建时换了新的榫卯,”南川的目光落在正房的梁架上,那里有一处修补的痕迹,木材的新旧差异清晰可见,“工匠们说,按您当年在笔记里写的法子修的,严丝合缝,比机器做的还准。”
顾景明的镜片后闪过些微讶异:“他们……竟还看得懂我的字?”
“您的笔记整理出版了,叫《瓦当识古》,”令秋将魂灯往窗台下挪了挪,光晕里浮出些微虚影——一群穿工装的年轻人正围着一张古建图纸讨论,图纸旁摊开着本泛黄的笔记,正是顾景明当年所书,“他们说,您写的‘看瓦当知年代,摸砖缝晓匠心’,现在是古建修复的口诀。”
顾景明望着那些虚影,忽然笑了,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欣慰,却有泪顺着沟壑滑落,滴在冰冷的瓦当上,化作点点荧光。“我年轻时总说,修古建像给老人治病,”他轻轻叩击着墙根的砖块,“得顺着它的性子来,不能硬来。那些后生……总算听进去了。”
南川从袖中取出张拓片,上面是那枚饕餮纹瓦当的全貌,纹路间还能看见当年炮弹擦过的裂痕:“这是修复工匠们特意拓的,说要刻在古建博物馆的墙上,让所有人都知道,有位先生用性命护过这些老东西。”
顾景明接过拓片,指尖的魂体穿过薄薄的宣纸,触到那些熟悉的纹路时,忽然对着虚空作了个揖,像是在向某位看不见的匠人致敬。“这瓦当是我年轻时在长安旧城砖堆里捡的,”他声音里带着对往事的怀念,“当时它碎了半块,我用糯米浆粘了三年才复原,没想到……”
“没想到它会替您看这古宅重建。”令秋将魂灯举到他面前,暖黄的光晕如薄纱般裹住他的魂体,“跟我们走吧。地府在轮回殿旁建了座‘古建苑’,缺个懂营造的先生。您去了,既能与历代工匠切磋技艺,也能时时望见阳间的古建——那些后生说,要让您守护的匠心,永远刻在砖瓦里。”
顾景明最后望了眼修复一新的正房——窗棂的雕花闪着新漆的光泽,却依着旧样复刻,瓦当虽换了新的,纹样却与他收藏的那枚分毫不差。他将拓片轻轻放在窗台上,与那些瓦当并排摆放,随后,魂体渐渐被魂灯的光晕完全裹住。
“告诉那些后生,”他的声音在光晕里渐渐远去,却依旧带着书卷气的温和,“修古建要像写史,不能添字,也不能漏字,得让后人知道,老祖宗的智慧,都藏在砖瓦缝里呢。”
魂灯被收入怀中时,令秋听见屋脊上的吻兽发出轻微的响动,像是在回应这位守护者的叮咛。他看向南川,见这位鬼王正望着那枚饕餮纹瓦当,玄色衣袍上的幽冥纹与瓦当的纹路隐隐呼应,生出几分跨越时空的默契。
“王,这学者的魂魄,倒比砖石还执着。”
“民国二十五年冬,我在废墟里收过不少魂,”南川转身离开,门轴的“咿呀”声在身后渐远,“只有他,还在惦记着未修完的斗拱。”
晨雾升起时,古宅的烟囱忽然冒出缕青烟,像是有人在灶房生火。令秋望着怀中的魂灯,忽然明白,有些守护从不必惊天动地,一枚瓦当,一页手稿,就足以在时光里筑起城墙;有些传承也从不会被战火焚毁,就像这榫卯的严丝合缝,这纹样的代代相传,永远都在诉说着“承”与“守”的重量。
霜降的寒气浸透了桑园旁的织坊,木梭撞击织机的声响早已沉寂,只余下檐角的蛛网在风中轻晃。令秋推开那扇挂着蓝印花布帘的木门时,闻到的不仅是桑皮纸的草木香,还有淡淡的蚕蛹味,混着陈年的丝线气息,让人恍惚间以为闯入了春蚕吐丝的梦境。织坊中央的老织机上,还绷着半匹未织完的云锦,金线与银丝在暗光里交错,像是凝固的星河,旁边的竹匾里堆着些蚕茧,虽已干瘪,却依旧能看出当年的饱满,阳光透过窗棂落在茧上,映出细密的纹路,宛如天然的诗行。
“王,”令秋将往生簿揣进怀里取暖,纸页边缘已被磨得光滑,“柳月娘,女,三十八岁,民国三十八年春殁于难产。在此织坊养蚕织布十六年,一手缂丝技艺冠绝乡里,临终前还在指导徒弟如何分辨蚕丝的优劣,魂魄被她亲手缫的第一缕蚕丝缚着,每逢月夜,就会坐在织机前,指尖在虚空中拨动,仿佛在编织一场未完的梦。”
南川立在织机旁的青石上,玄色衣袍在寒气里纹丝不动,衣摆处的幽冥纹在晨光里泛着冷光。他望着织机前的虚影——穿素色布裙的女子正坐在踏板前,将丝线穿过停经片,动作轻柔如拈花,鬓边别着朵绢花,是用缂丝技艺仿的牡丹,虽无香气,却栩栩如生。她的手指纤细,指腹却因常年拈丝而有些粗糙,可每当丝线在指尖流动时,那双眼睛就亮得惊人,仿佛能看见蚕丝里藏着的光影。
“是哪个丫头的丝线乱了?”虚影忽然抬头,声音带着江南女子的温婉,目光扫过空荡的织坊,最终落在南川身上,“缂丝要的是心细,一根线错了,整匹布就毁了。”
“柳娘子,”令秋将魂灯往织机前送了送,暖黄的光晕在寒气中晕开,驱散些许冷意,“您已在此守了七十四年。民国三十八年,您教出的徒弟,后来成了缂丝技艺的传承人,她在您的织机旁开了间工作室,收了二十多个徒弟,说要让您的手艺,像春蚕吐丝一样,绵绵不绝。”
柳月娘拈丝的手顿在半空,素色的袖口扫过织机,带落了几根散落的金线。她望着那半匹云锦,声音轻得像蚕啃桑叶:“阿芸的配色总差些灵气,”她忽然笑了,眼角的泪痣在晨光里格外分明,“我说过,要教她用凤仙花汁染丝线,那样的红色,才像春日里的桃花。”
“阿芸后来用凤仙花汁染的丝线,”南川的目光落在墙角的染缸上,缸底还残留着些暗红的花汁,像是昨日刚用过,“织成的《桃花图》被国家博物馆收藏,标签上写着‘柳氏缂丝传脉’。”
柳月娘的指尖在虚空中划出弧线,像是在模仿穿综的动作:“那丫头小时候总偷拆我的经线,被我罚着理线头,却不知理线头是学缂丝的第一步,心不静,线就理不清。”
“阿芸的孙女现在是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令秋将魂灯往染缸旁挪了挪,光晕里浮出些微虚影——个穿白大褂的姑娘正用显微镜观察蚕丝,旁边摆着本泛黄的笔记,封面上写着“月娘缂丝要诀”,“她把缂丝技艺用到了现代服装上,去年在国际时装周上获奖,领奖时她说,这荣誉,该分给九泉之下的柳师傅。”
柳月娘望着那些虚影,忽然低头,指尖轻轻拂过虚空中的丝线,魂体周围的空气泛起涟漪,带着
鬼王令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除妖师之魑魅魍魉
- 已签约,会持续更新。一件神器的丢失引发的巨大阴谋,所有人都身处漩涡之中,各种的尔虞我诈,各种的心怀鬼胎,把人性的恶展示的淋漓尽致。
- 41.6万字10个月前
- 玲珑之星:星辉女神2
- 星梦作为新一代的星灵守护者,肩负起探索星辉之源力量波动之谜的重任。她将独自踏上旅程,穿越森林、山脉和沙漠,寻找古老的秘密和未知的力量。在途中......
- 1.1万字9个月前
- 仙世界开局h仇人青梅竹马
- 简介正在更新
- 7.8万字6个月前
- 明日之王
- 我是沉沦中的王者,舍弃旧日世界,迎接新日世界,给你同样的经历,你未必能爬上我的位置。
- 1.2万字6个月前
- 傩面蚀月
- 都市白领苏棠收到三年前被毁古镇寄来的青铜傩面,戴上面具后右脸溃烂,浮现民国女子倒影。为破除七日血月诅咒,她深入沱江古镇,发现每代苏氏女子皆为......
- 1.1万字5个月前
- 探寻—我的秘密
- 梦、遗言到底想让我知道什么,我必须要探出这秘密。
- 1.8万字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