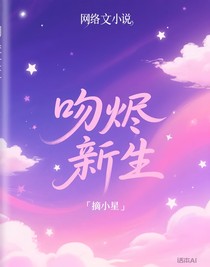第十章:枪魂寄残标
残阳如血,将镖局的青瓦染成一片赭红。令秋推开那扇脱漆的朱门时,檐角的铁马发出喑哑的碰撞声,混着院角老槐的落叶声,像是谁在低声诉说着陈年旧事。演武场中央的旗杆早已锈蚀,半面“威远”镖旗被风扯得猎猎作响,旗面的破洞处漏过斜阳,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宛如散落的星辰。
“王,”令秋用指尖捻去往生簿上的尘灰,纸页边缘的虫蛀痕迹里还卡着些细沙,“陆长风,字万里,男,三十九岁,道光二十五年冬殉于雁门关。掌威远镖局十二载,历三十七趟镖途未尝败绩,终为护朝廷饷银,力战悍匪于黑风口,身中十七创而殁。魂魄为其随身虎头镖所缚,每至朔风卷沙之夜,便在此演练枪法,枪风过处,瓦砾皆鸣。”
南川立在廊下的拴马石旁,玄色衣袍上的幽冥纹在残阳里泛着冷光。他望着演武场的虚影——穿玄色劲装的男子正持枪而立,左额的刀疤横贯眉骨,却丝毫不损其英气。那人手中长枪使得虎虎生风,枪尖划破空气的锐响里,还带着当年血战的余威,连周遭的风沙到了他身侧,都仿佛被枪风劈开,生生绕出条空道。
“是哪个后生,敢来偷学枪法?”虚影收枪定势,枪尖拄地的刹那,整院的风沙竟都静了静。他转过身时,目光扫过南川,虽见其周身阴气森森,却依旧挺直了脊梁,半点不见退缩。
“陆总镖头,”令秋将魂灯往演武场中央送了送,暖黄光晕在沙地上晕开圈柔和的光,“您已在此驻留一百八十二年。道光二十六年清明,幸存的镖师将您的虎头镖送回镖局,老镖师亲自为镖身缠上红绸,说‘枪魂寄于镖,英灵不远去’。”
陆长风握着枪杆的手紧了紧,指节处的魂体泛起淡淡的白影。他望着演武场中央的空位,那里本该立着尊铜像,却因年月久远,早已被风沙侵蚀得只剩个模糊的轮廓。“老七和小五……他们活下来了?”
“老七断了条腿,却咬着牙带着剩下的弟兄重建了镖局。”南川的目光落在演武场角落的石碾上,那上面有一道深沟,是当年陆长风练枪时,枪尖反复戳击留下的痕迹,边缘已被风沙磨得光滑,却依旧能看出当年的力道,“他说,只要这石碾上的枪痕还在,威远镖局的魂就还在。”
陆长风的枪尖在地面划出道浅痕,沙粒顺着枪尖滚落,像是无声的叹息。“那憨子……当年我总骂他练枪不用心,出镖时却总把最险的位置留给自己。”他忽然抬枪,使出一招“灵蛇出洞”,枪尖直指檐角的铁马,“还有小五,他性子最躁,我总说他得磨十年,才能懂‘稳’字怎么写。”
“小五后来成了镖局最稳的镖头。”令秋将魂灯往石碾旁挪了挪,暖黄的光晕在沙地上晕开,映出些微虚影——一个穿青布短打的后生正跪在石碾前,用布蘸着清水擦拭那道深沟,旁边摆着一壶酒,酒液沿着沟痕缓缓渗下,像是在喂饱这沉默了百年的石头,“他走的第一趟镖,特意绕路经黑风口,说要替您看看,那片戈壁的芨芨草,有没有漫过当年的血迹。”
陆长风的枪势顿在半空,魂体周围的风沙忽然慢了下来。他望着虚影里的戈壁,那里果然长满了丛丛芨芨草,在风中摇曳如绿色的火焰。“黑风口的石头是红的,”他声音轻了些,带着不易察觉的柔意,“那是被我们镖师的血浸的……哪能长草。”
“现在能了。”南川从袖中取出一枚虎头镖,镖身的锈迹里还嵌着些暗红的颗粒,“这是去年修路工人在黑风口捡到的,镖尾刻着的‘陆’字还清晰。他们在那里立了块碑,碑上写着‘护镖人魂归处’,每到清明,都有人去献酒。”
陆长风接过镖,指尖的魂体穿过锈迹,触到那熟悉的刻字时,忽然笑了。笑声里没有半分戾气,只有释然的坦荡,震得檐角的铁马都跟着轻响起来。“我当年总说,镖在人在,人亡镖不能亡。”他将镖轻轻放在石碾的沟痕里,“如今看来,这话没说错。”
令秋将魂灯举高些,暖黄的光晕如薄纱般漫过他的魂体:“跟我们走吧。地府在枉死城设了‘忠魂营’,正缺位懂枪术的教头。您去了,既能传艺于战死的英魂,也能时时望见阳间的镖路——那些后生说,要让‘威远’的旗,永远飘在他们走过的路上。”
陆长风最后望了眼那半面镖旗,残阳透过旗洞照在他身上,竟为这魂体镀上了一层金边。他对着演武场深深一揖,仿佛在向当年的弟兄们告别,随后,魂体渐渐被魂灯的光晕裹住。
“告诉老七的后人,”他的声音在光晕里渐渐远去,却依旧带着枪般的挺拔,“练枪先练心,心若如镖,何惧风霜。”
魂灯被收入怀中时,令秋听见石碾的沟痕里,忽然传出一声轻微的“咔哒”声——那枚虎头镖竟自己滚入了最深的凹处,像是终于找到了归宿。他看向南川,见这位鬼王正望着檐角的铁马,玄色衣袍在晚风里轻轻起伏,衣摆的幽冥纹与残阳的余晖交织,生出几分罕见的暖意。
“王,这镖师的魂魄,倒是难得的刚直。”
“道光二十五年冬,我在黑风口收过七名镖师的魂。”南川转身离开,铁马的碰撞声在身后渐渐远了,“他们都说,总镖头的枪,能劈开黄泉路的雾。”
暮色四合时,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悠长而嘹亮,像是在应和着百年前的镖铃。令秋望着怀中的魂灯,忽然明白,有些魂魄从不必借重阴司的拘引,他们自身的风骨,便是最硬的碑;有些信念也从不会被时光磨平,就像这石碾上的枪痕,这残旗上的风音,永远都在诉说着“护”与“守”的分量。
十二、药庐的青囊
惊蛰的雨打湿了山坳里的药庐,茅屋顶的茅草吸饱了水汽,散发出淡淡的草木香。令秋踏着泥泞走近时,看见竹篱笆上爬满了何首乌的藤蔓,叶片上的雨珠坠落在青石板上,发出泠泠的脆响,像是谁在轻轻拨动琴弦。庐内的药碾还在,碾槽里残留着些干枯的药渣,凑近了闻,还能辨出当归与川芎的气息,混着陈年的书香,让人恍惚间以为主人只是暂离。
“王,”令秋用帕子擦去往生簿上的雨珠,纸页边缘有些卷曲,“苏杏坞,字芷兰,女,二十四岁,清同治十年春殁于瘟疫。在此山坳行医五年,救治过周边三县的百姓,瘟疫暴发时,为寻一味救命药材,失足坠崖。魂魄被她随身携带的青囊缚着,每逢雨夜,就会在药庐前晾晒药材,药香能飘到山下的村落里。”
南川立在竹篱笆外的老松树下,玄色衣袍上落了些雨丝,却半点未湿。他望着药庐内的虚影——穿月白襦裙的女子正坐在竹榻前,将晒干的药材分门别类地装入药罐,动作轻柔,眉宇间带着淡淡的书卷气,虽已是魂魄之身,却自带一股安定人心的气场。她腰间的青囊鼓鼓囊囊的,隐约能看见里面露出的药铲与药方。
“是哪位乡亲不舒服?”虚影转过身,声音清润如泉水,目光落在篱笆外的南川与令秋身上,带着几分关切,却无半分惧意,“我这就去煎药,只是今日的柴胡还没晒透,怕是要多等片刻。”
“苏姑娘,”令秋将魂灯往篱笆内送了送,暖黄的光晕在雨幕中撑开一小片安宁,“您已在此守了一百五十六年。同治十年那场瘟疫,您寻到的那味药材,救了山下三百多口人。他们在您坠崖的地方建了座‘芷兰亭’,每年清明,都有人上山来,为您捎带些新采的药材。”
苏杏坞装药材的手顿在半空,月白的袖口扫过竹榻,带落了几片晒干的金银花。她望着窗外的雨幕,声音轻得像雨丝:“李婶的小孙子……他烧退了吗?还有张大爷的喘疾,那味川贝得用蜂蜜拌了蒸,才不会苦……”
“李婶的孙子后来成了县里的大夫,”南川的目光落在药庐角落的药锄上,锄刃上还沾着些泥土,像是刚从山里回来,“他说,小时候喝您煎的药,总觉得里面有甜味,后来才知道,您每次都会偷偷在药里加颗蜜枣。”
苏杏坞的眼眶忽然红了,却倔强地没让眼泪落下。她拿起竹榻上的药方,上面的字迹娟秀,却因年代久远而有些模糊:“那孩子怕苦,每次喝药都要哭闹半天,我便在灶膛里给他烤颗蜜枣,告诉他喝完药就能吃。”
“张大爷活到了九十岁,临终前还在说,是苏姑娘的药,让他多看了五十年的山桃花。”令秋将魂灯往药庐内挪了挪,光晕里浮出些微虚影——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正坐在“芷兰亭”里,手里拿着一束山桃花,轻轻放在亭中的石桌上,“他说,每年山桃花开,就像看见您背着药篓从山上下来,笑着问他身子好不好。”
苏杏坞望着那些虚影,忽然笑了,眼角的泪却顺着脸颊滑落,滴在竹榻上的药材里,化作点点荧光。“山桃花好看,却不能入药。”她轻声说着,像是在对自己低语,“我总说,等瘟疫过了,就教村里的姑娘们辨识草药,却再也没机会了……”
“村里的姑娘们都学会了。”南川从袖中取出一本泛黄的药书,封面上写着“芷兰药录”四个字,字迹与苏杏坞的药方如出一辙,“这是您当年的手稿,被李婶的孙子珍藏着,后来刻成了书,教出了不少懂草药的姑娘。她们说,要替您,把这山坳里的药香,传到更远的地方去。”
苏杏坞接过药书,指尖的魂体穿过纸页,触到那些熟悉的字迹时,忽然觉得眼眶发热。她轻轻摩挲着书封上的“芷兰”二字,像是在触碰一个久违的梦。“我当年总说,学医是为了救人,”她声音里带着释然的温柔,“现在看来,救人的法子,比我活得更久。”
令秋将魂灯举到篱笆边,暖黄的光晕如薄纱般漫过苏杏坞的魂体:“跟我们走吧。地府在忘川河畔设了座‘回春堂’,缺个懂草药的先生。您去了,既能为迷途的魂魄调理魂体,也能时时望见山下的村落——那些您救过的人,他们的后代,正在用您教的法子,守护着这片土地上的人。”
苏杏坞最后望了眼窗外的山坳——雨不知何时停了,天边露出一道淡淡的彩虹,映着满山的青翠,格外好看。她将那本《芷兰药录》轻轻放在竹榻上,随后,魂体渐渐被魂灯的光晕裹住。
“告诉那些姑娘们,”她的声音在光晕里渐渐远去,却依旧清润如泉水,“辨识草药,要先懂草木的心,它们肯牺牲自己,是为了救人,可不能辜负了这份心意。”
魂灯被收入怀中时,令秋听见药庐内的药碾忽然发出轻微的转动声,像是有人在里面,最后碾好了一剂安神的药。他看向南川,见这位鬼王正望着那座“芷兰亭”的方向,玄色衣袍在雨后的微风里轻轻起伏,衣摆的幽冥纹与天边的彩虹交织,生出几分罕见的柔和。
“王,这姑娘的魂魄,倒是难得的温润。”
“同治十年春,我在山下的村落收过不少瘟疫死者的魂,”南川转身离开,竹篱笆的藤蔓在身后轻轻晃动,“他们都说,闻到苏姑娘的药香,走黄泉路时,就不那么怕了。”
山下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清脆而明亮,像是在应和着山间的药香。令秋望着怀中的魂灯,忽然明白,有些善意从不必惊天动地,一碗带着蜜枣的药,一束放在亭中的花,就足以在时光里留下温暖的印记;有些守护也从不会被遗忘,就像这药庐里的药香,这山坳里的草木,永远都在诉说着“救”与“爱”的分量。
十三、笔冢伴残墨
谷雨的雨丝如愁绪,缠绕着城郊的旧书斋。令秋推开那扇虚掩的木门时,闻到的不仅是陈年的墨香,还有淡淡的樟木味,混着窗外芭蕉叶的清新气息,让人恍惚间以为闯入了某位文人的梦境。书斋内的紫檀木书案上,摆着一方端砚,砚池里的残墨早已干涸,却依旧能看出当年的浓淡,旁边堆着些泛黄的诗卷,风吹过,纸页轻轻翻动,像是在低声吟诵着未完的诗句。
“王,”令秋用指尖捻去诗卷上的灰尘,纸页边缘有些脆化,“沈清砚,字墨卿,男,二十八岁,民国十年夏殁于肺病。在此书斋著书五载,留下诗集《听雨轩稿》,却因生不逢时,无人赏识,郁郁而终。魂魄被他常用的那支紫毫笔缚着,每逢雨夜,就会在书案前写诗,墨迹虽不能落在纸上,却能在空气中留下淡淡的墨香,宛如无形的诗行。”
南川立在书斋的窗前,玄色衣袍被雨丝打湿了些许,却依旧挺拔。他望着书案前的虚影——穿青布长衫的男子正伏案疾书,眉宇间带着淡淡的愁绪,却难掩对文字的痴迷,手中的紫毫笔在虚空中舞动,虽无墨迹,却能让人感受到笔尖的顿挫转折,仿佛那些诗句已在他心中流淌了千遍万遍。
“是哪位书友,冒雨来访?”虚影抬起头,目光穿过雨幕落在南川与令秋身上,带着几分文人的清高,却无半分惧意,“我这书斋简陋,只有粗茶相待,只是不知,阁下是否懂‘一字千金’的滋味。”
“沈先生,”令秋将魂灯往书案前送了送,暖黄的光晕在雨幕中撑开一小片温暖,“您已在此守了九十二年。您的《听雨轩稿》,在三十年前被一位学者发现,重新校订出版,现在已是文坛公认的佳作,不少大学的中文系,都把您的诗选为教材呢。”
沈清砚握笔的手顿在半空,青布的袖口扫过诗卷,带落了几片干枯的花瓣——那是他当年夹在诗卷里的书签,如今早已失去了颜色。他望着窗外的芭蕉叶,声音轻得像雨打芭蕉:“我的诗……也有人读吗?他们会不会觉得,这些句子太消沉了?”
“您的诗里有风骨。”南川的目光落在书案角落的笔筒上,里面插着几支不同型号的毛笔,笔杆上的字迹虽已模糊,却依旧能看出当年的用心,“有位评论家说,读您的诗,就像在雨夜里走一条僻静的路,虽孤独,却总能看到前方的微光。”
沈清砚的眼眶忽然红了,却很快被他掩饰过去。他拿起案上的诗卷,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那年我在江南遇雨,躲在一座破庙里,写下‘雨打芭蕉叶带愁,书生落魄亦风流’,总觉得这句子太狂,却没想到,真的有人能懂。”
“不仅有人懂,还有人爱。”令秋将魂灯往诗卷旁挪了挪,暖黄的光晕里浮出些微虚影——一群穿着校服的学生正坐在教室里,齐声朗读着沈清砚的诗,窗外的雨丝飘进教室,落在翻开的书页上,像是在为这跨越时空的相遇,落下温柔的注脚,“他们说,您的诗里有他们的影子,那些关于理想、关于孤独、关于坚持的句子,总能给他们力量。”
沈清砚望着那些虚影,忽然笑了,眼角的泪却顺着
鬼王令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洪荒后世录
- 讲造物主的故事!
- 4.4万字11个月前
- 系统:剑山镇守五十年,出山成圣
- (已签约。爽文+系统+慢热+收徒养成+不圣母)破心魔,入圣境,一剑纵横三万里,豪取世间剑仙名。一剑开天,诸魔退避,我为人,当护人族天下。
- 2.2万字11个月前
- 狐朝
- 上层建筑,并非平民
- 2.3万字11个月前
- 孙悟空大战六耳猕猴
- 一路西天取经最终被如来封为斗战胜佛,可是谁知道那个孙悟空只是六耳猕猴假扮的,目的就是为了代替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好修成正果成为斗战胜佛,而......
- 5.1万字6个月前
- 葬神纪
- “葬神镜现世,天下大乱啊。”茶馆中传来老者的叹息,“神墓殿发下海捕令,说苏寒是巫族的走狗,要取他项上人头。”
- 2.5万字5个月前
- 吻烬新生
- 一场意外让他穿越成废人,系统降临让他有活下去的勇气,从此一路开挂,爱上胡列娜,装傻待在她身边…
- 15.2万字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