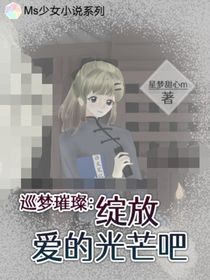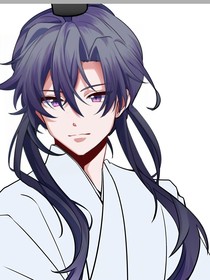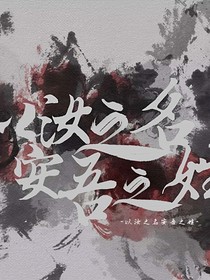江南案·深宅影
京城苏国公府的西跨院,暑气正盛。苏青桐坐在廊下的竹椅上,手里拈着一片刚摘下的夏竹叶,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叶面上的纹路。院角的石榴树结满了饱满的果实,蝉鸣一声声撞在朱红廊柱上,倒显得这午后愈发静了。
“小姐,这夏竹茶凉透了,换一杯吧。”侍女夏末端着新沏的茶过来,见她盯着竹篱外的石板路出神,忍不住轻声道,“您都在这儿坐了一个时辰了,太阳都移到西头了。”
苏青桐回过神,接过茶盏,茶盖碰到杯沿发出清脆的声响。她望着杯中浮起的茶叶,忽然问:“夏末,你说江南的夏天,是不是比京城凉快些?”
夏末愣了愣:“听去过江南的老仆说,那边水汽重,是比京城舒爽些。小姐怎么突然问这个?”
苏青桐没说话,只是将那片夏竹叶放进茶盏里。叶片打着旋儿沉下去,像极了去年中秋,李浚捧着圣旨从宫门前走过时的样子——他穿着石青色的官服,腰间玉带束得笔直,步履沉稳,连拂过他帽檐的风,都带着几分肃杀的利落。
那日她随母亲去慈安寺进香,恰好撞见他领旨查办漕运贪腐案,临行前与同僚说话,眉眼间的锐利,比寺门前的石狮子还要醒神。她躲在香案后,看了足足半盏茶的功夫,直到母亲催着走,才发现手里的念珠都攥出了汗。
“前几日听父亲说,李大人在江南查盐案,还救了位陈姑娘?”她忽然开口,声音轻得像被风吹散的茶烟。
夏末想了想:“是有这事,听说那位陈姑娘还受了伤。国公爷说李大人办案向来拼命,这回怕是又没少熬夜。”
苏青桐端着茶盏的手微微收紧,指尖触到杯壁的凉意。她自幼在国公府长大,见惯了勋贵子弟的骄纵或温吞,像李浚这样凭着一身骨气压住满朝非议、硬生生啃下一个个硬骨头的,独一份。
可这样的人,心里装着的是朝堂,是案子,是那些需要他护着的人,哪里会记得去年中秋,那个在慈安寺香案后,偷偷看了他半晌的苏家大小姐。
“去把那盒新收的碧螺春包好。”她忽然起身,理了理月白色的襦裙,“父亲说李大人的母亲明日过府赴宴,送过去当伴手礼。”
夏末眼睛一亮:“小姐是想……”
“只是尽邻里之谊。”苏青桐打断她,指尖拂过廊柱上斑驳的漆痕,语气里藏着一丝自己都未察觉的期待,“李大人在江南辛苦,做母亲的总惦记着。这点茶叶,也算替他尽点孝心。”
她转身回房,打开妆奁,从最底层翻出个素面的锦盒,里面放着枚竹制的书签,是她前几日照着江南竹影刻的。竹纹细密,边角被摩挲得光滑,却始终没勇气送出去。
其实她也知道,李大人的母亲未必会特意提起送茶的是谁,就算提起了,他此刻怕是正忙着查案,未必会放在心上。
可心里总有个小小的念头在冒——万一呢?万一他能看见那书签,能想起京城苏府里,有个姑娘,在每个蝉鸣的午后,都对着江南的方向,数着日子等他回来。
院外的蝉鸣还在继续,苏青桐将锦盒递给夏末,望着天边渐渐沉下去的日头,轻轻吁了口气。夏末的风正穿过竹篱,带着隐约的凉意,像极了江南的水汽,温柔地漫过心头。
客栈的窗棂透进半盏晨光,落在陈子衿搭在被沿的手背上。她睫毛轻颤,缓缓睁开眼时,喉咙的灼痛感已轻了许多,只是浑身仍有些发沉。
“姑娘醒了!”守在床边的芸香惊喜地起身,连忙要去叫大夫,却被陈子衿拉住。
“不必了,我好多了。”她声音还有些哑,目光扫过案上堆叠的账册抄本,“李大人呢?”
“李大人天不亮就去盐道衙门了,临走前让我们一定盯着您好好休息。”芸香端来温水,“他说等您醒了,先喝些粥垫垫。”
陈子衿接过水杯,指尖触到杯壁的温热,心里却想着盐仓的火——那火来得蹊跷,张启山明知他们在查账,偏在此时毁了盐仓,分明是有恃无恐。她掀开被子想下床,却被芸香按住:“姑娘您伤口还没好,李大人说了……”
“账册要紧。”陈子衿打断她,扶着床头慢慢坐起身,“烧了的盐仓是明线,他们想让我们盯着灰烬查,暗地里指不定在转移更重要的东西。”
她接过芸香递来的外衣,动作因牵扯到肩头的灼伤而有些迟缓,却执意要穿:“去把茗香找来,我记得她父亲曾在江南做过漕运,或许知道张记商号的底细。”
芸香拗不过她,只好叫来茗香。茗香听闻姑娘要查张记商号,立刻道:“姑娘没记错,我小时候听父亲说过,张记商号看着是做绸缎生意,实则一直帮盐商走漕运私盐,他们的船队都有特制的夹层船板,能藏不少货。”
“夹层船板……”陈子衿指尖在账册上划过“镇江码头”四个字,“苏公子说张启山把银子转移到了码头,说不定不只是运银子,还有私盐。”
正说着,李浚推门进来,见她已起身坐在桌边,眉头立刻蹙起:“怎么起来了?”
“躺不住。”陈子衿抬头看他,眼底带着几分急切,“张启山的船队很可能藏着私盐,我们得去镇江码头看看。”
李浚走近,见她脖颈的灼伤仍红肿着,伸手想探她额头的温度,却在半空中停住,转而拿起案上的薄毯披在她肩上:“码头那边我已让人盯着,张启山的船队没敢动。你身子没好利索,今日不许去。”
“可……”
“没有可是。”李浚语气不容置疑,却拿起一本账册放在她面前,“这是苏云佑从镇江带回的望月楼账册,里面记着张启山每年中秋都在那里宴请一位‘京城贵客’,你看看有没有眼熟的名字。”
陈子衿接过账册,指尖迅速划过泛黄的纸页。当看到“杨”字时,她猛地顿住——那日期恰好与去年杨夫人兄长南下的时间对上。
“是杨家人。”她抬头看向李浚,“张启山每年都在给杨家送私盐的分红。”
李浚点头:“我已让人将账册快马送回京,交由刑部核对。只要坐实杨家与私盐案的关联,杨夫人就再难翻身。”
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两人之间的账册上,将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照得清晰。陈子衿忽然想起昏迷前的火光,想起他抱着自己时急促的心跳,脸颊微微发烫,低声道:“那日……多谢你。”
李浚握着茶杯的手紧了紧,声音比往常低沉些:“你是查案的关键,不能出事。”
这话虽说得公事公办,陈子衿却从他眼底看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柔和。她低下头,指尖在“望月楼”三个字上轻轻点了点:“等我好些了,我们去一趟望月楼吧,说不定还能找到别的线索。”
“好。”李浚应下,看着她专注看账册的侧脸,忽然道,“粥在厨房温着,我去端来。”
他转身离开时,脚步比来时慢了些。陈子衿望着他的背影,又低头看了看肩上的薄毯,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窗外的阳光正好,江南的风带着水汽吹进来,带着几分暖意,像极了此刻她心里的滋味。
京城李府的正厅里,李老夫人正临窗翻着一本佛经。案上的青瓷瓶插着几枝新开的茉莉,香气清幽,混着淡淡的檀香,将初秋的燥意压下去不少。
“老夫人,苏国公府送了盒碧螺春过来,说是给您过府赴宴的伴手礼。”管家捧着锦盒进来,见她目光落在窗外的石榴树上,轻声补充道,“听说是苏家大小姐亲手挑的。”
李老夫人抬眼,接过锦盒打开,指尖拂过茶叶罐上精致的缠枝纹,忽然笑了:“这孩子,倒还记得我喜欢喝江南的茶。”她取出一小撮茶叶,凑近闻了闻,“明前的碧螺春,是有心了。”
正说着,门外传来脚步声,李浚的堂弟李砚抱着个食盒进来:“伯母,厨房炖了您爱吃的银耳羹,我给您端来一碗。”
李老夫人接过白瓷碗,舀了一勺慢慢喝着,忽然问:“你堂兄在江南,有信回来吗?”
李砚挠挠头:“前几日来了封信,说盐案查得差不多了,就是……提了句陈姑娘为了抢账册受了伤,他正盯着医治呢。”
“陈姑娘?”李老夫人眉梢微动,“就是那位跟着他查案的陈御史家的小姐?”
“正是。”李砚点头,“听说是位厉害姑娘,账目算得比账房先生还精,就是性子太急,火里来火里去的,倒让堂兄捏了把汗。”
李老夫人放下汤勺,拿起那盒碧螺春摩挲着:“能让你堂兄记挂的,定不是寻常女子。”她想起去年李浚回京述职,夜里总对着一堆盐案卷宗出神,提过一句“陈家有女,心思缜密”,当时只当是夸赞同僚,如今想来,倒是自己疏忽了。
“明日苏府的宴,你替我去一趟。”她忽然道,“把这茶叶还回去,就说我心领了。另外,让人给你堂兄捎些伤药过去,就说是……给陈姑娘的。”
李砚一愣:“伯母不亲自去吗?苏国公夫人前日还特意让人来说,盼着您赏光呢。”
“不去了。”李老夫人望向窗外,石榴树梢的阳光正暖,“让年轻人自己折腾去吧。咱们这些老人家,守着这院子里的茉莉,等着他们把案子查清楚,比什么都强。”
她重新拿起佛经,目光却落在书页间夹着的一张字条上,那是李浚幼时写的“愿天下无冤”,字迹稚嫩,却透着股执拗。这么多年过去,他这性子倒是一点没变,只是不知江南那趟浑水,能不能让他看清自己的心。
秋风穿过窗棂,吹得茉莉花瓣轻轻颤动,香气漫了满室。李老夫人合上书,轻轻叹了口气——这孩子,查案时精明得很,偏偏在儿女情长上,钝得像块顽石。
锦阙争芳录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新还珠格格之楚国皇后
- 玉龙跟小燕子从小被定了娃娃亲,两个人小时候经常一起玩,在某一天楚国遭遇灭国,此时小燕子很想司马玉龙,于是就一个人孤身去了楚国找司马玉龙,一想......
- 4.6万字9个月前
- 巡梦璀璨:绽放爱的光芒吧
- 最后一篇Ms系列作品【未来×古代化×时空穿越宫斗,温柔稳重的方雪雅】她们来到3000年后的世界里面,发现她们自己身上的一切都发生变化,这是X......
- 2.5万字9个月前
- 锦衣玉令
- 4.9万字7个月前
- 三两风月
- 六十年前,一场兄弟阋墙的人间惨剧,改变了南北格局。摄政王晏潇领兵北伐一路打到上京临湟府,却因被背叛身殒河北居庸关外。不甘的孤独魂灵飘荡在人间......
- 2.5万字6个月前
- 以汝之名安吾之姓
- 元和大陆被两大国都占有,分别是元龙国与岄鹤国。两国常年交战民不聊生,两国国君也心中权衡。后两国商议决定和亲。至于和亲的当事人愿不愿意,那就不......
- 8.1万字6个月前
- 千堆秋
- 沐之许、柳云澈,一对人人艳羡的青梅竹马,长大后互相喜欢,20岁的柳云澈成为了将军,后来出兵打仗,沐之许为他行,柳云澈答应,回来后就娶她,可他......
- 0.2万字22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