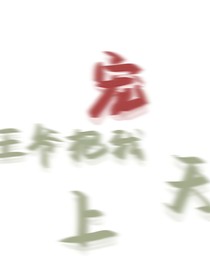第二章:锋芒初露,暗流涌动
选秀前夜,太后的宫殿灯火通明。沈昭华坐在紫檀木椅上,听着太后絮絮叨叨。
“昭华,谢临砚你得留意,谢家在江南声望高,拉拢了他们,南方就稳了。”太后呷了口茶,语气带着不容置疑,“还有萧策,镇国将军手握兵权,若能成一家人,北境也能安心。”
沈昭华把玩着腕间的玉镯:“母后,儿臣选夫郎,总要看顺眼吧?”
“顺眼?”太后放下茶杯,眼神锐利,“你是大靖女帝,不是寻常女子!顺眼能让边境安稳吗?能让世家臣服吗?”
沈昭华沉默。她知道太后说的是实话,只是心里那点别扭总也过不去。
“明日选秀,你好好看看,”太后放缓了语气,“选个家世、样貌都过得去的,既全了体面,又稳了朝堂,不好吗?”
“儿臣知道了。”她起身行礼,退出了宫殿。夜风吹起她的衣袍,她望着远处选秀公子们住的驿馆方向,冷笑一声——体面?这皇城最不缺的,就是体面的假象。
次日,金銮殿庄严肃穆。沈昭华端坐御座,太后坐在侧席,两旁女官分列,气氛庄重。
“传第一位,江南谢临砚。”
随着唱名,谢临砚缓步而入。他走到殿中,躬身行礼,动作标准,声音清朗:“草民谢临砚,参见陛下,陛下万岁。”
“抬起头来。”沈昭华道。
谢临砚抬头,目光温和,恰好与沈昭华对视,却又适时低下头,带着恰到好处的羞怯——这是世家公子们练就的“得体”。
“听说你才名远扬?”沈昭华问。
“不敢称才名,只是略通诗文。”他呈上一卷诗稿,“这是草民为陛下作的《宸宫赋》,愿博陛下一笑。”
内侍将诗稿呈上,沈昭华扫了两眼,辞藻华丽,对仗工整,却没什么新意。太后在一旁笑道:“谢公子好文采,配得上陛下。”
谢临砚谦逊行礼,沈昭华却只是淡淡道:“嗯,退下吧。”
他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诧异,却依旧恭敬地退到殿侧。沈昭华望着他的背影,指尖在御座扶手上轻轻敲击——太完美的人,往往藏着最深的心思。
谢临砚退下后,殿内安静了片刻。
“传第二位,镇国将军之弟,萧策。”
话音刚落,一个身影大步流星地走进来,与谢临砚的从容不同,他步子迈得又大又快,玄色劲装勾勒出挺拔的身形,腰间还挂着一柄短刀(按规矩本应卸下,他却像是忘了)。
“草民萧策,参见陛下。”他行礼也带着股武将的硬朗,头刚低到一半就抬了起来,目光直视沈昭华,毫不避讳。
殿内女官们倒吸一口凉气——哪有公子敢这么看女帝的?
沈昭华却不恼,反而饶有兴致地打量他:“萧公子似乎不太习惯这些规矩?”
“回陛下,”萧策声音洪亮,“草民是个粗人,不懂诗文,只会些拳脚功夫。若陛下要选能吟诗作对的,草民不行;但若是要选能骑马射箭、甚至上战场的,草民不输任何人!”
这话一出,连太后都皱起了眉。选秀选的是夫郎,哪有说要上战场的?
沈昭华却笑了,笑意漫到眼底:“哦?那萧公子倒是说说,你能替朕做什么?”
“替陛下守城门,护宫闱,只要是力气活,草民都行!”萧策梗着脖子,“但若是让草民天天描眉画眼、争风吃醋,恕难从命!”
殿内鸦雀无声。沈昭华看着他桀骜的样子,忽然觉得,这比谢临砚的“完美”有趣多了。
“勇气可嘉,”她缓缓道,“只是这后宫,不需要会打仗的。”
萧策脸一红,像是想说什么,最终却只是哼了一声,退到殿侧,故意离谢临砚远远的。两人一个温润站着,一个梗着脖子,形成鲜明对比。
“传第三位……”
内侍正要唱名,沈昭华抬手打断:“等等。”她看向殿侧的苏砚辞——刚才点名时,这寒门学子安安静静站在角落,几乎没被注意到。
“你叫苏砚辞?”
苏砚辞一愣,连忙出列行礼:“是,草民苏砚辞。”
“听说你是读书人,”沈昭华问,“刚才谢公子作诗,萧公子论武,你有什么想说的?”
苏砚辞抬起头,他肤色偏白,因紧张而泛红,却眼神清澈:“回陛下,草民以为,治国不在诗赋,也不在拳脚,而在民心。”他顿了顿,鼓起勇气,“近年北方大旱,百姓流离,若陛下能减免赋税、开仓放粮,比任何诗赋、武艺都有用。”
这话直白得近乎冒犯,却让沈昭华眼中闪过一丝赞赏。她刚想再问,殿外忽然传来内侍的声音:“启禀陛下,江南苏家公子温玉,因途中遇雨耽搁,刚到宫门,求见陛下。”
温玉?沈昭华挑眉。名册上似乎有这个名字,没落文人之后,没什么背景。
“让他进来。”她道。
朱红大门再次打开,一个身着月白锦袍的身影,终于踏入了这金碧辉煌的殿宇。
昭华录:凤榻犹寒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重生之锦绣王妃:独宠君心
- 5.0万字8个月前
- 重生嫡女开外挂
- 前世,陆婉晴错信小人,沦为刀俎上任人欺凌,任人践踏的侯府小姐,含恨而终,大梦初醒,她回到了出事前的一夜,任何人也将休想再从她手中夺走一分一毫......
- 8.1万字8个月前
- 与君:前世
- 蝶杀,一个另人闻风丧胆的阻织。齐国蝶杀少主代替武南候嫡女顾言瑾,收到任务暗杀功高震主的澜沧王,意外知道了“他”的秘密……
- 3.1万字6个月前
- 倾世疯魔
- 大梁朝的京都,盛世繁华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名字——疯批美人叶倾歌。她出身名门叶府,容貌倾城,才情无双,本应一生荣耀。然而,一场家族......
- 1.0万字4个月前
- 我和闺蜜双穿,搞钱最在行
- 我和闺蜜双穿,搞钱最在行
- 54.3万字4个月前
- 回京后,王爷给我宠上天
- 双生花开,一生一死。女主:谢朝朝男主:萧恒男配:萧逸女配:宋晚
- 0.6万字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