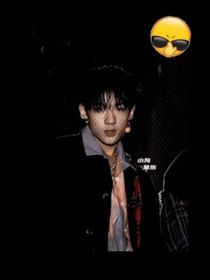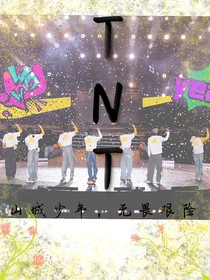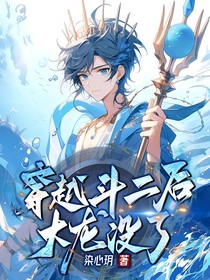托起香云水底看
入京四年,宋铮铮赴宴的次数一只手就能数完。
第一年,帖子寥寥;人们说她是“青州乡下土丫”,嫌她行礼的弧度大,袖口的风还带着山野气。
第二年,知道宋铮铮是礼部尚书之女,烫金请柬忽然雪片般飞进宋府。她不去,便有人说“端架子”;去了,又嫌她“不会端架子”。
一次她进宫赴宴,席上贵女们推杯换盏,笑吟吟地把“新裁绫裙谁先穿”当彩头。
有人故意拿青州口音逗她:“宋姑娘乡下来的,可认得这蜀锦?”
宋铮铮放下筷子,认真回答:“认得,这是成都府去年贡上的‘醉流霞’,一匹值三十两。可青州去年洪水,三十两能买三十石赈米。”
一句话落地,丝竹声都断了。
又一次,英国公夫人办赏花局,席间以“咏落红”为题赋诗。
轮到宋铮铮,她写的是:
“……愿化春泥更护花,莫教轻薄逐天涯。”
贵女们掩口笑她憨——京中最时兴的句子是“落花辞树不粘泥”。
她却把诗稿折好,亲自送到后园,埋在刚移栽的芍药根下。
众目睽睽,她蹲着身,土沾了指尖也浑不在意。
久而久之,城里流传一句闲话:
“宋家姑娘有三痴——不食剩、不惜绫、不笑贫。”
她参加静安县主的螃蟹宴,丫鬟端上冷蟹,县主笑说“将就些”。
宋铮铮偏要厨房重蒸,县主面上挂不住;她却把新蒸好的第一只蟹,先递给了站在角落里伺候的哑婆子。
满座愕然,她只低声道:“蟹寒,婆婆牙口不好,热的才不伤胃。”
有人劝她圆融些,她眨眨眼:“乡下来的,学不会弯弯绕。”
说罢,仍旧把席上没人要的果子包起,托小厮送到门外乞儿手里。
于是贵女们背后摇头:“傻气。”
可下一次设宴,又忍不住给她下帖——
她们想看看,这位“固执的傻姑娘”还能做出什么让她们下不来台、却又忍不住暗暗佩服的事。
帖子送到宋府那日,恰逢秋雨初歇,菊香浮在青石板的湿意里。
宋铮铮倚窗,一左一右两张洒金帖:
左边清远伯府——墨色浅淡,只印着一枝折枝黄菊,谦逊得像怕惊动人;
右边定国公府——朱红底、泥金纹,落款处赫然盖着当朝首辅的小印,锋芒毕露。
京中惯例:谁家权势盛,车马便涌向谁家。
不过一夜,风向已定——“大都去定国公府”。
连宋夫人也劝:“你父亲如今正需借梯上楼,定国公府那趟水,再浑也得蹚。”
宋铮铮却拿指尖轻轻点了点清远伯府那枝“怯生生”的菊。
“我就去这儿。”
“人少,不挤。”
“花是真花,不必看人脸色。”
“赏菊便赏菊,何苦把一朵花也分出个三六九等?”
她话说得轻,却带着刀裁般的利落。
午后,她换了一身月白小褂,袖口别着霍长缨送的那截袖箭,只带一个小丫鬟,登车往清远伯府。
清远伯府门前果然冷清,只两盏素灯、一位佝偻老苍头。
门楣旧漆剥落,却掩不住满院黄菊泼天似的香。
没有丝竹聒耳,没有高谈阔论。
风一过,花影摇摇,像替主人道一句:
——多谢肯来。
宋铮铮俯身嗅花,唇角弯起。
她想,幸好来了。
花不分贵贱,人又何必自划牢笼?
清远伯府的菊圃本静,风过时只听得花瓣摩挲。
宋铮铮立在“玉壶春”品种前,指腹轻抚花心,暗自推敲花瓣的翻折——该用破笔皴,还是清水晕?
忽听环佩乱响,小丫鬟喘着气跑进来:“姑娘,勇毅侯世子与临孜王来了!”
话音未落,两道挺拔影子已越过月洞门。
一人绛紫箭袖,佩玉击节;一人月白锦袍,折扇半掩。
满园女眷霎时如鸟雀惊枝,整鬟的整鬟,理裙的理裙。
偏那两人目不斜视,步履生风,衣摆扫过花畦,枝头的“金络索”被扇柄一碰,簌簌落瓣。
宋铮铮眉心微蹙,侧身让开半步——
她心中只掠过四个字:无礼至极。
旋即又有婆子慌报:“不好了,西池有人落水!”
两位贵公子竟毫不犹豫,径直往内院去。
紫袍那位甚至抬手拨开挡路的菊花,枝茎“喀啦”一声脆响。
宋铮铮低头看那枝被折断的“绿芙蓉”,断面渗出青白汁液,像无声的控诉。
宋铮铮拂去袖口沾上的碎瓣,声音极轻,却像袖箭离弦:
“花无罪,人失礼。”
说罢,她俯身拾起那枝残菊,拢进袖中——
回府后,她要将它画成一幅《折枝图》。
题跋她已想好:
“菊以幽芳自守,奈何横被轻狂。”
尤府后院里西池水浅,却冷得像一弯碎冰。
尤芳吟浑身湿透,青丝黏在苍黄的颊边,像一株被骤雨打蔫的野菊。
她缩在池畔石阶上,衣角滴滴答答落着水,四周女眷远远围着,无一人上前——庶女的身份,在这时节比秋风更凉。
姜家姑娘姜雪宁已半蹲下去,一手扶她肩,一手托她肘,声音稳稳的:“先起来,别坐地上。”
她自己的杏子红褙子也溅了水,晕开一片片深色花。
燕林世子随后而至,解下玄青织金的鹤氅,随手一抖便要往姜雪宁身上披——他只看见她背脊的湿印,却未看清真正落水的是谁。
就在鹤氅将落未落的一瞬,一道月白人影横插进来。
宋铮铮先一步把自己的浅碧绡纱斗篷褪下,兜头裹住尤芳吟。
斗篷内衬是细绒,轻薄却暖,还残着她身上的温度。
“尤三姑娘先穿我的。”
她声音不高,却足够让周围都听见。
随即俯身,一手穿过芳吟膝弯,竟直接把人打横抱起。
尤芳吟轻得像一捆湿透的芦苇,在她怀里微微发抖。
宋铮铮低头,看见小姑娘唇色发白,却仍低声道:“谢谢……宋姐姐。”
“别说话,省点力气。”
宋铮铮侧过脸,朝姜雪宁一点头,“劳烦姜姑娘引路,去最近的暖阁。”
姜雪宁怔了怔,随即应声,转身拨开人群。
燕临世子的鹤氅半悬在空中,终究落在自己臂弯。
他看着宋铮铮抱着人走远,月白袖口沾了水渍,像雪上落梅,步子却稳得不见一丝踉跄。
暖阁里炭火噼啪。
宋铮铮把尤芳吟放在软榻上,吩咐小丫鬟:“去你们三姑娘屋里取干净衣裳,再熬碗姜汤,放半勺红糖。”
转头又拿自己的帕子给她绞发,尤芳吟缩在斗篷里,眼神怯怯,却亮得惊人:“宋姐姐……你不嫌我脏么?”
宋铮铮:宋铮铮笑了笑,指尖轻弹她额头:“人不脏,水脏。回头洗个澡,又是香喷喷的小姑娘。”
门外脚步杂沓,清远伯夫人带着大夫匆匆赶来。
掀起帘子时,只见宋铮铮半蹲在榻前,一手替尤芳吟掖斗篷,一手悄悄把袖箭的暗扣扣好——仿佛方才抱人时,箭身硌到了小姑娘,她怕再惊着她。
那截乌沉的铁器在烛光里一闪,又隐进袖口。
无人看见,只尤芳吟看见了。
她湿漉漉的眼睛弯起来,像两弯小小的月牙。
闺房内,铜炉里沉水香轻缓地浮起。
尤芳吟换过了宋铮铮的斗篷,仍有些瑟缩,湿发披在肩头,像一绺绺打湿的鸦羽。
姜雪宁先开了口。
她自袖中抽出一方小小绣囊,囊口绣着一枝白梅,递到尤芳吟手里:“里头有二十两,是我月例里攒下的。先拿去给你娘修墓,碑上的字若还没刻,便请最好的石匠,别怕花钱。”
尤芳吟捧着绣囊,指尖微颤,刚要开口,宋铮铮已半蹲到她面前。
她没拿荷包,也没拿银票,而是把一只小小的檀木盒塞进尤芳吟掌心。
盒盖轻轻一掀——里头整整齐齐码着十枚小金锞子,并一张折得极薄的纸。
“我的私房,共三十两。”
宋铮铮声音低,却带着乡野里长大的爽利,“金锞子在京里兑银子方便,纸是我方才写的荐信。你拿着它去东四牌楼‘永固石坊’,找一位姓齐的老师傅——他欠我人情,碑座、碑身、刻字,全都会给你用最好的青石,不另收工钱。”
尤芳吟的眼泪啪嗒落在盒沿。
她想说谢,却哽得只能摇头。
宋铮铮抬手,拿袖口帮她擦泪,动作粗枝大叶,却极温柔:
“别哭。碑立好了,记得写信给我,就说——”
她想了想,忽地笑出一颗虎牙,“就说‘宋姐姐的袖箭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以后谁敢动这座坟头土,先问过箭镞答不答应’。”
一句话,把尤芳吟逗得破涕为笑。
姜雪宁也弯了弯唇,眼底闪着柔软的碎光。
窗外秋风卷过菊香,轻纱微动。
三位姑娘的影子落在茜纱窗上,小小一间暖阁,竟比外头万盏灯火更明亮。
午后日头正好,连菊影都淡得几乎看不见。
宋铮铮送完尤芳吟出来,刚转过回廊,就听见前院一阵高声——
燕临立在垂花门下,紫袍映日,玉冠晃眼,声音朗朗得能惊起飞鸟:
“……我娶她!如今便请旨,看谁还敢胡说一句!”
日光把他眉梢那点倨傲照得分明,字字铿锵,仿佛“娶”之一字是柄尚方宝剑,能当场斩断所有流言。
旁边几个看热闹的小姐拿团扇掩唇,低低称赞:
“世子当真风流果敢。”
“姜姑娘好福气呀。”
宋铮铮站在阴凉里,听得分明,忽然觉得好笑,唇角一弯,笑意却凉得像井水里浸过的玉。
——同样一桩事:
男子说来,便成了光风霁月的担当;
若换成女子,只怕先被指“失节”,再被嘲“攀高”。
她抬手遮了遮刺眼的阳光,指间袖箭的冷意顺着腕骨滑上来。
“青天白日,果真两样世情。”
语罢,她转身离开,裙角掠过碎金般的日影,像一把未出鞘的小刀,把光天化日下的双标无声地劈成两半。
暖阳斜照,前院忽然一阵环佩叮当。
“长公主驾到——薛家姑娘到——”
方才还嘈杂的菊圃霎时静了三分。
乐阳长公主沈芷衣一袭红衣,左颊那道浅淡的伤疤在日头下微微泛白。
薛姝伴在她右侧,绛纱长裙逶迤,笑得温婉。
尤家夫人忙迎上前,眼角余光却扫过满园宾客,心里打着小鼓:
清远伯府门庭冷落,难得贵人齐至,总得拿出点新鲜花样。
于是她扬声笑道:
“今日菊花开得极盛,不若各位小姐即兴挥毫,赛一赛‘画菊’如何?优胜者,本夫人以这盆‘赤线金珠’为彩头。”
话音落下,侍婢们已抬出长案、铺好宣纸,墨香混着菊香,顿时盈袖。
姜雪宁被点到名,握着笔却犯了难——
她擅琴擅书,唯独没正经学过画。
抬眼见公主立在阶前,正含笑看她,心里一急,反倒生出个大胆念头。
她搁下笔,转身朝沈芷衣福了福:
“殿下恕雪宁冒昧——可否借您笑靥一用?”
众人尚不及反应,姜雪宁已蘸了胭脂色颜料,指尖轻点。
几笔勾勒,公主左颊那道旧疤上便绽出一朵小小的丹枫菊,瓣薄如羽,色晕若霞。
花瓣尾端有意顺着疤痕的走势微挑,竟像把伤疤化成了花茎,天然一段风骨。
四周先是一静,旋即爆出低低的惊叹。
沈芷衣抬手欲触,指尖停在花瓣边缘,眼尾弯起:“原来本宫脸上也能开出花。”
薛姝目光闪了闪,笑着打圆场:
“雪宁妹妹别出心裁,这朵‘面上菊’倒也当得魁首。”
另一边,宋铮铮对喧哗充耳不闻。
她已择了最僻静一隅,案上只铺一张素白熟宣。
面前是一枝被日头晒得略卷的残菊——外层瓣边已枯,花心犹抱,像不肯低头的倔强。
她提笔先以淡墨扫茎,再换破笔蘸焦茶,枯笔一扫,卷瓣干裂之态跃然纸上;
继而以清水晕开赭石,在残瓣尖上点微红,像余烬里最后一点火星。
最后一笔,她用极细的狼毫在花茎裂口处勾出一道白——
那是折枝后渗出的浆液,也是不肯愈合的伤。
尤夫人抱着“赤线金珠”转过来,本想催她快些,却在看清那幅《残菊图》时倏然噤声。
纸上无风,却似有秋意透骨。
沈芷衣亦缓步而来,目光在画与宋铮铮之间停驻。
半晌,她轻声道:
“本宫今日方知,花可绘于纸上,亦可绘于人心——
而真正的菊魂,原来在残处。”
衔玉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gidle:月圆起落,花开有时
- 一次意外姜婉慈要攻略不同的人她们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呢?让我们来一起期待吧校园蔷薇(更新中)鲜艳玫瑰(未开启)伪装纠纷(未开启)笼中之雀(未开......
- 2.5万字9个月前
- TF三代:腹黑哥哥总想控制我!
- 苏淮安:“哥哥们,这是我男朋友”朱志鑫:“你长大了?!翅膀硬了!敢谈恋爱了?!”苏新皓:“妹妹你不乖了哦!”邓佳鑫:“我们该怎么惩罚你呢?!......
- 2.1万字9个月前
- TNT:山城少年,不畏艰险
-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未来迎接,这是无尽的战争无数的怪物在打破宁静,我们做的就是消灭怪物
- 0.7万字6个月前
- 喜羊羊之遗忘之境
- 一切的真相应该何去何从?那被遗忘的境界又究竟是什么地方?『喜羊羊同人文无限流副本闯关雷者慎入』【彼岸花开,幽魂暗藏,灼尽红颜,魅影纷扰,生死......
- 1.2万字4个月前
- 穿越斗二后大龙没了
- [已签约,禁抄袭,禁转载]【斗二同人+变嫁+男主雨浩+系统+无刀无虐+甜文+女主背景和实力都无敌】林辰因一场事故意外穿越到了斗二的世界!她发......
- 10.2万字4个月前
- 存在相遇
- 与其说你我之间终会遇见,不如说你我之间本就存在相遇阳光开朗、大大咧咧、有起床气、不知暗示、看美女就直眼x高傲孤冷、只宠老婆、怕疼、怕虫(作者......
- 13.3万字1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