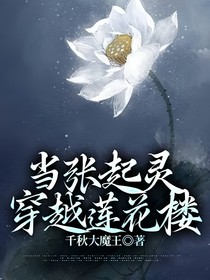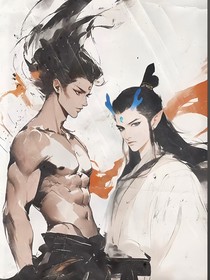忽闻檐角莺声碎
尤月一脚踏进厢房,便把自己扔到榻上,珠钗上的金翅颤得哗啦响。
“我挑了整整三日的金凤钗,连翅羽的弧度都让工匠改了又改,公主一句话就赏了姜雪宁!凭什么?燕临喜欢她,公主也喜欢她,天底下的好都叫她一个人占尽了?”
宋铮铮坐在案前,狼毫蘸着淡墨,在纸上点出一只蜷卧的小猫。她头也没抬,声音却软:“你瞧这只猫,毛色只是普通的梨花,可它眼睛圆,鼻尖粉,我就喜欢得紧。若拿它去比御苑里那只雪狮子,岂不是自寻烦恼?”
她笔锋一转,又勾出第二只猫:尾巴长,耳朵尖,正攀着窗棂偷看月亮。“每只猫都有自己的好。有的擅捕鼠,有的会撒娇,有的只负责好看。若非要排个高低,反倒把‘喜欢’变成了‘计较’。”
尤月侧过身,脸闷在绣枕里,声音闷闷地传出来:“你就会拿猫哄我。”
宋铮铮放下笔,走到榻边,把尤月鬓边乱了的碎发别到耳后:“可我说的是真话。我喜欢你呀,尤月——喜欢你挑钗子时那股认真劲儿,喜欢你生气时眼睛亮得像烧了两簇小火苗。若拿你去比旁人,我才是真的亏了。”
尤月“噗嗤”笑出声,却又立刻绷住,撇嘴道:“你现在说得云淡风轻,不过是因为没遇见真正在意的人。等哪天你碰上了,看你还比不比!”
宋铮铮愣了愣,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袖口,里面有一截薄薄的、折叠得极细的宣纸——那是她画废的第十一张“谢危”。
她没舍得丢。
宣纸只有两指宽,被她用裁刀细细裁成小小一片,像一片偷来的影子。
纸上只勾了几笔:
一道极淡的眉峰,一粒落在眼尾的小痣,再加一笔衣襟的折线——
此刻指腹摩挲过去,先触到纸边的毛茬,再触到墨线微微凸起的触感,像摸到雪地里一截冰棱,凉得她心口发紧。
她忽然把袖子拢得更紧,像怕那影子被谁瞧见。
然后抬眼,冲尤月笑得云淡风轻:
“真到那时候,我就把自己藏起来,谁也不给看。”
第二日卯正,凤阳阁学堂。
长公主沈芷衣一进来便径直走向姜雪宁,扬声吩咐,今日她要与姜雪宁并肩。
薛姝抿了抿唇,牵着书匣默默退到次席。薛姝来了,尤月便该往后退。
尤月僵在原地——她的案几就在姜雪宁右手,若再退,便得排到最后一排。她攥紧袖口,刚要开口,视线越过人群,落在最末那扇大窗下:
宋铮铮正低头翻书,乌发垂在一侧,露出一段雪白后颈,窗外一枝海棠斜斜探进来,花瓣落在她肩上,像给她披了件胭脂色的纱。
尤月忽然就咽下了那句“凭什么”。
她想起昨日宋铮铮笑眯眯说的“坐后面可以看花”,心里“嘁”了一声——傻子,谢少师讲学千载难逢,居然把大好前排让给窗外的花。
看了宋铮铮那副样子,尤月想好看的风景哪里是花,分明是人。
于是尤月抱起书匣,走到宋铮铮旁边坐下,用肩撞了撞对方,小声嘀咕:“喂,别只顾看花,小心漏了笔记,回头借我抄。”
宋铮铮弯眼一笑,没辩解。
她确实不敢坐得太近——谢危今日仍是一身苍青深衣,襟口绣暗银云纹,日光一照,像雪里浮动的剑光。她怕自己只要坐在他眼皮底下,就会忍不住把目光钉在那道剑光上,再也挪不开。
如今躲到最后一排,隔着重重背影与一窗花影,她才能悄悄抬眼。
看一眼,再垂眸,用指甲在书页空白处极轻地划下一道线——像划下一笔没人瞧见的影子。
谢危踏进学堂时,檐外一阵风过,满树海棠簌簌而下。
他第一眼便看见最末一排的宋铮铮——仰着脸,鬓边落了一瓣绯红,跟着海棠花的影子左右摇动,呆得可笑。谢危唇角不自觉弯了一下,笑意极淡,像刀尖掠水,转瞬即逝。
“先生。”薛姝已起身,声音脆亮,“学生有一问。男子主外,女子主内,自古皆然。您为何让我们读您编的《经纬世务策》?
学堂霎时静得能听见花瓣坠地。
谢危负手立在讲席前,目光清冷:“太后昔日被困慈宁宫,手握玉玺,对峙叛军三日。她凭的不是《女诫》,而是《盐铁》《管子》与《六韬》。若只读闺训,如今诸位早已随凤驾殉国。不愿留者,自可离去。”
声音不高,却似薄刃贴耳。
薛姝攥紧袖口,脸色发白。
宋铮铮的心却轻轻震了一下。
她先想:他说得对。书就是书,策论也好,女诫也罢,本不该用男女划界。
可下一瞬,她又听见心里另一道小小的声音——
不是她们不想读别的,而是自打蒙学起,摆在她们案头的就只有《女诫》《内则》。
小时候,母亲教她读书,用的也是描红笺上“清闲贞静,守节整齐”八个大字。
她记得自己问:“为什么哥哥能念《左传》,我只能背《女论语》?”
母亲答得温柔:“因为你是姑娘家,日后要主持中馈,读那些做什么?”
那一刻她不懂,如今懂了——
原来所谓“本分”,是一面早就被设好的屏风,把天地隔成两半。
屏风这边,她们被教导如何低眉、如何柔顺;屏风那边,山河社稷、策马山河,从未想过要给她们留一扇门。
谢危的话像一把刀,挑破了屏风,却也带着刀本身的寒气。
宋铮铮偷偷抬眼,看见薛姝咬得发白的唇,看见尤月攥紧又松开的拳,看见方妙低垂的睫毛在颤。
她忽然觉得胸口发闷:她们不是不想走出去,而是从来没人告诉她们——门外有路。
“先生。”
极轻极轻的一声,从最后一排飘出来。
谢危目光微转。
宋铮铮站起来,花瓣从她肩头滚落,声音软,却字字清晰:“学生愿意读。只是……也请先生记得,今日座中许多人,并非不愿,而是从前无人问过她们愿不愿。”
学堂里静得连风都停了。
谢危看着她,眼底那点寒光似乎被什么轻轻碰了一下,泛起极浅的涟漪。
她抬眼,对上谢危微凉的目光。
那目光像雪夜里的灯,明明照得人无所遁形,却又在灯芯处藏着一点极暗的火。
宋铮铮心里莫名一跳,赶紧垂下脑袋,假装去抚膝上的落花——指尖却偷偷把那片花瓣折成了一个小小的方胜,藏进掌心。
谢危收回视线,翻开卷宗,声音恢复平静:
“既留下,便先读《度支篇》第三——‘生丝价起于东南,而税赋定于西北……’”
窗外一阵风过,海棠簌簌落下。
宋铮铮听着听着,又忍不住抬眼。
这一次,她没去看花,也没去看谢危,只盯着自己掌心那枚小小的方胜——
仿佛只要把它藏好了,方才那一瞬的心跳也能一并藏住。
学堂散课,檐外海棠被夕阳烘成一片暖霞。
尤月收拾完书匣,回头招呼:“宋铮铮,你走不走?”
宋铮铮攥紧袖中那张才画好的小像,笑着摇头:“你先回罢,我还想描两笔花样子。”
尤月不疑有他,跟着公主她们走了。门扉一阖,偌大的学堂只剩宋铮铮一人。她悄悄展开掌心——素宣不过两指宽,寥寥数笔,一截侧影:眉骨稜朗、眼尾微挑,像雪里斜挑的竹。
“差一点又让它溜了……”她小声嘀咕,鼻尖沁出一点汗,却忍不住弯唇。
收好画,她轻快地追出去。前头青袍曳地,谢危负手而行,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宋铮铮踩着那影子,心里像揣了只扑棱棱的雀儿:随便说一句也好——问今日留的课业,问策论里哪一句最难……只要叫住他,声音就能飞出去。
脚步才提,就见回廊转角处,姜雪宁抱着一摞书迎上来。谢危停了,微微侧身听她说话。霞光里,两人肩线几乎相触。姜雪宁抬眸,谢危低头,风把他们的声音剪得细碎,一句也飘不到宋铮铮耳朵里。
她忽然就钉在原地。
方才还雀跃的心口像被轻轻按进一汪酸涩的泉水,咕嘟咕嘟冒泡,却无人看见。
指尖在袖中蜷紧,那张小像的边角被汗意晕开一点墨痕。
夕阳愈沉,回廊的影子并成了同一个。
宋铮铮慢慢收回脚,退到海棠树下。花影斑驳,落在她睫毛上,像一场无人知晓的小雪。
谢危负手,指间勾着那卷燕临的策论,原只是托姜雪宁顺路带去。谢危把手中折好的课业递过去,语气漫不经心:顺道问一句——丝价暴涨,姜姑娘竟让人提前便屯了生丝。巧合?”
姜雪宁接过纸卷,指尖在封皮上轻轻一弹:“世间原就不少巧合。谢少师若事事都要寻个因果,岂非太累?”
她抬眼,眸子里带着一点笑,“还是说,你早已不习惯相信巧合?”
谢危低笑一声,没答。
他忽地想起另一桩真正的巧合——
谢危笑了笑,笑意像薄刃划破晚风。
他想起酒楼那一幕——
暖灯火,宋铮铮捧着一张字,眉眼弯弯,声音压得很轻,却藏不住欢喜:“我就是喜欢这个人的字呀。”
当时他坐在暗处,指尖摩挲杯沿,漫不经心地想:谁的字,值得她那样喜欢?
后来才知,那幅字是自己的。
初入京时,他曾赴礼部尚书宋府拜会,席间随手留了一幅字——不过是行草《快雪时晴》十四行。一次聚会后,酒后挥毫,写了一幅《少年游》。笔意纵肆,锋芒毕露,是十九岁科场得意的狂态。
他早忘了,却被宋铮铮从一堆旧卷里翻出来。
那之后,宋铮铮像掘到宝。她跑遍书肆,搜他早年应试的草稿;她临摹他的字,从飞白到顿挫,一日日练得手腕发酸。
伴读甄选那日,他阅卷,翻到一叠小楷——
笔迹还稚嫩,却一笔一划都是他的风骨:撇捺带着他十九岁的傲气,勾折藏着他当年的锋棱。
那一刻,他忽然就明白了:
原来她口中的“喜欢”,竟是自己的旧影。
谢危垂眸,指腹在卷轴上轻轻一敲,心里生出一点极轻的得意——
像雪夜独酌,忽闻墙外有人折梅,原是为他而来。
衔玉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当张起灵穿越莲花楼
- 云顶天宫,张起灵进入了青铜门,没想到却是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张起灵穿越莲花楼,与李莲花、方多病相遇于灵童案破获后。三人行变四人行,修狗......
- 45.5万字8个月前
- 东京复仇者:新号别搞
- 前期:“我要拯救大家啊!”后期:“你们不要过来啊!”(拆官配+万人迷)双男双女……如雷请退
- 0.9万字6个月前
- 白月光和白莲花同时爱上我
- 我的白月光回来了,我要追他...结果白莲花来捣乱。以为是情敌,可竟然是追求者,两者相争,我选其谁?
- 7.0万字5个月前
- 综影视至意难平
- 大梦归离小鹿女瑶cp待定进行中……已完成世界:51.春花焰馆陶公主刘嫖cp慕容璟和✅50.少年白马醉春风楚黎cp叶鼎之✅49.长相思苏雪cp......
- 375.0万字4个月前
- 陈情归来之携君入尘
- 一声魏婴续情缘,一世入尘平天下,锄奸扶弱,只为无愧于心,皆因世人贪念,总归尘土,云深遇良人,情不知所起,平生知己,红颜入心间,缘起缘灭成大道......
- 1064.6万字4个月前
- 春将暮
- 靠近你靠近痛苦,远离你远离幸福
- 1.5万字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