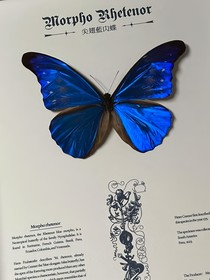第十六章 糖糕里的月光
李叔的糖糕摊子支在烟火巷中段的路灯下时,暮色正把青石板染成墨色。油锅滋滋地吐着泡,滚圆的面团在热油里翻个身,就膨成金黄的灯笼,糖心顺着裂开的小口往外淌,在油面上烫出星星点点的焦痕。
“今天的糖馅不对劲。”蹲在摊子前的赵奶奶咂着嘴,假牙把糖糕壳磨得咯吱响。她手里那只咬了半口的糖糕,糖心是浅褐色的,不像往常那样泛着琥珀光。李叔的长筷子在油锅里顿了顿,面团沉下去又浮起来,像团不肯听话的云。
“用了新磨的红糖。”他头也不抬地应着,往面团里包糖馅的手却慢了半拍。我看见竹匾里的红糖块带着细碎的黑渣——往年他总用南货店的老红糖,说是“熬得透,甜得沉”,今天这袋,是巷尾新开的便利店买的。
赵奶奶没再说话,只是把剩下的半块糖糕用油纸包好,揣进蓝布兜。她的背影在路灯下拉得很长,拐杖头敲在石板上的声音,比往常沉了三分。我突然想起上周赵奶奶来买糖糕时,曾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张泛黄的纸条,上面是她过世的老伴写的红糖糕方子,末尾还画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
后半夜收摊时,李叔把剩下的糖糕全倒进了泔水桶。油星浮在水面上,像片碎掉的月亮。“赵奶奶的老头子,当年是给我爷爷送红糖的。”他突然蹲在地上,用草绳捆着油桶,“那时候交通不便,他推着独轮车走三十里山路,红糖用棉被裹着,怕受了潮。”
我这才知道,李叔的糖糕方子,原是赵奶奶老伴传的。那年头物资紧俏,赵爷爷总把最好的红糖留给李家,自己家用掺了甜菜根的杂糖。“他说糖是甜人心的,不能掺假。”李叔用袖子抹了把脸,油锅里的余温把空气烘得发暖。
第二天清晨,巷口的南货店没开门。李叔站在紧闭的木门前,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纸条——是赵奶奶托人送来的,上面用铅笔描了个地址,说是城郊还有家老糖坊。他骑着吱呀作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出门时,车后座绑着的空糖罐,晃得像只装满了晨光的铃铛。
傍晚李叔回来时,自行车上驮着个半人高的陶瓮。他刚把瓮盖掀开,浓郁的焦糖香就漫了整条巷。赵奶奶拄着拐杖挪过来,往瓮里瞅了眼,突然红了眼眶:“就是这个味,当年他送的红糖,也带着点焦香。”
那天的糖糕卖得格外快。赵奶奶捧着刚出锅的糖糕,小口小口地抿着,糖心顺着嘴角往下滴,她却笑得像个孩子。李叔站在油锅前,额头上的汗珠掉进油里,溅起细小的火星,映得他眼角的皱纹都泛着光。
收摊时,李叔往赵奶奶手里塞了只油纸包。“刚出炉的,放了双倍红糖。”他挠着头笑,“按您老伴方子上写的,用慢火熬了三个钟头。”赵奶奶打开纸包时,月光正好落在糖糕上,糖心的光泽和天上的月亮交相辉映,像谁把满地清辉,都揉进了这甜糯的方寸里。
夜风穿过巷子时,带着糖糕的甜香。我看着李叔仔细地把赵爷爷的方子贴在陶瓮上,又往瓮里撒了把新炒的芝麻,突然明白有些味道从来不会消失,它们会变成月光,变成皱纹里的笑意,变成烟火巷里,代代相传的甜。
烟火巷里的味觉诗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拼命诉说
- 沈陌初对冉宁的爱,带满了痛苦。他爱她,可惜太迟了;她爱他,也因此付出了惨痛代价。但无论多少日夜颠倒,也无论她是否释怀过去种种,他一直都在她身......
- 0.8万字10个月前
- TF三代:入金陷渊
- 原本过着平常人家的生活的安一,在母亲攀上张家大树后实现了阶级跨越,她又该怎么面对之后的生活呢?网恋前男友×朱志鑫联姻对象×张泽禹豪门亲“哥哥......
- 2.8万字8个月前
- 戏子不简单(又名和我的军官上司谈个恋爱)
- 小甜饼民国林倾年刚回家就被他的朋友拖去了戏园,对于台上的人一见钟情。展开追求跟解冥悠相知相爱的故事。一起成长的故事
- 0.8万字4个月前
- 酸涩的butterfly
- 那个夜晚的飞机失事,给两人中间从此画上了一道不可磨灭的天河,迟来的爱却再无可能!
- 4.6万字4个月前
- 我在书中世界里彻底摆烂了
- #穿书#娱乐圈#搞笑#双男主#1v1岑宁在试戏的过程中离奇穿越成了同名同姓的一名有着相同经历的18线小胡咖身上,不幸遇到原生的死对头!!上选......
- 0.4万字3个月前
- 荒诞日常拯救计划
- 5.6万字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