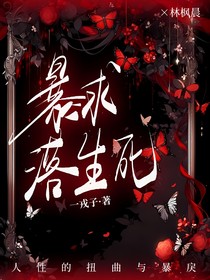第十七章 酸梅汤里的和解
入伏那天的蝉鸣刚起,张婶的酸梅汤摊子就支在了烟火巷口的老槐树下。粗陶瓮里浮着层细密的泡沫,绛红色的汤汁漫过沉底的乌梅,把正午的阳光染成透亮的琥珀色。我数着玻璃柜里的青瓷碗,突然发现少了最边缘那只——那是陈爷爷专用的,碗沿有道月牙形的豁口,是十年前他和张婶吵翻时摔的。
“陈老头今天没来?”隔壁炸糖糕的李叔往油锅里撒了把芝麻,香气混着酸梅汤的酸甜漫过来,“昨天还听见他在院子里念叨,说你这汤里少了样东西。”
张婶的长柄勺在瓮里搅了搅,木勺撞到陶瓮的声响闷闷的。她总说自家酸梅汤是烟火巷的招牌:乌梅要选福建的,山楂得用去核的,冰糖要分三次加,最后还要搁两朵晒干的洛神花。可陈爷爷偏说,真正的老方子得加陈皮,“你奶奶当年教我的时候,陈皮要放三年陈的,才有回香”。
这话戳在张婶痛处。十年前就是为这陈皮,两个老字号传人吵翻了天。陈爷爷的“陈家茶汤”和张婶的“张氏酸梅汤”本是巷子里的金字招牌,那年评“非遗传承”,就因陈爷爷在评审会上说张婶的方子“失了老味”,两家从此再没说过话。
日头偏西时,陈爷爷的拐杖声从巷尾传来。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手里攥着个牛皮纸包,站在酸梅汤摊子前三步远的地方,像尊晒褪了色的石像。张婶往青瓷碗里舀汤的手顿了顿,勺底的山楂果在碗里转了个圈,沉下去时带出细小的漩涡。
“丫头要喝酸梅汤。”陈爷爷的声音比蝉鸣还干涩。他身后跟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是他远房的孙女,昨天刚从乡下过来。小姑娘盯着玻璃柜里的碗,眼睛亮得像浸了水的黑葡萄:“爷爷说这里的酸梅汤,比罐头里的好喝一百倍。”
张婶突然抓起最边缘那只豁口碗,舀汤时手一抖,半勺汤汁溅在青石板上,洇出朵暗红色的花。陈爷爷掏钱包的动作停在半空——那只豁口碗,是当年他亲手送给张婶奶奶的,碗底还刻着个小小的“陈”字。
小姑娘捧着碗喝得直咂嘴,褐色的汤汁顺着嘴角往下淌,滴在胸前的小兜兜上。“爷爷,这里面有陈皮的味道!”她突然指着碗底,那里沉着一小块卷曲的橙黄色果皮,像只蜷着的小虫子。
张婶的脸腾地红了。我这才发现,今天的酸梅汤瓮里,果然漂着几片陈皮,颜色深得发褐,一看就是放了年头的。陈爷爷的喉结动了动,从牛皮纸包里掏出个小陶罐:“我这陈皮,是你奶奶嫁过来那年收的,正好三十年。”
夕阳把两个老人的影子叠在青石板上,像幅被拉长的水墨画。陈爷爷用拐杖尖挑出块陈皮,放进张婶的陶瓮里:“陈皮得和乌梅同煮,煮到汤色发暗才算好。”张婶没说话,却往他手里塞了只新碗,碗沿光溜溜的,是今早刚从窑厂取回来的。
收摊时,李叔的糖糕摊子还冒着热气。他笑着往我手里塞了块刚炸好的糖糕:“早该这样了。”糖糕的甜混着酸梅汤的酸,在舌尖化成股温热的暖流。我看着张婶和陈爷爷蹲在槐树下分陈皮,陈爷爷的拐杖靠在张婶的长柄勺旁,像两个终于肯并肩的老朋友。
夜风带着槐花香吹过巷口,陶瓮里的酸梅汤还在轻轻晃荡。豁口碗被洗得干干净净,放在最显眼的位置,碗底的“陈”字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光,像谁在时光里,悄悄刻下的和解诗。
烟火巷里的味觉诗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绝交吧,好朋友!
-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 65.8万字10个月前
- 极致的疯子才能幻化成天才
- 只有疯子才能被称为天才,疯子从来不是疯子,而是堕落的天才
- 3.5万字5个月前
- 星期一的蓝色狐狸(已完结)
- 架空校园救赎文(已完结)
- 2.1万字3个月前
- 错之语声逢
- 男主的爸爸把男主抛弃后被女主的妈妈捡回来养后发生了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
- 0.3万字2个月前
- 前世篇遗辜错付
- 莫栀颜与苏扶楹初中相识,因两人身份不同,只好在即将大学毕业时分开,苏扶楹决定追求梦想,毕业后选择当一名服装设计师,并自己开了一家小店,而莫栀......
- 2.3万字2个月前
- 暴求落生死
- 封面由快手上的三足鸟(4357476508)老师制作(无偿)又名《落生暴死》本书有xuexingbaoli情节林枫晨做好事却意外siwang......
- 0.3万字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