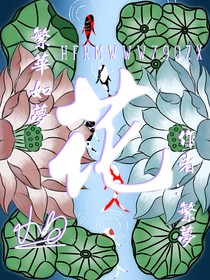云栖与云笙
“给!” 他飞快地把另一半塞进自己嘴里,一边嚼一边含糊地说,“快吃!躲……躲好!” 说完,不等疯狗反应,就像只灵活的小老鼠,又钻回箩筐后面,消失不见了。
疯狗握着那半块还带着小男孩体温和汗渍的杂粮饼,怔怔地站在原地。饼又硬又糙,混杂着尘土的味道。“啧,这小不点儿,自己都饿得前胸贴后背,还分我一半?”但这一次,这滋味里除了食物本身,还多了一层含义:是那个小乞丐,在目睹了她刚才的险境后,分享了他珍贵的食物,并且提醒她要“躲好”。这是一种来自同样挣扎在底层、同样朝不保夕的“同类”之间,无声的、朴素的关怀和守望相助。
她慢慢地把饼送到嘴边,小口小口地啃着。粗糙的饼渣刮过喉咙,却带来一种奇异的暖意。那个小乞丐的身影,连同之前摊主那声粗鲁却及时的呵斥,像两道微弱却真实的光,短暂地穿透了她心中厚重的阴霾。这世界固然冰冷残酷,但在缝隙里,依然存在着不求回报的援手和同类之间笨拙的温暖。她冰冷麻木的脸上,那丝微弱的松动似乎更深了一点。“行吧,这世道,也不全是烂泥坑。”
就这样,带着跛脚船夫沉默的芋头(“老头儿的烤芋头,真香!”)、哑婆婆破旧的蓑衣(“婆婆的蓑衣,够挡雨!”)、小乞丐分享的半块饼(“小耗子给的饼,硌牙但顶饿!”(ˊᗜˋ)و),以及无数个在寒夜中独自跋涉的冰冷记忆,疯狗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和灵魂,终于在一个飘着细雨的黄昏,看到了前方低矮的城墙和城门上模糊斑驳的字迹——青州县。
城门没有关闭,也没有炮火。进出的行人脸上带着疲惫,但少了那种刻骨的惊惶。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泥土气息、炊烟的味道,还有一种……属于人间的、缓慢而沉重的生机。“呼——,总算到个喘气儿的地界儿了?”
疯狗站在城门洞的阴影里,雨水顺着她披着的旧蓑衣滴落。她浑身泥泞,赤脚上布满新旧伤痕,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只有那双眼睛,在经历了极致的黑暗和沿途那些微弱的星火后,虽然依旧深藏着警惕和悲凉,却不再是一片彻底的死寂。那里面,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如同灰烬深处残存火星般的微光——那是人性在绝境中挣扎求存,并意外收获的点点温暖所留下的印记。
怀里的包袱依旧沉重,那罐灰菇冰冷依旧,丫丫的生辰八字紧贴着她的心跳。悲悯、无力、失去的痛苦并未消失,它们像烙印一样刻在她的骨血里。但此刻,站在这名为“青州”的土地上,感受着脚下泥土的实感,嗅着风中混杂的烟火气息,疯狗第一次清晰地感觉到:
她跑出来了。
她活下来了。
而这伤痕累累的“活着”本身,以及路上那些陌生人沉默或笨拙的善意,便是这片悲凉底色上,最真实、也最珍贵的人性温暖。“活着…真他娘的不容易,但也…不算太坏?”
她深吸了一口气,混合着雨水的清冷和人间烟火的气息,迈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青州县的暮色之中。前方的路依旧未知,但至少此刻,她暂时摆脱了那吞噬一切的绝望淤泥。新的故事,将在伤痕与微光交织的背景下,在这座同样饱经风霜的小城里,缓缓展开。
疯狗第一次见到云栖,是在青州城外那座被梅雨泡得骨头都酥了的药王庙里。空气湿得能拧出水,连绵的淫雨蚀尽了庙门朱漆,门楣上“悬壶济世”的匾额歪斜欲坠,虫蛀的孔洞如同溃烂的疮口。
她赤脚踩在积水的青砖上,苔藓滑腻如蛇,缠绕着脚趾。一股浓重的霉味混杂着陈年药草的苦涩,沉甸甸地压下来,像一张湿冷的裹尸布,勒得人窒息。庙堂深处,一个高大的男人正俯身给一个浑身脓疮的老者换药。粗布衣衫的后背洇开深色汗渍,动作却轻缓得像托着初生的雏鸟。
疯狗猫在柱子后面,死死盯着他头顶盘旋的魂色——深褐如凝结的血痂。她认得这种颜色。赌坊里典妻卖儿的赌鬼,衙门里草菅人命的差役,都拖着这般污浊的褐。“啧啧啧,又是个手上沾血的?”
可眼前这人,骨节分明的手指布满老茧,却透着一种奇异的温柔,眉骨上那道旧疤狰狞,一笑起来,眼角的纹路却舒展如晒透的稻田。“啧,这杀神笑起来还挺…慈眉善目的?怪哉……╮( •́ω•̀ )╭”
“新来的?”他抬头,递过一碗冒着热气的粥。粗陶碗沿有个小豁口,稀薄的米粒间浮着几点野菜。“喝了,帮忙晒药。”
疯狗没接,反而像只警惕的猫儿往后缩了缩。她的目光钉在他腰间那个褪色的旧香囊上——针脚歪斜如蜈蚣爬行,稚拙得刺眼。“这香囊缝得…跟狗啃的似的,哪个倒霉孩子的手艺?”
“云栖。”他并不在意她的戒备,径直把碗塞进她手里,掌心的粗粝刮过她手背,“栖云盟的,算不得好人,但能给你口饭吃。”
疯狗嗤笑,声音带着点沙哑的戏谑:“杀人犯么?” 她掂量着手里的粥碗,“这饭里…没掺什么不该有的‘料’吧?”
云栖的手顿了顿。供桌上油灯猛地爆开一朵灯花,将他半边脸映得明灭不定。他没否认:“嗯,杀过。” 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今天下雨了。
疯狗留了下来。这乱世,容身之处并非难寻——城南乞丐窝的草棚,码头苦力汗臭的通铺,甚至妓院后厨阴冷的柴房。可她走不了。云栖头顶那深褐的魂丝太古怪,它们不像其他杀人者那般张牙舞爪如荆棘,反而像古树深埋的虬根,沉默地、近乎温柔地,缠绕着每一个靠近他的生灵。“这人的魂色…跟老咸菜疙瘩似的,看着腌臜,闻着…倒还有点意思?” 她决定留下来,“就看看这‘咸菜疙瘩’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双手插腰。)”
第三日深夜,药王庙里静得能听见霉斑啃木头的声音。疯狗猫腰钻过晒药架子的缝隙,在药棚堵住了正独自碾药的云栖。月光从茅草顶的破隙筛下,将他佝偻的身影切得支离破碎,活像案板上没剁匀的排骨。药碾子单调的咕噜声在寂静里格外刺耳。
疯狗没直接问伤疤。她先是凑近药碾子,鼻子使劲儿嗅了嗅,故意用她那带着点沙哑的调子嚷嚷:“哎呦喂,这当归味儿冲的!能把死人熏活了!我说云大掌柜,您这手劲儿够可以的啊,碾得比耗子啃过的还碎!” 她一边说,一边状似无意地伸脖子去瞧他碾药的手。
月光和油灯的光线正好落在他那双骨节分明的手上。疯狗眼珠子贼尖,目光立刻锁定了那些隐藏在指关节褶皱里、细密交错的疤痕——那绝不是干活落下的茧子或砸药震的,分明是刀刃反复割裂又愈合的印记,像是被什么凶玩意儿啃过好几口又长好了似的。
“啧,” 她咂了下嘴,干脆不绕弯子了,小爪子(手指)直接虚虚点了点他指节上最显眼的一道疤,“这口子…瞧着可不像是药碾子咬的啊?哪个不长眼的刀子,敢跟您这铁手过不去?” 她语气带着点惯常的戏谑,但眼神却像探针,直勾勾盯着云栖的脸,想从那道疤脸上抠出点端倪来。
云栖碾药的动作只是极其细微地顿了一下,并未停下。咕噜…咕噜…药碾子的声音像碾在人心上。
“六年前,” 他开口,声音平淡得像在说今儿个天气不错,“一把剁骨刀砍的。”油灯昏黄的光将他扭曲的影子投在斑驳的棚壁上,影子晃动,真像一头被锁在破笼子里的困兽,在墙上徒劳地挣扎。
疯狗挑了挑眉,没吭声,心里嘀咕:“剁骨刀?嚯,够劲儿!这故事听着就带血沫子。”她看着他慢腾腾地从怀里摸出一方洗得发白、边角都磨起了毛的旧帕子。帕角上,一朵绣得歪歪扭扭的梨花可怜巴巴地趴着,针脚比他那破香囊上的“蜈蚣爬”还要笨拙几分,活像刚学爬的奶娃娃戳的。
云栖的目光落在那朵歪梨花上,那眼神,沉得能压垮一座山。他摩挲着帕子,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得像怕惊醒了帕子里的魂儿:“那晚…也下着雨,比现在还大。哗啦啦的,砸得屋顶直叫唤…” 他顿了顿,喉结滚动了一下,像是在咽下什么又苦又硬的东西,“我爹…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烟锅子烧得通红。他说…” 云栖的声音陡然低下去,带着一种冰冷的、刻骨的嘲讽,“县太爷家那个痨病秧子少爷,要个六岁的‘纯阳女娃’去‘冲喜’…值…二十两雪花银。”
疯狗心里“咯噔”一下,像被冰锥子扎了。六岁…冲喜…二十两…这几个词儿砸下来,她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比闻了馊粥还难受。她看见云栖握着帕子的指节骤然绷紧、泛白,捏得帕子都变了形,仿佛要把它嵌进骨头里。而就在这一瞬间,疯狗那双能窥见魂色的眼睛清晰地捕捉到——那原本深褐如血痂的魂丝里,竟悄然渗出几缕极其微弱的、却异常执拗的金线!那金线像从冻土里硬生生钻出来的嫩芽尖儿,又像血痂深处开出的、不要命的野花,微弱却倔强地缠绕着那方旧帕。
药碾子里,当归终于被彻底碾作齑粉,一股浓烈到极致的苦涩药香猛地炸开,呛得疯狗鼻子发酸。
云栖嘴角竟极其艰难地、极其缓慢地扯开一丝笑纹,眼角的沟壑因为这微小的动作而短暂地舒展开,却又立刻被更深的疲惫覆盖。“笙儿…” 他念出这个名字时,声音里才透出一丝真正的温度,像冰层下流动的水,“她当时啊,就缩在那柜子里…” 他抬起眼,目光似乎穿透了破败的棚顶,看向某个遥远又近在咫尺的地方,“小耗子似的,一声不敢吭…手指头都咬破了。” 他低头,指尖轻轻拂过帕子上那朵歪梨花,眼神温柔得能滴出水来,“如今…她能辨三百味药草,熬得一手好膏药…可这女红…” 他摇摇头,那丝苦涩又自嘲的笑纹更深了,“还是跟狗啃的似的,一朵梨花都绣不好。”
棚子里陷入一片死寂,只有油灯燃烧的噼啪声和远处隐约的虫鸣。那浓烈的苦涩药香仿佛凝固在了空气里。
疯狗沉默了。不是无话可说,而是心里堵得慌,像塞满了湿透的棉花。 她看着云栖指节上狰狞的旧疤,看着他死死攥着的那方绣着狗啃梨花的旧帕,看着那深褐魂色里挣扎着透出的、微弱却执拗的金光… 她脑子里那些关于“杀人犯”、“腌臜魂色”的标签,“咔嚓”一声,碎了个稀巴烂。
“呸!” 她突然低低啐了一口,不是冲着云栖,倒像是冲着自己之前那点浅薄的念头。月光下,她的眼睛亮得惊人,像是擦掉了一层蒙着的灰。
她懂了。
这深褐,哪里是什么罪孽的污秽?
这分明是血干透了、凝成痂的印记——
是被最深的苦难反复浸泡、捶打,却依然温热、依然能长出花来的厚土。
是一个哥哥用骨头和血泪,从地狱门口硬生生刨出来的一捧活命的土!
(内心咆哮:)这他娘的哪是腌臜?这分明是捂热了冻疮的泥!是能长出救命草的地!
梦长铭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快穿:娇软万人迷
- 全员单箭头,一见钟情梗,万人迷,脑子寄存—
- 4.5万字7个月前
- 玄界:生命与自然双灵能,在玄幻星际杀疯了!
- 『科技与灵能共存世界观,讲述的是女主两点半在玄幻世界经历各种各样有趣的事,结识许多的朋友,大女主,可以嗑cp,没有男朋友设定√,但是有很多男......
- 5.6万字8个月前
- 蘤
- 本片之前的名字《花》但由于一直打不出来,所以已《蘤》命名本篇文章是以一个穿梭在多重空间里的组织这个组织坐落在一道空间裂缝里名叫溟翼的神秘组织......
- 1.5万字8个月前
- 神界诸多事
- 围绕神界的几位神明而展开的故事,也有其展开的平行世界的故事
- 3.9万字4个月前
- 我给皇叔追皇姐
- 凌犀“世人皆知我爱孟婆,却无人知晓我爱得是你,再见之时我已是月老玄七”钰华“世人皆知我心系天下苍生,却无人知晓我为护你,方为三界之主,再见之......
- 8.4万字4个月前
- 怪异的小妹
- 林家有三子,两男一女。大哥名林萧,二哥为林子洲,三妹唤作林墨。那林墨满月之时,宴席上邀请了各大世家共同庆祝,却突发异状,她小脸泛红,哭声不止......
- 2.3万字3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