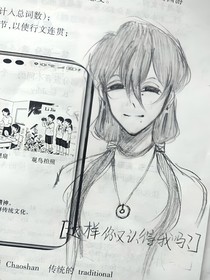奶系男友很听话
我家高岭之花男友,人前是冰山,人后是黏人精。
早上赖床非要我亲亲才肯起,出门前又蹭着要我帮他整理衣领。
直到回家发现厨房冒烟,他顶着一脸面粉从烤箱端出焦炭饼干。
“我、我看教程说这样你会开心……”他捏着烤盘小声解释。
我踮脚戳他鼻尖的面粉:“罚你打扫厨房。”
他立刻放下烤盘,湿漉漉的眼睛望过来:“打扫完……能喂我一块饼干吗?”
------------------
林屿这个人,在外面,是出了名的冰山,不苟言笑,眼神一扫就能冻住半屋子的人。可谁能想到,这尊冰雕,在我这儿,化得比春日里的最后一块残雪还快,黏糊得简直没眼看。
清晨的阳光,像碎金子一样泼了半床,暖洋洋地烤着被窝。闹钟响了第三遍,我闭着眼伸手去够床头柜,指尖刚碰到冰凉的塑料壳,腰上那条铁箍似的胳膊立刻又紧了紧,把我更深地拖进那个滚烫的怀抱里。
“再五分钟……”他含糊不清地嘟囔,下巴在我头顶蹭了蹭,细软的头发蹭得我脸颊痒痒的,呼吸间全是他身上那种干净又带着点暖意的气息,像晒透了阳光的松木。声音带着浓重的睡意,又软又糯,黏黏糊糊地钻进耳朵里。
我艰难地在他怀里转了个身,鼻尖几乎要蹭到他的下巴:“林先生,您再不起,今天早会就要变您的缺席审判大会了。”
他眼皮都没掀开,只是哼哼唧唧地,长睫毛在眼下投出浅浅的阴影。那副耍赖的样子,跟外面那个雷厉风行的林总监判若两人。我无奈,凑上去,在他温热的唇上飞快地啄了一下,像小鸟喝水。
“好了,盖章生效,起床令。”我拍拍他的背。
这下,那双紧闭的眼睛终于舍得掀开一条缝,眼底还氤氲着未散的睡意,像蒙着晨雾的湖面。他嘴角往上弯了弯,心满意足地又在我颈窝里拱了拱,这才慢吞吞地松开我,像一只终于被安抚好的大型犬。
好不容易洗漱完,换好衣服,我正对着玄关的镜子理头发,就听见身后熟悉的脚步声靠近。一回头,林屿已经穿戴整齐,笔挺的深灰色西装衬得他肩宽腿长,恢复了平日里那副精英模样,只是领带松松垮垮地挂在脖子上,领口也敞着,露出一点锁骨。
他站定在我面前,微微低下头,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我,也不说话。那目光,坦坦荡荡,又带着点无声的执拗,像个等着老师发小红花的小朋友。
“多大的人了,领带都不会系?”我故意板起脸,伸出手。
他立刻顺从地又低了低头,方便我的动作。指尖触碰到他颈侧的皮肤,温温热热的。我熟练地帮他整理好衬衫领口,把那条深蓝色的领带拉紧,系出一个端正的温莎结。他的目光一直落在我脸上,专注得近乎虔诚,仿佛我手里摆弄的不是领带,而是什么稀世珍宝。空气里有他须后水清冽的雪松味道,还有他身上独有的、令人安心的暖意。
“好了。”我最后拍了拍他的胸口,像完成一件重要作品。
他这才直起身,抬手自己又正了正领带结,嘴角弯起一个极浅的弧度,那点冰山融化的暖意只对我绽放:“嗯。”声音低沉悦耳,带着点晨起的微哑,像大提琴的低音弦被轻轻拨动。
送走这位“人前人后两张脸”的林先生,我长长舒了口气。白天是属于我自己的宁静时光。直到暮色四合,窗外的路灯次第亮起,像一串串发光的珠子。我估摸着他快回来了,换了身舒服的家居服,窝在沙发里看书。客厅只开了一盏落地灯,光线温柔,空气里有种黄昏特有的静谧。
然而,这份宁静很快被一种极其细微、极其不对劲的气味打破了。
像是什么东西……烤过头了?带着点蛋白质焦糊的刺鼻感。
我吸了吸鼻子,放下书,疑惑地站起身。那味道似乎是从厨房方向飘来的,而且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浓烈,还隐约夹杂着一丝……烟味?
心里咯噔一下,我快步走向厨房。越靠近,那股焦糊味就越发嚣张,简直像一张无形的网兜头罩下。推开厨房门的一刹那,我被眼前的景象钉在了原地。
烟雾报警器尖锐刺耳的蜂鸣声瞬间穿透耳膜,红色的警示灯疯狂闪烁,像一只受惊的眼睛。整个厨房弥漫着浓重的青白色烟雾,空气灼热呛人。抽油烟机嗡嗡地徒劳工作着,却根本无力招架这汹涌的浓烟。
而浓烟的源头,是站在一片狼藉中央的那个人。
林屿背对着我,高大的身影在烟雾中显得有些模糊。他穿着早上出门那件挺括的白衬衫,此刻袖子胡乱挽到手肘,昂贵的布料上溅满了可疑的深褐色斑点,还有大片大片斑驳的白色粉末。他头发有点凌乱,几缕发丝被汗水黏在额角。
最触目惊心的是他手里那个硕大的烤盘。烤盘上,赫然陈列着十几块……嗯,姑且称之为“饼干”的东西。它们呈现出一种近乎绝望的、深邃的炭黑色,表面布满狰狞的裂纹和焦糊的凸起,形态各异,扭曲得仿佛刚从地狱熔炉里捞出来的矿石。几缕带着焦糊味的青烟,正从这些“矿石”上袅袅升起。
他似乎被烟雾呛到了,侧过脸咳嗽了两声。这一侧脸,我才看清他的正脸——鼻尖、脸颊、甚至额头上,都沾满了白花花的面粉,活像刚从面粉袋里钻出来。几道可疑的黑灰横亘在面粉之上,大概是擦汗时不小心抹上去的。那模样,狼狈又滑稽,哪里还有半点“林总监”的清冷矜贵?
他似乎这才察觉到我的存在,猛地转过身。手里那个承载着“地狱特产”的烤盘也跟着晃了晃,几块焦炭饼干危险地滑动了一下。看到我,他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那双平日里深邃锐利的眼睛,此刻瞪得圆圆的,写满了惊慌和无措,像一只在森林里迷了路、突然被车灯照到的小鹿。
“我……”他张了张嘴,声音被烟雾呛得有些沙哑,还带着点不易察觉的颤抖,“我……我看教程说……说这样……你会开心……”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个字几乎含在喉咙里,眼神慌乱地在我脸上和那盘焦炭之间来回逡巡,捏着滚烫烤盘边缘的手指用力到骨节泛白。
空气里只剩下烟雾报警器不知疲倦的尖啸,混杂着抽油烟机的轰鸣,还有那挥之不去的、令人窒息的焦糊味。时间仿佛被这浓烟和噪音粘滞住了。
我看着他那张花猫似的脸,再看看烤盘里那些黑得发亮、形状诡异的“作品”,一股气堵在胸口,不上不下。生气?对着这张写满“我错了但我真的只是想哄你开心”的脸,火气像被戳破的气球,“噗”地一声就泄了大半。想笑?眼前这堪比灾难片的厨房现场和那盘“焦炭艺术品”,实在又让人笑不出来。
我深吸一口气——立刻被呛得咳嗽起来。烟雾缭绕中,我几步上前,踮起脚尖。指尖准确无误地戳向他鼻尖那一小撮特别显眼的白面粉。
“林屿,”我的声音因为咳嗽和强忍的笑意而显得有些怪异,“你是打算把厨房点了,然后我们今晚抱着这盘‘开心’去睡大街吗?”
指尖传来的触感温热,沾上了细腻的面粉。他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眼睛飞快地眨了几下,长长的睫毛上似乎也沾了点白色的粉末。他垂下眼帘,目光落在我戳着他鼻尖的手指上,像个做错事被抓包、等待审判的孩子,连呼吸都放轻了。
“罚你——”我收回手,故意板着脸,拖长了调子,目光扫过他身后那片杯盘狼藉的战场:操作台上像是被面粉炸弹袭击过,白茫茫一片;打蛋盆歪倒在洗碗槽边,里面残留着可疑的黏稠蛋液混合物;地上还躺着几个空鸡蛋壳,像小小的白色残骸;烤箱门敞开着,里面一片焦黑,惨不忍睹。
我顿了顿,清晰地吐出后半句:“把这里,全部打扫干净。”
话音落下的瞬间,林屿那双湿漉漉的眼睛“唰”地抬了起来。里面刚才的惊慌无措像退潮一样迅速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异的亮光,混合着一点委屈,一点期待,还有小狗看到肉骨头般的专注。他甚至毫不犹豫,立刻就把手里那个烫手山芋般的、装着焦炭饼干的烤盘“哐当”一声放在了旁边唯一还算干净的料理台角落。
然后,他往前凑近了一小步,高大的身影在烟雾中显得格外有压迫感,却又带着一种奇异的温顺。他微微低下头,温热的气息拂过我的额发,那双好看的眼睛一瞬不瞬地锁着我,嗓音放得又低又软,带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
“打扫完……”他顿了顿,喉结轻轻滚动了一下,目光飞快地瞟了一眼烤盘里那堆黑乎乎的东西,“……能喂我一块饼干吗?”
空气里,烟雾报警器还在声嘶力竭地尖叫,焦糊味固执地往鼻腔里钻。他脸上沾着面粉和灰,头发乱糟糟,昂贵的衬衫变成了抹布,厨房像个刚被龙卷风扫荡过的战场。
可他那双眼睛,湿漉漉的,亮得惊人,里面清晰地映着我的影子,像落满了星子的深潭,纯粹得只剩下一个执拗的、近乎孩子气的期待——打扫完战场,能不能得到一块属于他的、烤焦了的“糖果”?
我看着他鼻尖上那点被我戳过的、还没掉的面粉印子,又看看那盘实在无法称之为食物的焦炭。
“行啊,”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带着点磨牙的意味,又掺杂着一丝绷不住的笑意,“林总监,说话算话。你打扫,我‘喂’你。” 我特意在“喂”字上加了重音,看着他瞬间亮起来的眼神,心里那点残余的恼火彻底被一种又好气又好笑的无奈淹没。
这笨蛋,大概连那块饼干到底能不能吃都完全没考虑过。他脑子里大概只有“我做了饼干给她,她答应了喂我”这个简单到冒傻气的逻辑链条。
我退开一步,抱起手臂,抬了抬下巴,指向那片狼藉:“请开始你的表演,林大清洁工。”
男朋友小日常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被怨灵覆没的世界(第3部)
- 看前言
- 5.8万字5个月前
- 旧日绘卷
- [新人初次写文,不喜勿喷]听见旧日的低语了吗?棋子落入棋盘,搏弈的赢者是谁?是神祇端坐于诸天之上?亦或是人在牵动着傀儡的丝线?
- 4.5万字5个月前
- 棺音
- 《棺音》是一部充满诡异色彩的悬疑小说,作者佛棺异客以独特的笔触为读者开启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
- 5.9万字2个月前
- 难违命规
- 乐皓源:“宦墨轩你像璀璨的星辰,能遇见你真好。”宦墨轩:“乐乐你是我儿时的光亮,现在由我照亮你”屈一飞:“齐斐遇见你我可真幸运啊!(ᐢᴖ·̫......
- 1.2万字2个月前
- 柳南记事
- 就说这傅华羽遇到同为术士的梁奎、看着娇小但实力很强的安小姐、不怎么爱说话的嬴逢和自私自利的廉晟磊,四人最后的结局又会怎么样呢?且听我下回分析......
- 1.4万字2周前
- 基因咒:脑熵轮回
- (此书伏笔较多,脑洞巨大,节奏较慢,非爽文,且第一人称,喜爱无脑文和快节奏的勿入。) 当你的DNA开始说谎,该如何相信自己的真实存在? ......
- 7.1万字1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