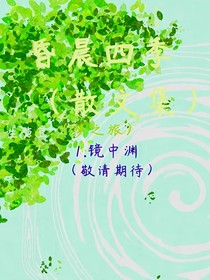布衫旧痕 2
他最终住进了城市顶端的一个水泥房间。四壁是毫无生命的森冷灰色,天花板异常高,空旷得像被吸走了声音的空间。那口孤零零垂挂的墙钟,滴答滴答,规律得让人心头发慌,每一个精准刻度的移动仿佛都在无声丈量着一种我们感知不到的时间。有人不知出于何种心思,在他房间唯一的小窗户外钉了一个粗糙的铁条鸟笼。起初,笼里有只羽毛凌乱、叫声暗哑如裂帛的斑鸠。后来斑鸠没有了,只剩下一个黑黝黝、空空荡荡的笼子轮廓,悬在同样灰白空洞的天幕前,像一个生硬的标点符号。
那段时间阴雨连绵。雨脚密密匝匝敲打着玻璃窗,水痕交叠又散开。他似乎格外容易疲乏,时常沉默地背对着门蜷缩在那张过于宽大的床上。那件常年浆洗的旧布衫偶尔晾在椅背上,水汽濡湿使它看上去更加脆弱而单薄,颜色是那种陈年的、接近腐朽的白。有人送来药汤,棕色,散发着浓烈的苦气,热气很快在瓷碗上方凝成薄薄的白雾,散逸在冰冷的空气里。他抬起眼皮,视线从雾气上掠过,既不看人,也不看碗。药汤渐渐冷了,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膜,最后变成一只毫无生命气息的褐色陶土碗盏。
他更多时候是起身,在那座水泥房间的地板上来回踱步。脚下的水泥地冰冷平坦,脚步落在上面几乎悄无声息。他走得很慢,沿着墙壁内侧画出一个又一个周而复始、不断叠加的方形轨迹。影子被顶灯拖得很长,贴着地面移动,变形,像一头蛰伏的巨大生物。有时他会突然停下,并非凝视墙壁或者窗外,而是死死盯着自己投在地面上那团扭动的黑影,下颌线条绷得极紧。
有晚半夜我醒来,或许是下雨的缘故,或许是那过分精确的滴答声搅扰了神经。走廊灯熄灭着,只余他门底下透出一线极淡的光。我起身,鬼使神差地朝那片微弱的光源走去。门并未关死,一条缝隙。我屏住呼吸从那条窄小的缝隙望进去。他竟端坐在桌前,桌上摊着一本极厚的大开本册子,纸页黄脆。他枯瘦的手指捻着书页一角,那页面上似乎是密密麻麻、曲折蜿蜒的河流水道图。可他并没有在看那些线条。他的眼睛微微闭着,头极其轻微地在摇动,不是否定,倒像是一种抵御不住的晕眩,或者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反复地、微弱地撞击着后脑。他搁在纸边的一只手,五指神经质地、极其快速地反复屈伸——张开、捏紧、再张开,指骨在桌面擦出细微窸窣的刮擦声,像是有无数只细小的耗子在啃噬那层看不见的蜡。房间里只有滴答声和他指骨的刮擦声纠缠在一起,寒冷寂静的雨夜仿佛凝固成了一整块巨大的、不透气的冰。
后来,更大的城市陷落得无声无息,像一枚熟透的果子砰然砸在烂泥地里。我们撤入山地深处。一条简陋的盘山公路绕着灰绿色的山体向上攀爬,路旁偶尔闪过一株半株挂着零星枯叶的野柿树。车队沉默,只有发动机粗重的喘息在冰冷的空气里回荡。他单独坐在一辆旧吉普的后排,车窗紧闭着,玻璃蒙着厚厚一层泥尘和水汽,将他蜷缩的身影扭曲成一个模糊、蠕动、难以识辨的灰色团块。那件发黄的白布衫隐在更暗处,只偶尔在车子剧烈颠簸的缝隙里显露一个褪色的边角。风撞击着车身,呜呜作响。
山上的驻地是个废弃的林场木屋,木头散发着长期被雨水浸泡的霉湿味儿,朽烂和被虫子蛀空的地方比比皆是。我们住在他隔壁。头几日还能听见他房里有缓慢的踱步声,沿着木板墙壁内侧单调循环,如同墙上那台早就停摆的挂钟指针曾经可能划过的轨迹。后来那脚步声也消失了。一个沉重的黄昏,铅灰的云层压在山梁尖上,空气憋闷得像浸满了水的破棉絮。我端着一碗煮成浆糊似的疙瘩汤推门进去。他竟靠在冰冷的板壁下睡着了,头歪向一侧,那姿势看着就不舒服。他额角顶在墙壁一条裂开的缝隙上,缝隙深处渗出冰冷的潮气。我靠近,放下碗的动作惊动了他。他倏然睁开眼,那眼神是散的,茫然地向四周虚空搜索,仿佛刚从某个遥远、破碎而陌生的场景中艰难浮出水面。额角被板壁缝隙压出一道浅浅的红色凹痕。他的嘴唇很干,似乎嗫嚅了一下,却什么也没能说出。最后,他迟缓地转过脸,目光空洞地落向小窗外那片被山风撼动、哗哗乱响的浓密杂木林,深秋的风刮过树林,仿佛无数只黑色瘦骨嶙峋的手在拍打着空气。
命运的折痕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特种兵之火凤凰:戎马一生只为守护信仰
- 战鼓擂动,英雄志在四方;铁血丹心,无愧使命担当。踏遍山河,无愧雄心壮志;战旗飘扬,无愧热血满腔。一身戎装,一生荣耀闪光;保家卫国,不负国家,......
- 12.6万字7个月前
- 大爱仙尊:我怎么是古月方正啊?
- “你以为穿越成反派弟弟,就注定是方源的踏脚石?”古月方正一睁眼,成了《蛊真人》里被兄长剜心炼蛊的倒霉弟弟。觉醒的隐忍系统却要他“忍辱偷生”—......
- 3.0万字4个月前
- 癫狂审判
- “我们都一切都是被控制的?”“是的。”“那……”“没错,我现在说的话,我的思维,都是被控制的。”“那几次循环……”“命运因果而已,改变不了什......
- 0.2万字4个月前
- 祈愿凉归
- 风雪,战争,灾年又将侵袭衍国,而前定国侯的嫡长子安凉,又被当今的皇上盯上……
- 0.4万字1个月前
- 昏晨四季(散文集)
- 就是简单说一些日常的灵感事情,有时候是一些只有一篇的小散文,有时候算是一个连续的故事,有自己的词牌名。准备好面对镜中的自己了吗?《镜中渊》—......
- 5.1万字2周前
- 星核猎手捡到失忆美强惨
- 5.4万字6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