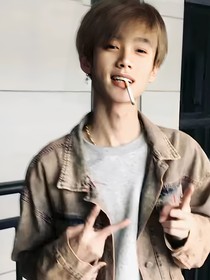第2章 春灯(二)
沈溯静静的坐在房间,江洄好像总是这么热情,好像对所有人都一样。
那是自己第一次见江洄,在旧鼓楼后面的钟表铺。
那天的风像坏了节拍器的曲子,把梧桐叶吹得乱七八糟。沈溯蹲在地上捡碎玻璃,指尖划开一道很深的口子,血滴在铜制齿轮上,像一粒朱砂落在老雪里。
“你流血了。”有人蹲下来,递给他一张揉皱的演出票。
票根背面印着德彪西《月光》,日期是 2019 年 5 月 12 日——那是沈溯母亲最后一次登台的日子,也是她吞下整瓶安眠药的日子。
沈溯抬头,看见一张过分明亮的脸。少年额前的碎发被汗打湿,眼里晃着整条春熙路的霓虹。
“我叫江洄。”少年说,“大提琴 A 组,音院附中。”
沈溯没说话,把票根折成很小很小的方块,塞进胸前的口袋。
很多年后,沈溯在凌晨四点的病房里醒来,看见江洄背对他站在窗前,那截票根被做成了吊坠,悬在锁骨之间,像一滴永远不会坠落的雨。
沈溯伸手想碰,却只碰到空气。
原来他们之间,从一开始就是隔着玻璃的。
沈溯第三次见到江洄,是在市立博物馆的修复室。
那天,江洄把一把断颈的大提琴抱进来,要求“让它再活一次”。
沈溯只用目光示意:放那儿。
江洄却故意俯身,在离他左耳只剩十厘米的地方,用气声说:“修得好,我请你喝酒。”
沈溯没抬头,但左手腕的旧疤在袖口下微微发烫——他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像坏掉的节拍器,失控地快了两拍。
江洄开始频繁出现。
他会在沈溯低头补绢帛时,用指尖敲工作台,敲出《天鹅》的开头四小节;
沈溯从不回应,却在下一次江洄靠近时,把刚补好的裂缝朝外侧移了十五度——那是方便江洄右耳听清共鸣箱的弧度。
他们像两把音叉,各自残缺,却开始共享一段听不见、说不出的频率。
某个雪夜,江洄带着半瓶威士忌闯进修复室。
他右手小指肿得厉害,却硬要拉琴给沈溯听。
琴弓第三次滑脱时,沈溯第一次主动伸手——不是扶琴,而是攥住江洄的手腕。
江洄愣住,沈溯在他掌心写:
“疼就停。”
江洄却用左手把沈溯的指尖带到自己喉结,让他感受声带的震颤:“沈溯,我要怎么停啊?”
江洄的泪水大滴大滴的落下来。
沈溯张了张嘴,唇形在“t”与“ing”之间碎裂,像被剪断的胶片。
江洄凑近,用额头抵住他:“没关系,我听见一半就够了,我听见你说了,我就停。”
沈溯手腕有些颤抖,江洄的指尖感受到沈溯左腕上的一道道凸起,江洄发现了沈溯的割痕。
后来江洄则在沈溯左腕的割痕上,纹了一串摩尔斯电码:
· — · — · — (I)
— — — (L)
· — ··(O)
· — — (V)
· (E)
— — (U)
沈溯回到家后,静静的靠在门边上,他第一次吻了江洄——不是唇,是那截带着“LOVE YOU”的小臂。
好像没有人不会爱江洄,他自由,热烈明媚,好像世界上所有美好的词语都能与他相配,沈溯的指尖第1次碰上江洄的手腕时,像他和上天交换了一张残缺的门票。
而江洄呢,他第1次见到沈溯就知道自己喜欢他,那个人太安静了,好像总有一层奇幻而密闭的屏障将他与世界隔绝开来,像是街边的泡泡,江洄想要戳碎那层泡泡。
所以江洄的十七岁生日愿望是:
——“让沈溯开口说一句话,哪怕只是‘嗯’。”
因为他记得,当他拎着琴盒站在钟楼底下,三月的风吹得猎猎作响。沈溯坐在钟楼的台阶上,膝盖摊开一本《机械钟表原理》,纸页被风掀起,像一群白鸽。
江洄把琴盒“哐”地放在他面前:“沈溯,帮我翻谱。”
沈溯没动。
那天江洄拉的是圣-桑《天鹅》。最后一个泛音消失时,钟楼上的铜铃突然响了——下午四点整。
沈溯终于抬起头。
江洄逆光站着,琴弓垂在身侧,像一柄收鞘的剑。
沈溯说:“弓根太用力,第二把位偏高。”
声音很低,像冬天里被雪压断的松枝。
江洄愣了三秒,然后笑得见牙不见眼:“原来你会说话啊!”
沈溯没接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薄荷糖,放在江洄掌心。
糖纸是绿色的,印着一片很小的叶子。
后来江洄攒了一整罐这样的糖纸,在 2019 年的冬天全部烧掉。火光照亮他半张脸,他说:“沈溯,你骗我。”
沈溯的抽屉里有一本《失语症临床观察》,扉页写着:
“病人无法完成‘我爱你’的发音,疑似创伤后语言中枢选择性抑制。”
江洄发现这本书是在 2018 年的暑假。
那天他溜进沈溯家,想偷看沈溯写给暗恋对象的信——结果信没找着,倒是在书柜最底层翻出这本书。
江洄坐在地上,笑得直打滚:“原来你是真的说不出来啊!”
沈溯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两杯冰美式,表情有点无奈。
江洄晃着书:“那我要是喜欢你,岂不是很吃亏?”
沈溯把咖啡放在桌上,蹲下来,用指尖碰了碰江洄的喉结。
指尖很凉,像一块玉。
江洄瞬间安静了。
沈溯的指尖一路向下,最后停在江洄心脏的位置。
“这里听得见。”沈溯说。
江洄眨了眨眼,突然有点慌。
江洄开始教沈溯用手语说“我爱你”。
沈溯学不会,他的手指只能做精确修复,却打不出柔软弧度。
于是江洄把大提琴横放在两人之间,让沈溯把左手按在弦上,自己用弓拉。
琴弦震动,沈溯的掌心感到“嗡——”一声长鸣。
江洄用口型无声地说:
“这是‘我’。”
接着他换了一把更短的弓,让弦发出短促的三连音:
“嗡、嗡、嗡。”
“这是‘爱’。”
最后,他让沈溯自己拉一次。
沈溯右手僵硬,拉出一道嘶哑的滑音。
江洄把耳朵贴在他胸口:“我听到了,完整的。”
江洄登台,独奏改编版《广板》。
观众席最后一排,沈溯捧着一束鲜花。
曲终,江洄放下弓,没有鞠躬,而是朝沈溯的方向,用右手小指在空气里划出一道弧线。
那是他们私下约定的暗号:
“我爱你。”
沈溯站起来,左手拇指抵住喉结,艰难地做了一个口型。
没有声音,但江洄“听”见了。
因为下一秒,整个音乐厅的灯突然熄灭,只剩舞台上一束追光。
光里,沈溯走到江洄面前,把一枚用旧琴码雕成的戒指套进他右小指。
戒指内侧刻着一行小字:
“Time will not heal, but we will.”
江洄用琴弓在沈溯左腕的银线上,轻轻敲了三下。
这是他们共同完成的,第一句也是最后一句:
“我爱你。”
江洄和沈溯第一次接吻,是在 2018 年的 6 月。
那天是江洄的生日,他请了全班同学去 KTV,沈溯也来了。
玩到一半,江洄不见了。
沈溯找了一圈,最后在安全通道里找到他。
江洄坐在楼梯上,抱着膝盖,像一只被雨淋湿的狗。
沈溯蹲下来:“怎么了?”
江洄抬头,眼睛红红的:“他们说我爸要娶新老婆了。”
沈溯没说话,只是伸手摸了摸他的头发。
江洄突然扑过来,抱住他:“沈溯,我只有你了。”
沈溯僵了一下,然后回抱住他。
两人抱了很久,久到安全通道的声控灯都灭了。
黑暗中,江洄的呼吸喷在沈溯的颈侧,很热。
沈溯的指尖碰到江洄的嘴唇,像碰到一块烧红的炭。
江洄小声说:“沈溯,我想亲你。”
沈溯没说话,只是低头吻住他。
那是一个很轻很轻的吻,像一片雪落在唇上。
江洄的眼泪掉下来,砸在沈溯的手背上。
沈溯用拇指擦过他的眼角:“别哭。”
江洄哽咽:“沈溯,你会一直陪着我吗?”
沈溯点头:“会。”
那天之后,他们开始偷偷谈恋爱。
沈溯会在江洄练琴的时候,给他带一杯冰美式;
江洄会在沈溯修表的时候,坐在旁边给他念谱子。
他们像两只小兽,在寒冷的冬夜里互相取暖。
2018 年 12 月,沈溯的母亲去世。
葬礼那天成都下了很大的雪。
江洄在墓园门口等到天黑,才看见沈溯出来。
沈溯穿着黑色大衣,领口有一圈很小的白色绒毛,像落了一层雪。
江洄冲过去抱住他。
沈溯没动。
江洄说:“沈溯,你哭吧。”
沈溯还是没动。
江洄把他压在一棵松树上,雪从枝头簌簌落下。
“你哭啊!”江洄吼道,“你他妈哭出来行不行!”
沈溯的眼神很空,像是被抽走了灵魂的钟表,只剩下一具精致的壳。
江洄踮起脚,吻他的眼睛。
沈溯终于眨了一下眼,睫毛扫过江洄的嘴唇,像一场很小的雪崩。
那天江洄把沈溯带回家。
沈溯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雪,轻声说:“我没有妈妈了。”
江洄跪在地板上,把额头抵在沈溯的膝盖。
“我也没有。”他说,“但我有你。”
沈溯的手指插进江洄的发间,很慢很慢地揉了揉。
“江洄,”他说,“我可能会变成很坏的人。”
江洄抬头看他:“那我就变成更坏的人,陪你一起坏。”
沈溯笑了,那笑容像冰裂的湖面,底下是湍急的水。
2019 年 5 月,江洄的右手小指骨折。
是沈溯砸的。
那天江洄在排练厅,拉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第二大提琴协奏曲》。
最后一个和弦,他故意拉错了一个音。
指挥暴跳如雷:“江洄!你他妈在干什么!”
江洄把琴扔在地上,笑得像个疯子:“我拉错了,又怎样?”
沈溯冲进来,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你疯了吗?”沈溯的声音在发抖。
江洄看着他,一字一句:“你不是说我拉错一个音就去死吗?我现在拉错了,你怎么还不去死?”
沈溯的拳头砸在江洄的右手上。
骨头断裂的声音很清脆,像折断一根树枝。
江洄跪在地上,疼得浑身发抖,却还在笑:“沈溯,你终于生气了。”
沈溯蹲下来,抱住他。
“对不起。”沈溯的声音哽咽,“对不起……”
江洄把脸埋在他肩窝,眼泪渗进黑色毛衣。
“沈洄,”他说,“我疼。”
沈溯吻他的手指,吻那截扭曲的骨头。
“我知道。”沈溯说,“我陪你疼。”
2019 年 6 月,江洄退学。
沈溯在火车站送他。
那天成都下着雨,江洄的背包上挂着一只很小的毛绒熊,是沈溯抓娃娃抓到的。
江洄踮脚亲了亲沈溯的下巴:“等我回来。”
沈溯点头。
火车开动的瞬间,江洄把那只熊从车窗扔了出去。
沈溯站在原地,看着那只熊被雨水打湿,像一团脏兮兮的云。
江洄在火车上哭到崩溃。
沈溯在站台上站到天黑。
那天之后,他们断了所有联系。
溯洄从之y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王楚钦:娇醉
- 简介正在更新
- 1.0万字9个月前
- 非正常关系(半娱乐圈)
- 程司瓷表面是个不出众的化妆师,实际是专跟鬼打交道的小道士,看似是新人,实则是经验丰富的老手,他是个有良心但不多的道士,碰到解决不了的事,他会......
- 10.7万字9个月前
- 陌路终是不相逢
- 安之若素,微笑向暖。
- 10.9万字2个月前
- 七零美娇娘:嫁个军官生萌宝
- [娇软甜妹vs面冷心热军官]姜宝儿是青山村的福娃娃,从小就运气好,别人都挖空的山上,她去逛逛就能捡到野鸡野鸭,甚至还能捡到极品山参。姜宝儿就......
- 2.1万字4周前
- 璇子:椿璇并茂
- 璇子CP原创女主(有hxt但没有感情喜欢hxt的别进)本文可能会给非非搭新的Cp
- 1.3万字3周前
- 海风与白衬衫
- 谢清宴与钟宴丞,从校园到婚纱的20年爱情长跑,从青涩少年到成熟大人,学会勇敢表达爱。岁月安宁,气质恬雅(谢清宴)宴然自若,沉稳可靠(钟宴丞)
- 14.2万字2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