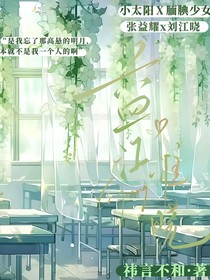第4章 夜航
7 月 22 日 16:05,G308 次列车准点抵达成灌快铁犀浦站。
江洄把大提琴盒背在右肩,右手小指仍打着白色铝托。
他右耳的蝉鸣从 6000Hz 降到 4000Hz,却多了低频轰鸣,像鼓风机贴着耳膜。
出站闸机刷身份证——“验证失败”。他侧身让后面的人,第三次才听见闸机提示音:
“滴——请通行。”
声音像隔着一层毛玻璃。
沈溯站在黄色警戒线外,手里拿一把黑色长柄伞,伞檐滴水。
他今天穿了件墨绿色工装夹克,领口别着一枚黄铜表盘改装的领针,指针停在 17:23。
江洄出现的那一刻,沈溯的呼吸出现 0.5 秒停滞。
他把伞往前倾,像递出一柄倾斜的天幕。
江洄没接伞,直接撞进他怀里,琴盒硌在两人胸口。
沈溯闻到他头发里有北京地下室的霉味、列车盒饭味,以及淡淡的松香。
江洄在他耳边说:“我右耳快聋了,你得大声点。”
沈溯却发不出声音,只把他抱得更紧。
7 月 23 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耳鼻喉科。
沈溯挂的“特需号”,江洄把病历本塞进沈溯手里:“你替我回答,我说话费劲。”
诊室门合拢,沈溯第一次对陌生人开口——
“他右耳低频 40dB,伴耳鸣,病史 40 天,突发性可能性大。”
嗓音哑得像砂纸,却足够让医生抬头。
“你是家属?”
沈溯点头,喉结滚动。
医生开了鼓室注射+高压氧,顺带一句:“病人情绪焦虑,最好同步心理科。”
走出诊室,江洄用左耳凑近沈溯:“医生说我焦虑?”
沈溯在病历本上写:【我也焦虑。】
江洄笑,接过笔补一句:【那一起治。】
7 月 25 日,暴雨回潮。
沈溯把江洄带回钟楼上的小屋——那是母亲生前的调音室,四面墙嵌满钟表机芯。
雨点砸在铁皮屋顶,像无数枚硬币滚落。
江洄把琴横在膝上,试音,A 弦低了 20 音分。
他拧轴,右手小指使不上劲,啪——弦轴滑脱。
琴弦反弹,在他虎口划出一道细血线。
沈溯单膝跪下,把他的手指含进嘴里,血腥味混着金属味。
江洄浑身一颤,用左耳贴近沈溯胸口,听见心跳像过载的节拍器。
“沈溯,我快听不见你的心跳了。”
沈溯把他拉进怀里,用极轻的声音说:
“那就让我听见你的。”
江洄低头吻他,舌尖尝到雨水的咸。
钟表滴答、雨声、耳鸣,三种节奏在黑暗里错位,像三支乐队同时调音。
凌晨 3 点,两人被同一声炸雷惊醒。
江洄的耳鸣骤停,世界突然真空。
他抓住沈溯的手腕,指甲陷进皮肤。
沈溯反手扣住他,用拇指一下一下摩挲他的腕骨——那是他们约定的 SOS:
· —— · —— · —— · ——
江洄张了张嘴,发出一声无声的尖叫。
沈溯把他压进床褥,额头抵额头,用气息而非声音说:
“我在这儿。”
一秒后,耳鸣重新灌进江洄右耳,像洪水冲垮闸门。
他大口喘气,眼泪顺着太阳穴滑进鬓角。
沈溯用舌尖舔去那滴泪,咸得发涩。
7 月 27 日,高压氧舱,江洄开始接受治疗。
舱内加压到 2.2ATA,耳膜胀痛。江洄捏鼻鼓气失败,右耳尖锐刺痛。他抬手示意,技师暂停加压。沈溯隔着舱窗看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再指向他:
【一起呼吸。】
江洄闭上眼,想象自己躺在沈溯的钟表铺里,耳边是慢半拍的怀表。疼痛竟奇迹般缓解。
出舱时,江洄右耳听阈回升 15dB,他听见沈溯说的第一句话是:
“饿不饿?”
声音像隔了十年,又像只隔一层纱。
8 月 2 日凌晨,暴雨第二场。
钟楼顶层漏雨,电路跳闸,所有钟表同时停摆。
黑暗里,江洄踩到一块碎玻璃,脚底划开 3cm 口子。
沈溯点燃最后一支蜡烛,把他抱到工作台上,用酒精冲洗。
江洄疼得直抖,却突然笑:“沈溯,你看,我们又停电了。”
沈溯没笑,用纱布缠好他的脚,然后俯身吻住他的脚踝。
江洄弓起背,手指插进沈溯发间,声音发抖:
“别再把我送走了。”
沈溯用鼻尖蹭他的小腿,哑声答:
“除非你把我一起扔掉。”
蜡烛燃尽,最后一滴蜡油落在江洄脚背,烫出一声极低的呜咽。
8 月 15 日,沈溯带江洄去墓园。
雨后的石板路湿滑,江洄把琴弓当拐杖,一瘸一拐。
墓碑前,沈溯点了三支香,鞠躬,然后跪下。
江洄没跪,他把大提琴架在碑前,拉《天鹅》第一主题。
右耳仍有轰鸣,但他把 A 弦调成 438Hz ——比标准略低,像一声迟到的叹息。
琴声在潮湿的空气里飘,沈溯背对墓碑,眼泪砸在柏油路面。
曲终,江洄用左手比了一个手势:
手掌贴胸,食指指向墓碑,再指向沈溯 ——
以后,我陪你守时间。
8 月 31 日,暑期最后一天。
江洄复查,右耳恢复到 25dB,耳鸣转为偶发。
医生笑:“小伙子恢复得不错,再坚持一个疗程。”
走出医院,江洄把诊断书折成纸飞机,朝空中一扔。
纸飞机被风卷进银杏树梢。
沈溯抬手看表:下午 17:23。
他忽然说:“江洄,我们开一间诊所吧。”
江洄侧头:“什么诊所?”
“时间诊所,”沈溯顿了顿,“专治来不及和回不去。”
江洄笑出声,把右耳贴过去:“大声点,我刚治好。”
沈溯深吸一口气,用尽全力,一字一顿:
“江洄,在一起吧。”
江洄眨了眨眼,眼泪先一步掉下来。
沈溯用左手捂住江洄的嘴,右手小指勾住江洄的左手小指那只还打着铝托的、微微变形的小指。
“好,”江洄说。
“但这一次,轮到我先开口。”
成都最热的一天。
“0:00 诊所”冷气坏了,沈溯把门敞开,让穿堂风卷走酒精味。
柜台玻璃下压着江洄的复查单:
右耳 60dB,左耳 90dB;医嘱:避免强声刺激。
沈溯用红笔在医嘱旁写:
“那就让他只听我的心跳。”
夜里十一点,江洄排练完《春之祭》回来,浑身汗味。
他把大提琴横在门槛,人直接倒在地上。
沈溯拎一桶冰水给他冲脚,
江洄缩了一下,笑:“医生不是说要保暖吗?”
沈溯把毛巾盖在他脚背,声音低却清晰:
“我比医生管用。”
9月,沈溯给江洄做了一台“骨传导耳机”。
原理粗暴:把蓝牙振子贴在乳突,再把信号放大 20dB。
第一次试听,江洄抓住沈溯的手腕,
“我听见你的脉搏,像低音鼓。”
沈溯把耳机摘下来,贴在自己胸口:
“现在轮到我听你。”
两人交换耳机,心跳在颅骨里共振,
像两条暗潮在耳蜗里相遇。
9 月 20 日,北京实验剧团正式邀请江洄。
邀请函上写:
“为聋人观众版本《天鹅》招募首席大提琴。”
江洄把邀请函折成纸飞机,飞到沈溯面前:
“我去三个月,回来陪你过冬。”
沈溯把飞机展开,在背面写:
“我只给你三个月零一天,逾期罚款——一辈子。”
沈溯送江洄去东站。
检票口,江洄把一张车票塞进沈溯口袋:
北京→成都 2019.12.31 17:23 硬座
“如果那天我没回来,你就把票撕了。”
沈溯握住他的手腕,声音第一次发抖:
“如果你敢不回来,我就去北京,把你绑回来。”
北京。
江洄的排练厅在地下二层,手机没信号。
他给沈溯发微信,消息一直转圈。
沈溯把诊所座机接到手机热点,
每天 23:00 准时打过去,响三声,挂断——这是他们约定的暗号:
“我还活着,也想你。”
9 月 15 日,江洄排练到凌晨,
脚下一滑,右耳撞到铁架,
耳鸣像炸开的白炽灯。
他蹲在地上,手指抠着地板缝,
无声地喊沈溯的名字。
成都暴雨。
沈溯在钟楼顶层修表, 一道闪电劈断电线,
他整个人被掀翻,喉头撞到桌角。
当晚,他发现自己说不出完整句子,只能发出气音。
他给江洄发语音,
江洄听不见,只能看见转圈的语音条。
10 月 8 日,江洄从北京寄回一只纸箱:
里面是一双磨破的舞鞋、
一张写着“对不起”的车票、
以及一只烧焦的毛绒熊——
熊肚子里塞着沈溯当年送他的薄荷糖纸,
糖纸背面写着:
“等你回来,我们一起吃新的。”
沈溯把糖纸含在嘴里, 甜味早已蒸发,只剩苦涩。
10 月 15 日,成都暴雨橙色预警。
沈溯坐在诊所门口,
雨水漫过门槛,漫过他的脚踝。
他抱着江洄留下的琴盒,
一遍遍擦弦,弦却越来越锈。
凌晨三点,江洄突然出现在街对面,
浑身湿透,手里攥着那张 12 月 31 日的车票。
沈溯站起来,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
“你迟到了。”
江洄把车票撕成两半,
一半塞进沈溯口袋,一半自己吞下:
“我把回程时间吃掉了,现在只能留在你身边。”
10 月 31 日,万圣夜。
两人把诊所搬到钟楼废墟顶层,
用透明雨布搭了一个帐篷。
雨布外是城市灯火,
雨布里只有一盏煤油灯。
江洄把大提琴横在两人之间,
弓毛断了三根,
他用手指拨弦,发出沙哑的颤音。
沈溯把右手覆在他手背上,
低声说:“以后,我做你的弦。”
江洄侧头,左耳贴着他胸口:
“我听不见,但能感觉到。”
雨布外,一道闪电劈过,
照亮废墟上唯一完好的字:
【0:00】
溯洄从之y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倾城掠影:许诺的薄昇
- 独立设计师许诺与商业巨头薄昇之间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在一场华丽的商业宴会上,两人一见钟情,却因各自的坚持和背景而陷入一场强取豪夺的较量。随着......
- 2.6万字9个月前
- 八色协奏曲
- 4男4女作者的神仙8人友谊现实版爱情公寓?不,是友情公寓~根据真实经历90%还原我们,是同一套小说的书迷我们,是风格迥异的创作者我们,是彼此......
- 1.0万字6个月前
- 我想起来了漂泊的意义(暂定标题
- ☝唉,本故事主要讲的是一个比地球大十倍的蓝星上,世界各国纷争不断,一个黑袍男在人贩子手中救下来了一个小女孩一起漂泊的俗套模板文。精神状态不是......
- 4.5万字6个月前
- 青州为枝
- 十七岁时风华正茂的年纪,也是心动的开始。心动始于初见,说好是一见钟情,其实是蓄谋已久。
- 1.0万字5个月前
- 顶A傅总他占有欲太强
- 【双男主/快节奏/甜文/】“我说我现在想跑还来得及吗?”“来不及”——和我同在一条船,没那么容易下来哦注:多个同世界,同人物,不同剧情
- 4.6万字3个月前
- 益江淮晓
- 本文是双向暗恋文,是BE文哦,女主在高二时暗恋的,男主在高一时暗恋的,后面会有几个人一起成为5人小队
- 1.2万字3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