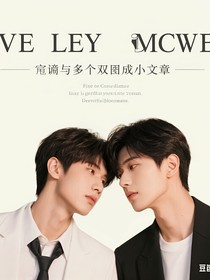胎毛绳梯
酒瓶在陈九安掌心滑了一下,冰凉的玻璃贴着橙汁结晶的痕迹,像某种活物的鳞片。他没松手,也没再看王大春那颗能映出便利店角落的头颅。招财猫嘴里转动的铜钱方向不对——那不是罗盘该指的方位,是倒的。
他把酒瓶塞进道袍内袋,抬脚踹向楼梯口的镜面残片。
玻璃没碎,反而像水面般荡开一圈涟漪,映出的不再是他的脸,而是一座倒悬的塔楼轮廓,塔尖插在地下,塔基悬在云里。王大春喉咙里发出一声闷响,像是被人捂住了嘴,他的镜面头皮上浮现出一行字:“梯子是反的。”
话音未落,地面裂了。
不是水泥开裂,是整块镜面像蛋壳一样剥开,无数细密的胎毛从缝隙里钻出来,带着烧焦脐带的腥味,缠上陈九安的脚踝。那些毛发又黑又韧,沾着暗红黏液,一碰皮肤就收紧,像活蛇往肉里钻。
他咬破舌尖,血滴在掌心,画了个“破契符”。铜钱刚贴上胎毛,就“啪”地炸成黑灰。胎毛断了一截,可断口立刻长出新的,反而把李桂香的脚也缠了进去。她还昏迷着,嘴唇发青,假发歪斜,露出头皮上那道渗血的契文。
“操。”陈九安低骂一声,把尸酒泼向地面。
酒液落在镜面上,发出“滋”的一声,像烧红的铁按进油锅。镜层开始冒泡,胎毛的蔓延慢了半拍。他趁机拽起李桂香,拖着她往楼梯冲。每走一步,背后的镜墙都在重组,碎玻璃悬浮空中,拼成无数个倒立的千斤闸虚影。
就在他踏上最后一级台阶时,一根胎毛猛地抽上来,缠住他手腕。他反手用铜钱割断,断裂处喷出一股黑血,溅在楼梯扶手上,立刻腐蚀出几个小洞,冒出焦臭烟气。
李桂香被拖到门口,突然在昏迷中喃喃一句:“绳是反的……头朝下才是梯。”
话音落下,整栋老宅的天花板轰然塌陷。
不是砖瓦砸落,而是整片镜面天花板像被什么东西从上面撕开,裂成蛛网状。上百根粗如手臂的胎毛绳索从天而降,像蜘蛛吐丝,瞬间织成一张巨大的网,将四人全部兜住,吊离地面。
陈九安悬在半空,胎毛勒进肩膀,铜钱在裤兜里发烫,几乎要烧穿布料。眼罩下的符纹像被烙铁贴着,疼得他眼前发黑。他抬头,看见那些绳索不是垂下来的——它们是从上往下“长”出来的,根部扎在云层里,一节节扭动,像脊椎在伸展。
王大春在旁边大吼:“别碰绳子!这是‘倒悬引魂幡’!活人碰了会替死!”
话音未落,远处工地传来塔吊的轰鸣。那台钢铁巨兽正缓缓转向老宅,吊钩像巨爪般高高扬起,对准他们悬空的位置。
胎毛开始收缩。
每根绳索都随着某种心跳般的节奏收紧,勒得陈九安肋骨发出咯吱声。他掏出铜钱去割,可刚割断一截,断口立刻再生,反而多出几股细毛,缠上他的脖子。
“没用的……”他喘着气,抬头看那云层中的绳头,“这东西……是活的。”
就在这时,陈小雪动了。
她被单独吊在中央,镇魂钉在她后颈微微震颤,毛衣口袋里的平安扣裂开一道缝,霉斑蔓延成符文形状。她咬了咬唇,突然伸手撕开衣领,露出锁骨下方那道旧疤。
然后,她低头,用牙齿咬破下唇。
血顺着嘴角流下,滴在右手的口红上。那支口红早就干裂,颜色暗红如凝血。她抹开嘴唇,将带血的膏体狠狠按在缠住自己的胎毛绳上。
“他说过……”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却异常清晰,“血契要血来解。”
火,烧起来了。
不是明火,而是从口红涂抹处蔓延出一道暗红色的光,像血管在胎毛里搏动。整条绳索猛地一抖,发出婴儿啼哭般的尖啸。其他绳索也开始燃烧,火光顺着胎毛网迅速扩散,空中浮现出“七月初七”四个字,由灰烬拼成,悬在半空三秒,才缓缓散去。
塔吊的钢索已经甩出,带着千钧之力劈向绳网。
就在撞击前一瞬,陈小雪左眼缝着的绣花针“叮”地一声,脱落一针。
绳梯没断。
反而活了。
燃烧的胎毛扭动起来,像一条苏醒的巨蟒,整张网开始向上拉升。王大春拼命挣扎:“别让它拉!这是引魂幡!上去了就回不来!”
陈九安却突然伸手,死死抓住一根燃烧的绳索。
“不是引魂。”他盯着绳芯里浮现的墨迹——那是他再熟悉不过的符咒笔法,是他爷爷二十年前写在黄纸上的那种,“这是接应。”
王大春瞪着他:“你疯了?这是杀阵!”
“杀阵不会写‘以吾孙血,续梯三丈’。”陈九安声音低下去,手指抠进燃烧的胎毛里,“它认的是血契。我们不是祭品……是它要救的人。”
他把最后一枚铜钱塞进燃烧的绳节。铜钱瞬间熔化,变成一颗赤红的符眼,嵌在绳结中央。整条绳梯猛地一震,所有火焰向内收缩,绳索拉直如剑,带着他们垂直升空。
塔吊的钢钩擦着脚底掠过,砸进老宅天井,碎石飞溅。
他们越升越高,胎毛绳梯像活龙般扭动,穿过云层。陈九安低头,看见城市缩成一片暗影,工地的探照灯像萤火般微弱。
就在他们升至最高点时,云层裂开一道口子。
云中,隐约浮现出千斤闸的轮廓,铁门半开,像是在等他们落下。
陈小雪忽然浑身一颤。
她听见一个声音,贴着耳膜响起,像是从她体内传出来的:
“橙子熟了。”
民间的鬼故事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铠甲勇士星辰
- 男主唐明峰本来约好朋友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旅途当中。无意间得到了铠甲变身器。开始了一段全新的冒险。率先说明啊,整本书剧情偏长一些,分上下两......
- 4.6万字7个月前
- 穿越成一只小鸟
- 原创,长生不死小鸟看世间万物,男,以路人视角看其他事物(因为是穿越,不认识食物,又因为不死,所以有毒的有难吃有好吃,没毒的非常好吃)
- 0.3万字6个月前
- 西游记2010(二)
- 悟空失望之后离开了西游团队,再次和唐僧几人相遇却成为了敌人,唐僧再也找不回曾经那个一直保护他,信任他的悟空了(孙龙cp)
- 20.6万字4个月前
- 铁树长情
- _(:з」∠)_(已签约)【现名:树影照人双】李成锦x李苏民阮恬恬x宋归林遇金不换的铁树Vs假真诚的锦花热情活力好学生Vs失落堕落坏学生一开......
- 4.5万字3个月前
- 星辰交织的灵魂
- 不由多个双男主小故事组成的书
- 4.3万字1个月前
- 魔尊重生后被系统逼成校花
- 10.0万字3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