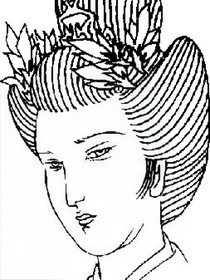新的转机
“三天二十支?赵先生,这怕不是要了命?”王二把最后一块铁锭扔进石灶旁的水坑,蒸腾的白汽裹着铁腥味扑了满脸,“官营作坊的老师傅都说,‘十炉九废’,咱这临时搭的炭炉,能成五支就烧高香了。”
赵夜没说话,正蹲在地上用树枝画图纸——枪管只留三尺(比明军制式鸟铳短半尺,省料),扳机用熟铁直接锻打(省去雕花、刻款的工序),引信孔斜钻三十度(减少炸膛风险,牺牲部分精度)。他指尖划过“枪管厚度”的标记,突然抬头:“我们造的不是‘合格铳’,是‘救命铳’。”
“啥意思?”李根正用铁锉打磨枪管毛坯,虎口震得发麻。
“官造铳要保十年不炸膛,咱的铳,能打十枪就行。”赵夜捡起块从矿洞带出来的熟铁——这是最关键的“取巧”,省去了从矿石冶炼熟铁的两月工期,“这些铁锭是官矿废弃的熟铁,含碳量早就达标,直接锻打就能用,省了最耗时间的‘炒铁’工序。”
周铁山蹲在烽火台边缘,望着山下蜿蜒的小路,手里攥着马三留下的半张卫所布防图——张恪的残兵果然在往鹰嘴崖方向移动,烟尘在谷底像条黄蛇,约莫有五十多人,还牵着两匹驮着火药的马。
“得加快了。”周铁山把布防图拍在石灶上,“张恪的人离这儿不到十里,他们要是发现烽火台有铁,肯定会拼命攻上来。”
赵夜突然站起来,对着众人道:“改工序——枪管不淬三遍火,淬一遍就行;准星不用铜片,直接在枪管上敲个凸点;枪托不用硬木,找些耐烧的桦树枝,削巴削巴就能用。”
“那打两枪不就炸膛了?”春丫正往炉膛里添木炭,闻言手一抖,火星溅在脚背上。
“总比被流民军砍死强。”赵夜摸过李根手里的枪管毛坯,指尖能摸到锻打的纹路,“我们要的是‘能响’,不是‘耐用’。闯王的人要这些铳,是为了突袭卫所残兵,打一仗就够了——打完了,铁匠营有的是时间修。”
这话像盆冷水,浇灭了众人对“精品铳”的执念。乱世里的铁器,哪有那么多讲究?能在生死关头响一声,就是好铳。
分工立刻调整:王二带三个壮实的流民专司锻打,把熟铁锭烧红了往死里砸,只求枪管成型;李根和两个年轻人负责“快手淬火”——把锻好的枪管扔进掺了盐的冷水里(盐能让冷却更快,省时间),冒完白汽就捞出来;周铁山用马三留下的野猪肉皮擦枪管(猪油能防生锈,省去打磨工序);赵夜则蹲在石灶旁,凭手感校准引信孔的角度,手指被烫出了水泡也顾不上擦。
春丫的活儿最杂:给炉膛添炭要盯着火候(太旺会烧化铁料,太弱打不动),给众人递水要算着时间(每人喝三口就得停),还要盯着烽火台底层的暗室——那里藏着最后的盐和半袋救命的米。
第二天傍晚,第一支“快手铳”成了。
枪管泛着不均匀的青黑色(一遍淬火的后遗症),枪托是根歪脖子桦树,准星就是个歪歪扭扭的铁疙瘩。李根抱着铳跑到五十步外的崖边,对着块从卫所缴获的铁甲扣动扳机——“砰”的一声,铁屑飞溅,铁甲上穿了个指甲盖大的洞。
“成了!能穿甲!”李根举着铳大喊,声音里带着狂喜。
赵夜却摸了摸枪管,烫得吓人:“打第二枪试试。”
李根刚把第二发铅弹塞进枪管,还没扣扳机,枪管突然“咔嚓”一声裂了道缝——果然,一遍淬火的枪管扛不住第二发的压力。
“没事。”赵夜从石灶旁捡起块破布,擦了擦李根脸上的硝烟,“打一枪就够了。”
第三天清晨,烽火台的石灶旁已经堆了十九支铳。最后一支还差淬火,王二正抡着大锤往死里砸枪管,胳膊上的青筋暴起,像条要蹦出来的蛇。
“快了!就差一锤!”王二吼着,声音嘶哑。
突然,周铁山从崖边滚了下来,肩上插着支箭,血顺着箭杆往下滴:“他们来了!张恪的残兵……带着火铳!”
众人瞬间绷紧了神经。赵夜抓起一支铳塞给李根:“你守左边石阶,五十步外打领头的。王二,放下锤子,拿铳守右边——记住,只打一枪,打完就换地方!”
他自己也摸了支铳,摸索着走到烽火台入口,耳朵贴在断墙上听——脚步声杂乱,带着喘息,还有人在喊“冲上去抢铁!总兵大人说了,带回去有奖!”
是张恪的亲兵,大概还不知道张恪已死在卫所兵变里,只想着抢点铁去投靠别的官军。
“来了!”李根的声音发颤。
赵夜听见第一支铳响了,是官军的鸟铳,子弹打在断墙上,碎石溅了他一脸。他深吸一口气,凭着枪声判断方位,举铳对准石阶拐角,扣动了扳机——
“砰!”
一声惨叫从石阶下传来,接着是滚石坠落的声响。
“打中了!”春丫忍不住喊。
赵夜没停,摸出第二发铅弹往枪管里塞,手指被烫得钻心疼——这铳果然只能打一枪,枪管已经烫手了。
官军的反扑更猛了,有人开始往烽火台底下扔火把,想烧着木柴逼他们出来。周铁山忍着痛,抱起石头往下砸,嘴里骂着:“狗娘养的!有种上来单挑!”
就在这时,王二突然喊:“看那边!是马三的人!”
赵夜听见了——是骑兵的马蹄声,越来越近,还夹杂着熟悉的呼哨声,三短两长,是闯王哨探营的信号。
官军显然也慌了,枪声变得杂乱。赵夜抓住机会,对李根道:“扔最后一支铳下去!”
李根抓起那支没淬火的枪管毛坯,使劲往石阶下扔——铁器撞击石头的脆响,在官军听来,像是还有很多铳。
“撤!快撤!闯王的人来了!”石阶下传来惊恐的呼喊,脚步声瞬间变得慌乱,往山下逃去。
马蹄声很快到了烽火台底,马三的声音响起:“赵先生!没事吧?”
赵夜扶着周铁山站起来,肩上的箭已经被春丫拔了,用盐袋里的粗盐撒在伤口上(春丫说这样能消炎),疼得周铁山直抽冷气。
“二十支铳……还差一支。”赵夜望着石灶旁的十九支铳,声音有点哑。
马三跳上烽火台,看见满地的铁屑和发烫的枪管,突然大笑:“这十九支就够了!比我想象的强十倍!”他指着山下官军逃窜的方向,“看见没?就凭这些铳,咱能把张恪的残兵追出三十里!”
他从怀里掏出个皮囊,扔给赵夜:“这里面是火药,够你们用到登封。收拾东西,现在就走——去晚了,铁匠营的好位置就被别人占了。”
赵夜捡起地上的十九支铳,掂量了掂量,每一支都滚烫,像揣着一团火。这些铳确实粗糙,打不了几枪就会坏,甚至可能炸膛,但它们刚刚救了所有人的命,还将带着他们走向开封,走向那个“均田免赋”的模糊未来。
周铁山被两个闯王的兵扶着,咬着牙站起来:“走!去开封!”
春丫把最后一点盐塞进怀里,李根背着母铳,王二拎着老铁锉——这把从草棚带到矿洞,又从矿洞带到烽火台的铁锉,已经磨得短了半截,却仍是他们最顺手的家伙。
队伍慢慢往山下走,十九支铳被分着扛在肩上,在朝阳下泛着青黑的光。赵夜走在最后,摸着怀里那支没装准星的短铳,突然想起刚穿越时在草棚里的日子——那时他们连块像样的铜料都没有,如今却能带着十九支铳,跟着闯王的人走向战场。
“赵先生,想啥呢?”春丫回头喊他。
“想开封的铁匠营。”赵夜笑了笑,空洞的眼窝里像藏着点光,“那里的铁,应该比矿洞的更纯吧?”
马三在前头喊:“开封府的官仓里,不光有铁,还有缴获的红夷炮零件!你们要是能把炮修好了,闯王说不定赏你们个‘火器百户’当当!”
笑声在山谷里回荡,混着马蹄声、脚步声,还有远处隐约传来的号角声——那是闯王的大军在集结,要往开封去了。
(本章完)
盲龙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锦瑟华年情未央
- 古代言情
- 1.4万字8个月前
- 感受中国传统女性故事
- 描述历史人物的故事。
- 1.5万字3个月前
- 胤禛重生之我的青梅竹马是爱新觉罗……胤禟
- 本小说讲述了雍正皇帝胤禛重生后的故事,相见不如不见,不见不如不念,但愿彼此心安深处是吾乡。
- 0.8万字2个月前
- 大理寺咸鱼探案手记
- 1.0万字2个月前
- 中华上下五千年(第一季)
- 历史
- 4.1万字4周前
- 青锋隐情
- 《青锋隐情》主线剧情脉络第一卷:暗涌(冷青风身份危机初现)核心冲突:冷青风的杀手过往被屠烈威胁,必须在保护北幽/师门与隐藏身份之间抉择。关键......
- 0.4万字1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