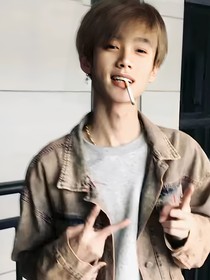第十五章 对骂
马蹄踏碎河岸的薄冰,溅起浑浊的泥浆。叶初蘅勒马停在赤水河畔的前沿观察哨,凛冽的江风扑面,却吹不散她眼中凝结的冰霜与杀意。望远镜的视野里,对岸人影绰绰,一面残破却异常醒目的红旗在料峭寒风中猎猎作响。她几乎一眼就锁定了那个站在高处、同样举着望远镜的身影——白婉龄!那身影挺拔如青松,隔着奔流的赤水河,仿佛都能感受到她目光中的锐利与嘲弄。
“白婉龄!”叶初蘅的怒吼压过江涛,带着撕裂的沙哑,被风卷向对岸,“你这背主求荣、忘恩负义的下贱胚子!赤水河的水,也洗不净你手上的血污!”
望远镜中的身影似乎顿了顿,随即放下,一个清晰、略带沙哑却异常响亮的女声顺着风飘了过来,带着浓重的关外腔调:“哎哟喂!这不是叶大小姐吗?隔着条河嚷嚷啥?火气还没下去呐?小心嗓子嚎劈叉喽!”典型的东北腔调,带着毫不掩饰的揶揄。
这轻飘飘的回应如同火上浇油。叶初蘅胸中那被强行压下的怒火轰然炸开,母亲教导的温婉汉语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血脉里属于草原的暴烈彻底主宰了她。她猛地将手中的勃朗宁弹匣高高举起,朝着对岸的方向,用尽全身力气,吼出了那古老而怨毒的诅咒:
“ ( 黑洞里的野狗!长生天降雷劈死你!)”
粗粝的蒙古语脏话裹挟着寒风,像淬毒的投枪,狠狠掷向对岸。那声音里的怨毒与诅咒之意,即使听不懂语义,也让河岸这边随行的士兵们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仿佛听到了来自地狱的狼嚎。
对岸沉默了一瞬。
随即,白婉龄的声音再次响起,那东北腔调拔高了,带着针尖对麦芒的犀利,语速快得像连珠炮,毫不示弱地怼了回来:
“嗬!叶大小姐能耐见长啊!蒙古话骂得挺溜!咋地?骂人还得翻祖宗家谱找词儿?憋急眼了就学野狗呲牙乱嚎?省省吧!有那功夫多琢磨琢磨你那‘神机妙算’咋就成筛子眼儿了!几十万条枪杆子,愣是让俺们这些穿草鞋的‘泥腿子’在你眼皮子底下‘溜达’了四趟!你那地图画得再花哨,不也成俺们兜里的玩意儿了?还‘神助’?呸!是你们自个儿蠢得冒泡,瞎指挥,净拿兄弟们的命填你那狗屁不通的‘铁桶阵’!叶初蘅,你瞅瞅你脚下淌的是啥?是水?那是你自个儿兄弟的血!是你不长脑子流的脓!”
白婉龄的东北话如同冰锥,又狠又准,专挑叶初蘅的痛处戳。每一句“泥腿子”、“溜达”、“蠢得冒泡”、“兄弟的血”,都像重锤砸在叶初蘅的心口。她气得浑身发抖,望远镜几乎捏碎,眼前阵阵发黑,喉咙里那股腥甜再次翻涌。叶初蘅彻底失控,更恶毒、更粗鄙的蒙古语诅咒如同决堤的洪水,疯狂地倾泻而出,诅咒着白婉龄的血脉和出身,声音因极致的愤怒而扭曲变形,回荡在空旷的河岸。
“哈哈哈!”白婉龄爆发出一阵极具穿透力的、带着浓浓嘲讽的大笑,“急啦?急眼啦?翻来覆去就那几句鸟语?老娘听不懂,也懒得懂!有本事你游过来啊?光站那边儿跳脚骂娘顶个屁用!还‘血’?叶初蘅,你记着,‘鹞子’的血,羊角坳的血,还有这赤水河两岸被你们祸害死的乡亲的血,都在天上看着你呢!你那‘青天白日’的皮再光鲜,也遮不住里子烂透了的臭!还‘瓮中捉鳖’?下次再想整这出,提前吱声儿,省得俺们‘不识抬举’,又把你那破瓮踹稀碎!这弹匣,”她似乎扬了扬手,指向叶初蘅手中的东西,“好好留着!下次见面,看看到底是它先喂你颗‘花生米’,还是老娘先把你那身狗皮扒下来当擦脚布!”
白婉龄的东北话骂得酣畅淋漓,字字如刀,句句见血,将叶初蘅的骄傲、部署、武力威胁连同那身军装都踩进了泥里。
“啊——!”叶初蘅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尖啸,暴怒之下竟将手中的望远镜狠狠掼在地上,镜片瞬间碎裂飞溅!她双眼赤红如血,死死盯着对岸那个模糊却无比刺眼的身影,胸膛剧烈起伏,如同濒死的野兽。冰冷的杀意取代了所有语言,那支擦得锃亮的勃朗宁弹匣在她掌心被攥得滚烫。
“白婉龄……”她声音嘶哑,如同砂纸摩擦,“赤水河……今日流的,是我叶家军的血……来日,我必让你,让所有‘**’,用你们的血……把这赤水……再染红一次!血洗!我定要血洗赤水!”
凛冽的江风卷走了她最后的毒誓,只剩下赤水河浑浊的波涛,在两位宿敌之间,奔流不息,仿佛预示着未来更加惨烈的血色碰撞。
青丝烬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我真的很美丽(单纯分享语法)
- 英语语法(适用于初中,高中,专升本和四级的基础语法)
- 10.6万字5个月前
- 对你的爱永无止境
- “失去的意识前一刻,我想到的是东北雪林里吹来的冷风和你的眼睛”
- 0.2万字4个月前
- 失忆后蹦出来一个未婚夫
- 这个作者很懒什么也没留下~
- 0.2万字3个月前
- 浅亦识,南亦知
- 娱乐圈小甜文白月光女神*国民老公温暖高贵大小姐*幽默开朗大少爷双强互宠/反套路甜剧/娱乐圈成长/双向奔赴的暗糖拒绝炒CP的顶流男女主,在「避......
- 2.4万字2个月前
- 璇子:椿璇并茂
- 璇子CP原创女主(有hxt但没有感情喜欢hxt的别进)本文可能会给非非搭新的Cp
- 1.3万字3周前
- 千纸鹤与孤独症女孩
- 白栀子是内心丰富却因阿斯伯格综合症难与人沟通的女孩。十六岁的她,有个和蔼可亲、疼爱她的姥姥刘长英,姥姥常督促她学习、陪她玩耍。但发病后,同学......
- 6.4万字1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