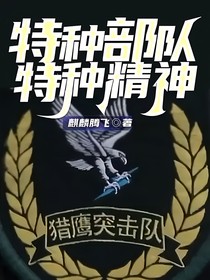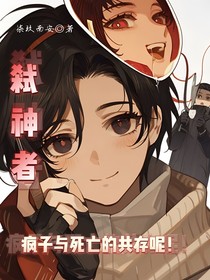第13章:布防图的分量
第13章:布防图的分量
第1节:皮司令的“眼”
秉礼学校的阁楼里,蛛网在梁上晃荡,孙敬之铺开的布防图占了半张八仙桌。赵山河的指尖悬在“老槐树”的标记上,指腹因用力而泛白——图上标着“无岗哨”,但他总觉得哪里不对,父亲生前教他的测绘口诀突然在耳边响:“树高遮目,坟矮藏兵”。
“这图是孙先生带人画了半月的。”李百晓靠在门框上,左臂缠着渗血的布条,是昨天爬树侦察时被日军流弹擦伤的,“日军的明哨都标了,暗哨……”他往窗外瞥了眼,岗楼的探照灯正扫过老槐树顶,“不好找。”
赵山河突然抓起桌上的炭笔,在老槐树的根部画了个黑圈:“日军暗哨藏在这儿。”他的声音发紧,指尖点在树与坟地的夹角,“老槐树的虬根能挡子弹,坟头的石碑能藏人,从这往外看,涵洞入口的动静一清二楚——是最佳狙击位。”
李百晓猛地直起身,伤口被扯得“嘶”了一声:“你怎么知道?”他昨天趴在坟堆后观察了三个时辰,确实在树根后瞥见日军的钢盔,只是没敢确认,“我没跟你说过这细节。”
“我爹曾是测绘员。”赵山河的炭笔在黑圈外又画了道弧线,“他教我看地形,说‘鬼子的暗哨,总爱躲在让自己觉得安全的地方’。”他想起父亲临终前攥着的军用地图,上面也有个类似的黑圈,“这老槐树的位置,符合所有暗哨的特征。”
孙敬之突然一拍桌子,八仙桌的木纹都震得发颤:“对!”他推了推眼镜,镜片反射着炭笔的光,“上周我路过老槐树,听见树下有‘咔嗒’声,当时以为是松鼠,现在想来,是枪栓上膛的动静!”他抓起布防图往怀里一塞,“快!让夜校的人去做标记,用红布条系在槐树枝上!”
“我去。”春杏突然从阁楼角落站出来,辫梢的红头绳晃了晃,手里攥着柱子留下的艾草,“俺熟路,能从坟地的缝隙钻过去,鬼子发现不了。”她往门口走时,赵山河看见她袖管里露出半截镰刀——是柱子的遗物。
李百晓往春杏手里塞了个窝头:“小心。”他的目光落在赵山河画的黑圈上,突然笑了,“皮司令说要找个‘眼’,能看穿鬼子的花花肠子,原来就是你。”他往布防图上的涵洞画了个箭头,“有这暗哨位置,伏击的胜算至少多三成。”
远处传来日军换岗的军号声,悠长而刺耳。赵山河望着春杏消失在巷口的背影,突然想起父亲说的:“好的测绘员,不光记地形,更记人心。”他摸了摸布防图上的黑圈,炭粉沾在指尖,像抹不掉的责任。
孙敬之正用米汤调浆糊,要把修改后的布防图重新誊抄:“等春杏的标记到位,就给皮司令发信号。”他的笔尖在纸上划过,“这‘眼’亮了,咱们的仗就好打了。”
阁楼的窗棂被风吹得轻响,赵山河望着老槐树的方向,仿佛能看见春杏正猫着腰穿过坟地,红头绳在暮色里像一点跳动的星火——那是照亮胜利的光。
第2节:暗号的默契
油灯的光在“礼”字校徽上流淌,银质边缘的磨损处泛着温润的光。赵山河的指尖抚过那道刻意留的缺角,突然想起孙敬之最后一次整理校徽的模样——先生总说“礼者,信也”,此刻这枚校徽,果然成了最硬的信物。
“就这么定了。”李百晓将柴刀鞘往供桌上一放,正放着,梨木的“晓”字在灯影里像个挺直的脊梁,“秉礼学校用‘礼’字校徽:完整的,是安全,让送信的人放心往里走;要是故意磕出豁口,就是危险,掉头就跑,别回头。”
他突然抓起校徽往供桌角一磕,“当”的一声脆响,边缘立刻缺了块小角。赵山河的目光落在那缺口上,像看见孙敬之被伪军按在地上时,仍紧紧攥着校徽的手——先生用生命护过的信物,此刻成了守护更多人的暗号。
“五岳庙就认这刀鞘。”李百晓翻转刀鞘,“晓”字倒过来,像个警示的箭头,“倒着放,是紧急,不管白天黑夜,见了就得立刻碰面;正放着,按约定的时辰来,早一刻晚一刻都不行。”他的拇指在刻痕里蹭了蹭,带出点木屑,“夜校的人都认这记号,柱子以前总说‘李叔的刀鞘比军令还准’。”
提到柱子,春杏突然往墙角缩了缩,辫梢的红头绳扫过地上的步枪——那是柱子牺牲前擦得锃亮的枪。赵山河的心猛地一沉,这暗号里藏着多少人的血?王老汉的玉米地,孙敬之的课堂,柱子的牛棚……每道刻痕都是记功碑。
“皮司令定的规矩,就是这点好。”李百晓突然笑了,柴刀在掌心转了半圈,铜环撞出轻响,“简单,管用,就像他打仗一样,不玩虚的。”他往赵山河手里塞了块粗布,“春杏绣的‘礼’字香囊,以后就让她带着送信,姑娘家的针线筐,比咱的枪杆子更不惹眼。”
赵山河展开粗布,上面的“礼”字针脚密实,却在右下角留了个极小的结——是春杏的记号,跟她辫梢的红头绳一样,透着股倔强。“这结要是松了,”他突然说,声音压得低,“就是信被动过。”
李百晓的眼睛亮了亮,猛地拍了下他的肩膀:“赵兄弟懂行!”他往庙门瞥了眼,夜色里传来日军岗楼的梆子声,“就这么办,多一层防备,少一分风险。”他抓起刀鞘往腰间一系,“我这就去跟夜校的人说,让他们认准了‘礼’和‘晓’。”
赵山河将校徽别回胸前,银质贴着皮肤,传来一阵冰凉的踏实。庙外的风卷着纸钱的味道飘进来,混着油灯的烟味,像无数双眼睛在看着他们。他突然想起皮司令的话:“默契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此刻他与李百晓,一个摩挲校徽,一个按着刀鞘,无需多言,已有千言万语。
“咚——”
远处突然传来日军敲锣的声音,三短一长,是宵禁的信号。李百晓往供桌下摸了摸,掏出半截梭镖:“该走了。”他的目光落在赵山河胸前的校徽上,“记住,见‘礼’如见人,见‘晓’如见枪。”
赵山河点头时,油灯突然晃了晃,将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两个并立的盾。他知道这暗号从来不是冰冷的规矩,是用信任焐热的约定——从皮司令到孙敬之,从李百晓到夜校的每个学员,都在这“礼”与“晓”里,藏着同一份盼头。
第3节:首次传信
暮色像块浸了水的布,沉沉压在秉礼学校的后墙。春杏攥着“礼”字香囊的手沁出冷汗,针脚里的棉线被攥得发皱,却仍死死护着囊里的纸条——是李百晓画的日军新增岗楼分布图,边角用红笔标了“速转”二字。
“顺着墙根走,”李百晓送她到巷口时,往她兜里塞了把炒豆子,“遇到伪军就说给先生送绣活,他们查得松。”他的手按在春杏肩上,力道不轻,“记住,香囊不能离身,针脚要是松了,就别往里递。”
春杏点点头,辫梢的红头绳在暮色里晃了晃。她穿件靛蓝布褂,挎着针线筐,筐里的碎布掩着香囊,看着就像个走亲戚的村姑。可只有她自己知道,袖管里藏着柱子的镰刀,刀鞘上还留着哥哥的指温。
赵山河在阁楼窗口等了半盏茶,终于看见墙根的影子。春杏的脚步比平时快,靠近时突然往墙上靠了靠——是约定的“安全”信号。他推开虚掩的门,刚要开口,目光就被那香囊拽住了。
香囊上的“礼”字绣得周正,可右下角的结不对。春杏的针脚向来是“单套结”,利落紧实,此刻却是个松散的“双环结”,线的颜色也深了些,像是被人拆开重缝过。赵山河的手猛地攥紧,皮司令的话突然在耳边炸响:“细节里藏着生死,一点错不得。”
“赵先生。”春杏的声音发颤,将香囊递过来,指尖的炒豆子渣还没擦净,“俺叔说,让您赶紧看,看完烧了。”她的眼睛往巷口瞟,辫梢的红头绳抖得厉害。
赵山河接过香囊,指尖故意在结上顿了顿。线是新换的,比原来的粗,针脚歪歪扭扭,显然不是春杏的手艺。他突然笑了,声音放得轻:“你绣的‘礼’字越来越好了,就是这结……”他往春杏手里塞了块麦芽糖,“下次让你叔给我带两尺蓝布,我想做个新书签。”
“蓝布”是暗号,意为“信被动过,速查来源”。春杏的脸“唰”地白了,攥着麦芽糖的手突然往针线筐里摸——是摸镰刀。赵山河按住她的手,摇了摇头,目光扫过巷口的槐树影,那里有个黑影一闪而过。
“俺这就回去跟叔说。”春杏的声音发紧,转身要走,却被赵山河拉住。他飞快地从香囊里抽出纸条,借着阁楼的微光扫了一眼——岗楼分布图是真的,但角落多了个极小的“十”字,像是暗号。
“告诉李师傅,”赵山河将纸条塞进嘴里嚼烂,混着唾液咽下去,“图收到了,让他放心。”他往春杏的针线筐里塞了个空香囊,“这个旧的我留着,下次让你带个新的来。”空香囊是“信已毁,安全”的意思。
春杏刚走出巷口,赵山河就摸到了阁楼的枪。远处日军岗楼的探照灯扫过槐树,照亮了那一闪而过的黑影——是个穿伪军制服的人,正猫着腰跟在春杏身后。他的心沉到谷底,这香囊被动过,果然是陷阱。
夜风卷着槐树叶的沙沙声,赵山河握紧了枪。他看着春杏的背影在暮色里越来越小,突然想起柱子的照片——少年咧嘴笑着,仿佛在说“别怕”。这封被做了手脚的信,究竟藏着多少凶险?
巩县烽火抗日之豫西铁血提示您:看后求收藏(笔尖小说网http://www.bj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中国川魂第二部
- 书接上回本书是中国川魂三部曲第二部第一部《中国川魂》已经讲完,本书为第二部将为您继续讲述川军将士们1939年-1942年的抗战故事,欢迎您继......
- 10.2万字8个月前
- 特种部队,特种精神
- 看一个小兵成为一代兵王的曲折道路。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 14.2万字7个月前
- 弑神者疯子与死亡的共存呢!
- 当神秘复苏之风吹拂大夏,在那和谐的表面,又会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洛似锦——黎念安宋佑年——沈天韵陈露河——沐协晨赵夜玖
- 1.0万字5个月前
- 九国争霸
- 一个遗失的大陆,行成了九个国家。赵国军营俩个修士因为个人原因杀了城主府的俩个修士。这俩个修士的死,让赵国误以为是敌对辽国干的,以为辽国即将开......
- 0.9万字4个月前
- 决战河山1
- 国难当头,出身于显赫富贵商会之家的川军中尉吴德庆从黄埔军校毕业,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安逸的生活,投身于民族解放的铁血洪流之中。作为中尉连长,他以......
- 35.9万字4个月前
- 战姬绝唱与星穹铁道之终极决战
- 故事讲的是战姬绝唱symphogear与星穹铁道联手消灭黑暗势力
- 2.8万字4个月前